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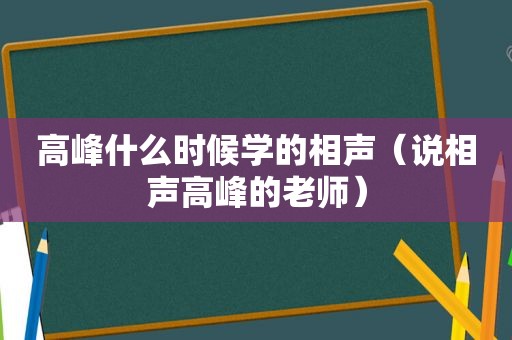
德云社总教习
从未离开相声
被誉为“德云总教习”的高峰,总被人当作老艺人,询问他从艺多少年了?这让生性严谨的他每次都要耐心地征询对方:应从哪一个节点,算作从艺起始年呢?
在天津德云社后台,高峰接受记者专访,谈到最初与相声结缘的故事:“从首次登台的时间计为正式从业的起点,那我就真不算早,我是在初中二年级时登台表演相声的。”他又笑着反问:“比如有的人一提就是将半辈子献给了相声事业,结果中间好几十年都没碰过相声,很可能半辈子加起来也没正式说过几年相声,这也算从艺半生吗?”
少时自学的高峰,曲艺路因其赤诚的热爱而通达,博得老先生们的一致认可。他正式拜的师父有两位,相声门师从相声名家范振钰先生,西河门师从曲艺老艺人金文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都对他青睐有加,也都跟郭德纲说过:“我有个徒弟,现在还上着学,有机会让他去北京说说。”
高峰日日与相声为伴,感悟日深。他慨叹老辈艺人对相声艺术永远存有恭敬心,他们将艺术触角伸进生活的各个角落,犀利地剖析着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并于演出之际时有发挥,“一个相声作品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相声肌体刻烙的是时代印记。”
当问及今日的相声创作为何难出经典?高峰反问:“怎么证明一个相声作品火了呢?它在社会上能产生轰动效应,能创造流行语言。马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的相声作品《纠纷》中有一句‘你轧我脚了’,因场景设计逻辑准确,故事饱满,很简单的一句话,成为多少年的流行语。朋友间有了纠纷,有人来一句‘你轧我脚了’,就能缓解气氛,可见相声艺术对生活的影响力。”反观今日的相声创作,高峰直抒己见:“现在是把流行词汇搁在相声里,相声由过去的创造流行元素,改为借用已有影响力的流行语,这个区别直接导致相声的影响力变弱了。观众现场反映可能很热烈,但忘得也快。我师父范振钰先生与高英培先生的代表作《钓鱼》是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历经几十年,至今经久不衰,令人津津乐道,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从业者深思。”
金文声先生推荐他去德云社
头一场表演了《开粥厂》
记者:您在德云社的演出一般都是倒二,这个位置很重要,感受如何?
高峰:观众总调侃我们是“郭德纲于谦喝水上厕所的时间”,其实这个调侃是我用了比较长时间的一开门包袱,最早是我在说书时的一个现挂。正常演出需要控制时间,前面的节目,一个短上三五分钟,四五个节目加一起就是二十几分钟,这些时间都得我来补。那些年我给郭老师助演,经常一演就是四五十分钟,还演过68分钟。比如郭老师最后一个节目是夜里10点上台,甭管我几点登台,也得撑到点。后来我上台得戴块手表,因为表演时间越来越长,不好估计了。不少朋友反映,你站台上说半天也不入活呢?我不敢入活啊!一入活,我们就下台了。剩下几十分钟咋办?我还得翻个节目,小段就不能说时间长了,那得多少个小段才能把时间填满啊!这就尴尬了。我在“倒二”,是郭老师对我的信任,他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把握好节奏。又有观众给我提过,你怎么说半天都不下台呢?这我得声明一下,可真不是我故意占着舞台不下去,影响大家看郭德纲。我是带着任务上台的,要求我几点完活,我必须得说到点。
记者:您最早认识郭德纲是什么时候?
高峰:2005年,郭老师和经纪人王海到天津看望金文声先生,金先生说:“你先别走,我叫来一个孩子,给你看一看。”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正在实验室做实验,电话没有信号,金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拨号。等到晚上10点多,我出了实验室,立马接到电话:“郭先生在家里等你了,我给你打了半天的电话也联系不上,可急坏我了!”我急忙忙打车赶去了金先生家。见到郭老师,随意聊聊天,问我在哪儿演出、和谁搭档、演啥节目等。最后郭先生说:“行!既然金先生强烈推荐,周末你到北京,周六看一场,周日演一场。咱们互相考察考察,演一场给你50块钱买冰棍。”人家说考察我那是客气,那时候一场50块钱不少了。
记者:到德云社第一次演出效果怎么样?
高峰:2005年7月10日,第一次到德云社,我报的是《开粥厂》。按说头回演出没有演这个的,难度太大。郭老师一听说“行”,安排了李文山先生给我做搭档。演出时,他还安排我返场演了快板《小寡妇》,目的是增强观众对我的熟悉度。也是得到了观众和郭老师的认可吧。自第一次演出后,郭老师每周都亲自通知我周末演哪场。那年德云社还没火,一场演出大概有六七个节目,算上主持人约有十几个人,票价20块钱,刨去人员吃喝穿戴、劳务费、房租水电费等,根本剩不下多少钱,不少时候都是赔钱演出,贵在郭老师对艺术认真,不计得失地坚持。
记者:当时您是天津北京来回跑吗?
高峰:经常坐火车去北京。郭老师不仅给我劳务费,还报销我京津往返的火车票钱。有人说,你上学说相声就为了挣零花钱,实话实说还真不是,路上来回太折腾了,基本上是赔钱圆梦。有家里给的生活费,也不指望着靠说相声生活,纯粹就是对相声艺术的一腔热忱。若不是真爱,也不可能从小时候就始终亲近相声。总的来说,当时为相声支出的钱,远远多于挣到的钱。
难忘中国大戏院专场
亲历德云社成长发展
记者:当年郭德纲第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办专场,应该是您最难忘的一次演出吧?
高峰:那是2005年11月5日,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原定是当年10月5日演出,后因故改到了11月5日。那是郭老师第一次离开北京办专场,也是第一次在家乡办专场,很是重视,但确实没啥经验。网上总有人说我是救场去的,郭老师因为感动,特别招我进德云社,其实不是。那时我已在德云社演出四个多月了,当天我正好在天津演出,所以人在天津。下午4点多,郭老师的经纪人王海给我打电话,让我速速赶到后台。我到了中国大戏院才知道,因为大雾高速公路封了,其他演员还在北京,只能临时买火车票,到天津站的时间是晚上7点35分,赶到中国大戏院最快也得晚上8点,但专场演出的开场时间是晚上7点15分。我们跟戏院的人商量,可否晚点儿开场?人家不同意,票上印着几点开始,就必须准点开灯开幕。这可要了命,整个后台只有郭老师和我两个演员!
记者:这种紧张的氛围还真挺有戏剧性的,说起来像传奇故事,但其实是真事。
高峰:郭老师问我知道《西征梦》吗?我还真没仔细听过。他说,“直接上吧。”我俩换上大褂就上台了。我们俩都是天津人,在家乡演出很亲近,观众对郭老师的包袱很认可,我再砸几个现挂,效果还挺不错。结尾的时候,郭老师直接就结束了,我还按照老规律说着呢,他一鞠躬告诉我“到底了”,我说我也鞠躬。这活是愣上,现在叫“盲捧”,按流行语说Bug挺多。很多观众对这场演出挺难忘的,毕竟难得有一场演出是没对过词的。
这段说完后,郭老师返了《口吐莲花》,也是大段。说到快一半的时候,我往台口一看,大伙儿都到了,于谦老师穿好大褂在后台口等着了。其实不用都穿上,估摸于老师也急坏了,所以穿戴齐全,等招呼。郭老师一回头看到于老师,心里踏实了,节目也算开开了。演员们都挺不容易的,大伙儿着急忙慌地赶到剧场,气都没喘匀就得上台,这就得业务非常扎实,不然容易忙里出乱。
记者:您是德云社的老队员了,是怎么做到一直坚守这个阵地的?
高峰:我是一个随心随性随缘的人,家里人不反对我在德云社说相声,我在德云社待着也挺自由的,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一群热爱曲艺的人聚在一起挺舒服。郭老师火了以后,我们剧场多了,演出场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这是很好的事情,就一直很安心地待下去了。
说相声要有师父指导
更需要自身钻研和苦练
记者:您怎么评价郭德纲的相声?
高峰:郭老师的相声既不是传统相声的照搬,也不是崭新段子博眼球,而是传统翻新的相声。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传统相声全部创新,观众听着没有距离感,既亲近又新鲜还很有意思。我敢说像郭老师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很难再有了。除了社会影响,他对相声行业的贡献是能够与前辈领军人物并谈的。这个访谈发出去后,我想肯定有评论会讲,“你在郭德纲那儿干,当然得说他好话。”绝不是这个概念,我是因为郭老师的好,才会跟着他干。
记者:您被称为“德云社总教习”,谈谈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高峰:大概是在2007年,第一批鹤字科招进来后,我和几个老师一起教学。好几个老师教,总得有个责任老师,我就是责任老师。“德云社总教习”的名头是郭老师给起的。前些年,我有个专场,演出得有个名目啊,郭老师就给我想了这么一个名头。其实,我是愧不敢当,为啥呢?因为我只是把没进门的学员领进门来,仅此而已。这不是谦虚,我们这行从来都是老先生们今儿他教你几句,明儿他教你几句,甚至有时候是老先生教别人,我在旁边听着也等于教我了。这行自古就这样,只要老先生不支你出去,你就可以旁听受教。有时候,我假装擦桌子扫地叠大褂,就为了听几句好受教。过去没有录像,学员是带着饭到演出现场,一边听一边记。马志明先生当年也是带饭去听活,除了活本身,还得听不同人的不同演法。相声这行,总的来说,有师父的指导,更需要自身的努力钻研和苦练。有无数段相声,我一听就能对口型,这就是听得太多了。熟能生巧,首先得熟!师父领进门后,一个演员的艺术水准和业务能力的高低,在于个人的自我要求与积累,所谓“修行在个人”。
高峰自述
上初中时登台说相声
感谢老先生无私传授
相声老艺术家冯宝华和我奶奶家是邻居,按街坊邻里辈分论,我称呼他二爷爷。那个大院里住的人家,几乎都是干曲艺行的,我特别爱去二爷爷那儿听他聊天。老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别和蔼。我记得一到晚上六七点钟,他提个包就出门了。现在回想,估计他是到哪儿演出去了。可惜我那时候才五六岁,没有机会和二爷爷学习相声。
自初中起上台说相声,我登上了不少学校的舞台。渐渐地,校园的大小活动中,我的相声成为必备节目,被老师推荐到社会活动中参加演出。在一次慰问老红军的活动中,我演了《大保镖》,老红军们静静地听着。我们那时根本不懂看场合选活,用行话说就是“把点开活”,可能说得也不利索,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特别感谢那些老红军对我们学生的爱护和尊重。
没有师父交代帮衬,我走过一些崎岖的道路。守着一台收录机,挨个儿台轮着听,只要是听到播出相声,就赶紧录音保存。同学们知道我的爱好,以实际行动支持我,把不听的英语磁带全部赠送给我。我是一边录,一边听,一边学。如今我仍然保留着这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磁带,大概有近700盘。甭管电脑里存着的相声段子播放效果有多好,我也没舍弃这些磁带,它们是我青春的记忆,也是我当初努力的见证。
别看我从初中开始登台说相声,但真不知道社会上还有相声剧场演出。高考结束后,我在家翻报纸,看到中华曲苑成立两周年,才知道有相声专场演出。2001年暑假,我带着和我一起说相声的同学一起到剧场听相声。中华曲苑门票是10块钱,包厢是15块钱,燕乐剧场是6块钱,名流茶馆是10块钱。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于宝林、冯宝华、尹笑声等老先生们恢复了相声茶馆,当时叫“老艺人相声队”。此后我就常去茶馆听相声,去的次数多了,和老先生们慢慢都认识了。
第一次去老先生家,是李鸣宇带我拜访王派快板演员何德利先生。我内心想既是看望老先生,也想跟先生学王派快板。没具体说怎么个学法,我一个穷学生也没啥钱买礼物。老先生非常无私,不要学费,让我周末到家里学快板。后来就约定俗成为周末上午进家学习。何德利先生是出了名的诚恳、朴实、热情。何先生给我说活,手把手地示范拿板的拿法。我特别感谢何先生,无私传授不计名利。
相声门户中,我的恩师是范振钰先生,师爷是班德贵先生,师祖是马三立先生。我2004年6月6日拜师范振钰,赐“应”字。西河门户,我的恩师是曲艺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原名金刚,艺名金连瑞),师爷是张起荣先生,师祖是张士权先生。2006年12月20日拜师金连瑞,赐艺名高增禧。快板门户亦是金文声先生的弟子,快板艺名高启明,师爷是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生,师祖是数来宝老艺人海凤先生。
作者:张一然
来源: 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