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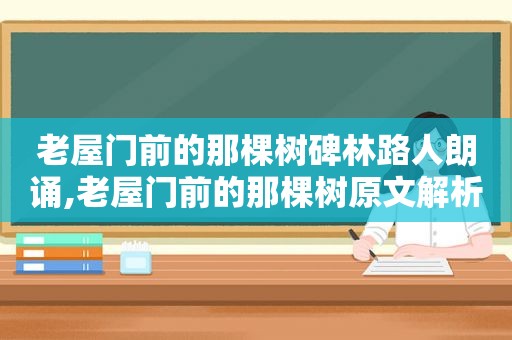
我们家的木屋坐东朝西,屋前屋后都是田野,离山远,离溪也远。每到夏天的午后,火热的太阳毫无遮拦地斜射着木屋板壁,木屋成了一个蒸笼,娘说,晒得没处躲。爹便在木屋前的土坪里栽了棵梨树。
从我记事起,梨树已粗如菜碗,高齐木屋,春夏树叶浓密的时候,整棵树就像一把巨大的伞,给我家木屋带来了阴凉,也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喜乐。
对梨树的期待是从每年正月初一开始的。当我们规矩虔诚地吃完迎新饭,新年就会穿过浓浓烟雾醺醺然地来了。娘用陶钵盛了米饭,放上一个白瓷调羹,嘱咐我们兄妹去给屋前屋后的树木喂新年饭。“树神保佑,果子累累,像天上星子一样多。”“棵棵都要喂,不结果的四季青也要喂,靠它固堤护屋呢。”每年,娘都会这么说;每年,我们都从屋前的梨树开始,在它的大树桠间喂上一调羹米饭,才走向菜园边的桃树,屋后的四季青。也许真是新年饭喂得好吧,梨树年年一树素白一树绿,一树青梨一树甜。
秋冬两季,梨树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听凭我们攀爬、骑坐。娘天天忙碌,但眼尖得很,只要梨树枝头冒出一点嫩芽,她就会在树干周围插满杉树枝、猫儿刺,我们再不敢攀爬。这个时节,梨树一天一个样地开始了它的戏法:清早起来,睡眼惺忪中,发现了一两个花蕾,揉揉眼再看,又发现了几个。待到梨花全部绽放,花丛中叶芽开始舒张,树冠一天天变绿。一场梨花雨过后,枝桠间会有小青果钻出来。天天瞅它,它只有那么大,干脆忍着几天不去看它,它就会吓到你,竟然有鸡蛋那么大了。到了六月,阳光一充足,一天热似一天,它就水灵灵、甜津津的了。这个时候,大哥二哥奉了娘的命令大显身手,开始分批采摘。
刚下树的梨,和地里生产出来的所有作物一样,娘都会精挑细选一篮子,由大哥给独居的奶奶送过去尝鲜。娘的这份孝心,至今在村里传为美谈。舅舅、大伯和爹的师傅是一定要送的,还有邻里。
梨子成熟的时节,我感觉是我家最富有的时节。一篮子梨子送出去,从来不会空篮子回来,这家的鸡蛋、玉米,那家的花生、甜高粱,都是我们的爱物。有次奶奶竟然把姑姑给她买的橘子罐头放在篮子里要大哥带了回来,这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稀罕物啊。爹找来一把电工起子,小心地撬开盖子,娘拿来四个饭碗给我们兄妹平分,娘瞅了瞅罐头,先给我们每个碗里夹三个橘片,最后剩下的一片夹进了爹的嘴里,一滴汁水落在爹的胡子上,惹得我们大笑。娘再给我们的碗里均匀地倒上罐头汁水,剩下一点点汁儿娘倒进了自己嘴里,并舔了舔瓶沿,馋得我们兄妹再也忍不住,用手捏着橘片,喝着甜蜜的罐头汁儿,全家喜气洋洋。
邻居,过路人,经常有人坐在梨树的阴凉里,吃着那甜脆多汁的青梨,谈论着农事和家常。后来田地承包到户,我爹有文化又勤劳,搞科学种田,粮食大丰收,担回来的谷子堆满了堂屋,这么多谷子必须马上晒好入仓才行。爹和娘商量来商量去,只好把屋前坪里的梨树砍了。我们虽然很是不舍,但有白米饭吃的幸福还是远胜过对一棵梨树的热爱。
树大分杈,人大分家。我们兄妹一个一个离开了老屋,爹也因病离世,老屋老了,只剩下娘还在那儿走出走进。每到春节和娘的寿辰,我们一大家人聚在木屋里,喝着娘酿的水酒,满屋子热闹,偏西的阳光透过门窗直射进堂屋,娘就会说起老屋前的梨树,说起栽梨树的人。(文/罗瑞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