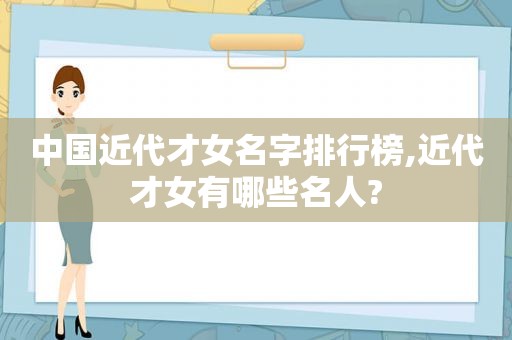本
文
摘
要

凌叔华(1900—1990),名瑞唐(棠),笔名叔华、素心,祖籍广东番禺县,生于北京。凌家是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凌叔华祖父凌朝庚是番禺巨富,父凌福彭是光绪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等,晚年与梁鼎芬等编纂《番禺县续志》。凌叔华曾师从女画家缪嘉蕙、王竹林、郝漱玉习画,并得到齐白石亲传,又曾跟随辜鸿铭学习古典诗词和英文。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擅长写作与绘画,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民国才女。1941年底,凌叔华途经广州湾进入内地,撰写了《由广州湾到柳州记》一文记述她的见闻。
凌叔华
从香港到广州湾
1925年1月,凌叔华创作的短篇小说《酒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轰动一时,在国内外产生不少反响。凌叔华一举成名,迅速成为知名女作家,从而奠定她的文坛地位。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学校的金钥匙奖,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任职。
1927年7月,凌叔华与陈源结婚。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兼英文系主任。他们相识始于1924年,当年5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陈源和徐志摩负责接待工作,凌叔华加入欢迎代表行列。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曾借用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凌叔华和陈源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此后通过书信往来讨论文学艺术问题,后来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两人婚后曾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的身份到日本留学一年多时间。回国之后,陈源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凌叔华跟随丈夫来到武昌住在珞珈山上,与女作家苏雪林、袁昌英过从甚密,被并称为“珞珈三杰”。在此居住的几年时间里,凌叔华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绘画活动,曾负责主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积极扶持青年作家。
随着战争局势发展,不少学校内迁到大后方,武汉大学决定内迁到四川乐山县。1938年初,凌叔华又跟随丈夫陈源迁到四川乐山。1939年底,凌叔华母亲逝世,她从乐山到北京奔丧。根据凌叔华和陈源的女儿陈小滢回忆,“1939年,母亲说外祖母去世要回去奔丧,她一个人独自带着我离开四川,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已被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她们最初住在北平史家胡同,1940年凌叔华在燕京大学兼课,搬去燕京大学南门外的羊圈胡同居住。1941年秋,华北战时吃紧,凌叔华决定携小滢离开北京回到乐山。“两年后的1941年秋天,母亲决定带我回四川。那时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经香港转到广州湾,乘的是香港沦陷前的最后一班船。到了广州湾之后,听说香港已经沦陷,所以又赶快逃难,乘了小火轮,挤上破旧的汽车,再转乘小火车,经广西柳州、桂林、金城江,再到贵阳、重庆,最后回到乐山时,已经是1942年的春天了,这中间竟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凌叔华和女儿从北京出发,经过上海到香港,然后从香港途经广州湾进入内地。
凌叔华将这一路的亲历过程撰写为《由广州湾到柳州记》。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建军在《凌叔华佚文及其他》中指出,“1942年,凌叔华把她从广州湾至柳州的这一段经历写成《由广州湾到柳州记》一文,发表在当年8月的重庆《妇女新运》第4卷第8期。全文约8000字,如同日记一般,详细记述了其逃难时的见闻和感受,在具体展现战时社会乱象的同时,也随手对沿途的山川风物作了生动的描绘。这篇文章是了解凌叔华生平事迹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国威也认为,该文“是一段有关抗战时期广州湾的宝贵史料,保留了当其时广州湾社会概况的文人观感”。正是在凌叔华的笔下,使我们看到当时广州湾、遂溪和廉江的诸多面相,对于战时广州湾进入内地的细节有更多的了解。
凌叔华曾住赤坎宝石大酒店
1941年12月3日,凌叔华乘船到达广州湾,她在《由广州湾到柳州记》中开篇即写道:“笔者去年十二月二日离香港搭船到广州湾,三日到广州湾西营,即乘公共汽车到赤坎。这地方因是法国租界,且由香港到内地,不必经过敌人防线。有此优点,故此两年这地方突然繁荣起来,尤其是海防也归敌人管辖之后。”抗战时期,由于沿海城市的相继沦陷,广州湾成为进入内地的主要通道,聚集大量的难民和商人,广州湾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港口。
宝石大酒店位于赤坎中山二路。
凌叔华来到广州湾时候正是香港沦陷前夕,为了等待一位朋友从香港过来,在赤坎待了一周时间。“由赤坎到郁林,须走六天旱路,得有走过的人带领方才放心走。我们因为要等待一个朋友同行,故在铜臭熏人、 *** 林立的赤坎住了近一周。此地店房粗俗而索价昂贵,四望均为作买卖店铺,马路虽有两三条,但十分嘈杂污秽,连一处可以散步的地方都没有。我同小莹(注:“小莹”即“小滢”)住得闷极了。她才过十岁,对于买卖,比我更觉索然。朋友本约定九日由港到,到后即全走旱路去郁林,不想在八日下午我们就得到号外说日本已实行攻打香港了。赤坎只与香港相隔一日水程,故街上立刻呈现恐慌,居民买米买面买油买酱,饮食店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似乎都想把钞票掷出去,换回随便什么可吃的就成。与我们结伴走的一个朋友联君,他也觉得如此情形,此地不可再住下去了。”凌叔华将赤坎形容为“铜臭熏人、 *** 林立”,赤坎作为广州湾的商业中心,经济呈现“畸形繁荣”,大型赌馆包括“吊花会”“两利”“万利”。1939年9月5日《大公报》的报道中就曾提及,广州湾除了“烟赌公开,居民多染此癖,娼妓也公开,妓院林立,靠妓院过活者几达千人。因烟赌娼妓都公开,所以广州湾有“小澳门”之称。故此凌叔华对于广州湾赤坎的观感并没有好印象。日军攻占香港的消息传到广州湾,居民就疯狂抢购食品。在同行者“联君”的建议下,决定赶紧逃离此地。
她们住在大宝石酒店,计划通过雇请轿夫、挑夫开始进入内地。“我们回到大宝石饭店,即去找账房先生代为找轿夫脚行,定于次日动身到郁林去。雇了两乘竹轿,我一,小莹一,另雇了挑夫七人,联君随挑夫走路。价钱时常改,此次言明由此到郁林,每轿二百四十元,挑夫每市斤重合一元二角,(且须以广西秤计,边秤比较低些),伙食自备,赏钱随意,并由账房开具保单,担保工人可靠,另外工头二人签字,担保其他工人,工头之身份证明书交与我们拿着,以免意外。”“大宝石饭店”即宝石大酒店,20世纪30年代初由许爱周兴建,内设中西餐厅,并设有花园茶座,是当时综合性的新型酒店。为了保险起见,凌叔华通过酒店的账房先生联系轿夫、脚行,议定价钱,开具保单就从赤坎出发往郁林。就在凌叔华来到广州湾的数月之前,1941年7月21日《申报》登载了署名为“漱南”的《经广州湾赴内地途径与旅费》一文,里面就提及:“赤坎至郁林,坐抬轿六天可到,每人抬费250元(一人坐一轿,行李不能随身带,虽小包亦为轿夫所不允)。行李每市斤8角,假定以140市斤计,共须112元,六天食宿共60元。最要注意者,即能多人合一团体,行李轿在前,客轿在后,以便监视,每到一宿站亦须轮流注意,尤以石角宿站要特别注意。第一日赤坎至遂溪,第二日遂溪至廉江,第三日廉江至石角,第四日石角至良田,第五日良田至陆川,第六日陆川至郁林。”两者价钱相比,轿钱从250元降到240元,行李则从每市斤8角升到1.2元,说明这是时价,并不是统一的价格。但是他们走的路线就是一样的,凌叔华一行也是从赤坎到遂溪,再到廉江、石角。
凌叔华画作。
途经遂溪、廉江的见闻
香港沦陷,人心惶惶,她们按照计划往遂溪出发。“诸事均办妥当,于是我们次日清早九时冒雨走,意欲当日到遂溪,因那里有比较干净可靠的客店下榻。十一时到雷州关(即蔴章关)时,大雨倾盆,轿子衣箱均淋漓滴水,查关的在一架蓆棚下,地上水深没足,泥泞不堪,但铁面的关员并未忘记他的威风,他喊令脚夫放下各物检查,每个衣箱,每件东西,都拿出来细看,看到我的旧皮鞋及旧衣服,有一个说:‘这东西还带到内地,算来不够挑夫力钱’,同行朋友因带了几身新做西服,他们很兴头的拿去估价,结果按赤坎时价估出,得收税八百元,联君忍痛交了,方让我们挑夫走路。与我们同被查关的人,有一人带了两小箱606药针,一个查关的低声要求他照原价卖两盒与他,一切免了上税,但那人不肯,结果抽了他一大笔税,这人后来在路上把这事告诉我们,他觉得纳税还是上算。”她们刚出寸金桥没多远就来到麻章海关,随后受到关员的检查。同行“联君”携带的西服被收税800元。“606药针”是治疗皮肤病的药物,能有效治疗梅毒,由德国科学家、“化学疗法之父”埃尔利希(1854-1915)发明。这位同行者宁愿抽重税也不愿意原价出卖,也说明贩卖这类药物取得高利润。 她们在途中欣赏树林和流泉,还在草棚底下吃了一碗煮红薯,只卖2角一碗,称得上是价廉味美。穿越田陇,凌叔华和小莹下轿走路,大概5点左右抵达遂溪长江饭店。凌叔华写道:“遂溪为小县,居然有公园,有体育场,惜天黑,未能各处细看。长江饭店,房间均木板作壁,一室二床,有铺盖的要十二元一宿。被褥不甚洁,我们均换了自己的,有饭食,每人每餐五元大洋,我们已饥肠辘辘,夜餐于此。”她们惊叹遂溪这个小地方拥有公园和体育场。
翌日天还没亮,她们就离开遂溪,上午10点左右在山坡一饭铺吃中饭,有白饭,有腊肉,腊肠,炒蛋等,每人花费5元。下午3点就达到廉江,到街上散步,去杏花楼吃晚饭。“廉江为较大之县分,街道铺面均宽阔。我们在路上买了一个菠萝及几个香蕉,到杏花楼。三人花了十五元,吃了餐很丰盛的饭。有鸡,有鱼,有肉了。此地去年被轰炸过,到处断壁颓垣,但现在人心似已恢复常态,生意人们熙来攘往,十分热闹。进廉江境时检查站上知道我们由香港到内地的,都纷纷围了讯问香港情形,适有萧氏父女正经此欲到广州湾转香港回沪,听我们说香港已开战,他们也停在廉江,预备走回路了。萧氏已过六十,人却健实,女约廿岁,亦能随父走路。他们来时雇了两架自行车,行李及人都搭在骑车人后,说是比轿子快些,但是回去时,他们决定走路了。”她们花了和午餐同样的价钱,却能在杏花楼吃了一餐丰盛的饭,显然晚餐更为优惠。
次日,她们9点从廉江出发距离十几里是鸡笼山、七星镇,“据说那是土匪出没之地,联君去岁经此,彼匪抢劫过,过那里的人如请了县府的兵保护过去便没问题。我们搭在另外六个客人一齐,合份请了三个兵跟着过去,共用了六十元,另加酒钱十元,他们三人全副武装陪我们过岭。”她们凑钱请三位士兵保护过岭,但是凌叔华和年幼的女儿都想见识一下“土匪”,“小莹与我都有点兴奋,心中也想遇到土匪见识见识,但也怕真得遇到土匪。她一路问人到了鸡笼山没有,但到了七星镇过大来桥遇一粗大老人及二青年人要收路钱时,她又害怕了。据后来说,老人等如人少且无兵相送时,他们便要强收买路钱了。在鸡笼山上时,有手拿白布旗自卫团三人向路人捐钱,不给他们钱也没作声,据说这也是土匪一种。七星镇及鸡笼山形势均不雄壮,土匪想来也不是什么大规模的。”估计这些散兵游勇就是敲诈零星行人得以度日。
从廉江到石角的公路宽敞,可惜被破坏了,“电线杆沿路歪的斜的,甚至以一根细竹代替的,样子十分贫乏可怜”。下午4点半到石角,那里有财政部派遣的关员检查行李。石角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因此带着挑夫到两广交界处的蟠龙住宿。“小莹很高兴,因为她发现了自己在十分钟内走两省,在广东吃饭,在广西睡觉,石角街道十分古旧狭窄,所以铺面人家在市上的均有宽阔屋檐,遮了半边街道,大约南方多雨,此种办法,专为下雨着想,赤坎旧街亦如此,街道狭窄黑暗,很不方便。”实际上,这一类骑楼建筑就是为了阻挡风雨侵袭和阳光直照的,难免使整体街道显得狭窄黑暗。
随后,他们继续赶路,经良田、陆川、郁林、贵县、桂平、石龙、象县、白沙等地,抵达柳州,然后回到四川乐山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