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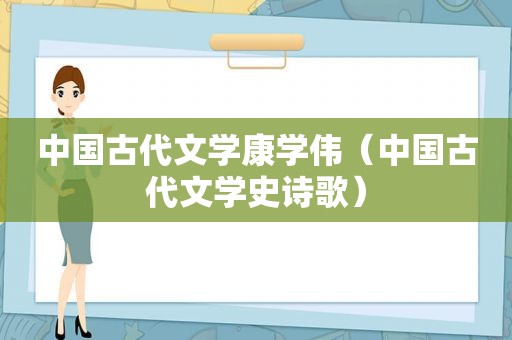
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
全民阅读
★★★★★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在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大有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坚定学术理想,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传承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文学与中华文明走向新的历史性辉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贡献中国文学应有的智慧。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担当,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肩负的时代使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应该坚持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弘扬传统;创新话语;贡献智慧;文化担当;时代使命
***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淀了非常深厚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走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应当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贡献文化智慧,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义不容辞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
一
深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其学科走向创新发展,首先要大力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家国情怀与美善理想,这是中国古代优秀作家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精神传统。
首先,弘扬家国情怀,就是要崇尚理想信念、守护民族气节、深化人文关怀,以此确立我们的文学价值观自信,这是我们创新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贡献文学智慧的精神导向与思想基础。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家,对于人生、社会、民族、国家,始终拥有一种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远大抱负,一方面追求完美的人格理想:“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一方面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象辞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这种理想信念成为古代文学家们的主流价值追求,并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当中。
屈原一生坚守高洁的理想,不愿同流合污,虽被放逐,却依然坚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信念;司马迁身受屈辱,但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志向,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曹操虽历经征战,年齿渐暮,却仍然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诗文中,展示出美好的“桃花源”理想。李白、杜甫虽为一介布衣,但却拥有“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太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比稷与契,此志常觊豁”(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雄心壮志。这些理想信念的内涵虽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肯定自我的价值,坚信人生的道路,期待社会的进步,勇于克服困难、实现理想信念,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奋斗目标,更是一种道德追求,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精神传统。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这种家国情怀就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气节。《诗经·无衣》表达了为国御侮的决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则精心刻画了李广、苏武等忠勇报国的民族英雄形象。从魏晋六朝以至唐宋明清,这种心忧天下、勇赴国难的精神,在一代代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陈子龙《辽东杂诗》八首之三)等等。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在民族危亡之际,用自己的文学作品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与精神标识。
深厚的民本思想与人文关怀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大主题与重要内涵。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追求“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理想。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念。
所有这些思想价值观念,都在倡导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浓郁的人情之美,成为古代文学反复吟咏的传统主题,如孟郊吟诵母子情的《游子吟》,苏轼追忆夫妻情的《江城子》,李白感念朋友情的《赠汪伦》,白居易咏叹天涯情的《琵琶行》等等。进一步的,儒家还将“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爱人”精神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这种仁爱精神具有了体恤民众、感受苦难、承担责任的重要内涵:“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羌村》三首其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这些诗篇感情深沉,关注现实,执着人间,不求个体解脱,不寻来世恩宠,而是将个体心理沉浸在人际关怀的情感交流中,这不是概念的认识,而是情感的陶冶,它将以亲子之爱为基础的人际情感塑造、扩充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人性本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最具标识意义的精神内涵之一。
其次,弘扬美善的理想,就是要弘扬美善统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要求真、善、美三者的有机统一,但西方文学更注重真与美的结合,而中国古代文学更注重美与善的统一。
孔子曾评价《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认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韶》是颂美大舜的乐曲,所以得到孔子的全面肯定,《武》是歌颂周武王的乐曲,孔子认为武王的文德不足以媲美武功,因此说它美则美矣,然未尽善。可见,在孔子眼中,乐曲的最高标准是尽善尽美,美善合一,而善的地位似乎更在美之上。这种美学精神也充分体现在古代文学家的理论与创作中。
比如曹丕提出“铭诔尚实”(《典论·论文》),左思反对赋创作“虚而无征”,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三都赋·序》),刘知几倡导“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作风(《史通·载文》),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标举“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的创作原则。这里的“实”“征”“本”“不虚美”“信”,与其说是求真,不如说是向善。在古代文学家看来,求真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精准描摹客观事物,而在于追求一种真实、真诚、诚信的态度,在于扬善贬恶,在于追求至善,这当然与古代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有直接关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毛诗序》)可见,“诗”所要言的“志”,事关治世安邦,事关“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说到底,就是要通过“诗”传达事功、政教、历史、教化等等社会经纬之善。
事实上,《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皇矣》《绵》等篇章所讲述的也正是族群的历史、政治与教化之事。所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意,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这便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教说,也就是美善统一的理想与精神,它要求文学发挥讽谏劝戒的政治教化功能,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将社会的伦理政教与个体的身心情感统一在文学作品当中,一方面充分表达个人的的情感、欲望,一方面适时的传递社会理性、社会规范与政教体制,由此也形成了文与质、缘情与载道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学理论形态,美善统一的理想也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原则与美学精神,渗透在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即便抒发的是浓郁的个人情怀,也依然离不开政教伦理之道,因为古代的文学家与士大夫们本来就是伦理政治的主体,所以美善兼具、美善统一的文学精神也就必然贯穿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性特征与重要传统,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题、思想内涵、艺术风格、美学传统的形成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创作、文本和批评话语体系,为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学科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承担起确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贡献文化智慧的时代使命,就必须进一步创新话语体系,提升话语的创造与创新能力。
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传承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文本与批评的话语传统。古代文学的观念、创作、文本与批评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中发展起来,有别于外国的文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就文学创作目的而言,古代文学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理为本”“文以意为主”“文以气为主”等观念;就文学创作来源而言,古代文学强调取源于物、取源于道、取源于心、取源于经。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夫文章者,原出六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第九》)等等;就文学创作的思维而言,强调以“静虚”的心态领悟、体验对象,以“神思”的“妙想”构思文本、布局文本,以“兴会”的瞬息激发文思、激发创造。
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系统而独特的文本话语体系。首先是文体话语。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到李昉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姚鼐《古文辞类纂》等等,对于文体的分类少则十余种,多则百余种。这与中国古代特有的泛文学观念以及多元化分类标准有直接关系。就表述方式、语句、格律而言,大致可分为诗、词、散文、戏剧、小说等;就文体内部结构而言,大致可分为五古、五律、七古、七律、骈文、散文等,这些文体有相对侧重的语体功能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比如文重叙事,诗重言志,词重抒情,比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陆机《文赋》)古代文学的文体话语,是在中华民族话语秩序中形成的文本体式,表现出古代文学创作、批评特有的文本言语方式,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
其次是语言文字的表达话语。汉字是中国特有的文字符号系统,具有视觉、听觉和联想的独特美感,对话语的表达方式也有着独特的要求:“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文章要避免生僻怪字,否则不和谐;要避免多次出现同一偏旁的字或同一个字,要合理布局繁简笔画,否则影响整体美感;要严格规范排列组合汉字的声调、音韵、格律,以此形成双声之美,叠韵、押韵之美,平仄相间之美。此外,古代诗歌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字数由偶而奇,单音字和双音词的配合更趋默契,韵律更加和谐,语言节拍也更富于音乐性;而词组、语句也有独特的话语表达特点,可以借助结构倒置、省略介词等手法,拓展文本内部的美感想象空间。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汉字、词组、语句和语汇共同构建起来的文本话语体系,创造出独特的汉语言文字之美。
中国古代文学还有系统而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就社会批评的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就是“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就是不拘泥于文字、词语的含义,而要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理解作者的创作主旨。为此必须通盘把握作者的思想人格、创作背景,围绕文本、遥想作者,披文入情、反复涵咏,深入肌理、透彻分析。就文学本体批评的角度而言,还有立足历史流变的文本史批评以及立足文本自身的意象批评。前者侧重研究不同文本间的文体关系,后者侧重研究文本自身的风格特点。此外,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和评点等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批评文本形态,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几种批评方法和文本形态各有特点又相互渗透,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话语的有机性和整体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话语体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它们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古代文学是不可逆转和不可复原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其内在的文学活力存在于当代人对古代文学不断的解读和理解中,存在于古代文学对当代的文学文化、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当中,正是在这种解读与影响的过程中,古代文学为当代人提供民族文学遗产的滋养,为当代的文学和文化创造、为中国特色文学学科的建构提供灵感与智慧支持,这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目的与方向。
推动古代文学研究传统话语体系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首先应树立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主体意识。将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经验与问题,放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中、世界文学发展的格局中加以考察,一方面认真剖析、厘清在文学的起源、本质、价值和文学史观等重大问题上,西方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话语的负面影响,纠正以西方文学话语为坐标系,研究、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偏差;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积极开展与西方文学话语体系的平等交流对话,在对话中激发创新意识、提升思维能力、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在对话中逐步确立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在全球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中的主体定位。
其次要立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学科方法,构建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学科体系。与西方的纯文学观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观是包括学术文化与文学在内的多元文学观;与西方崇尚真美,注重叙事、写实不同,中国古代文学强调美善统一、言志抒情、传神写意,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话语的出发点。要摒弃目前狭隘的古代文学学科理念,倡导广义的古代文学观念定位,倡导构建多元知识兼容的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学科界限,拓展学科视野,促进交叉研究,创新学术思维,恢复古代文学研究的本来面貌,重塑古代文学史观,历史地、动态地描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观念、内容形式、文体功能的古今演变过程。这意味着我们既不套用西方的概念术语,也不沿用狭义的学科方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而是立足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体观念,认真研读古代文学文本,建构真正具有古代文学特色的研究话语体系。
要探索形成中西融通,科学、规范、多元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应将训诂、评点、感悟、鉴赏等传统研究方式与实证、演绎和理论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注重原始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注重以吟诵、诵读、感悟和体验的方式,理解文学文本的审美形态、审美特性与情感内涵,再现古代文学创作的精神历程。要在中国古代重实据、重情韵、重领悟的方法基础上,运用西方重理性、重演绎、重归纳、重系统的逻辑思维方法,寻绎、重构古代文学史、文学理论史的研究范畴、思想体系,形成中西融通、有古代文学学术个性与学术品格,独立而开放的学科研究方法。
要积极对接中国当代的文学文化话语体系,让古代文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立足人生、立足生活、面向大众、面向社会。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追寻、描述以及尽可能还原古代文学的现象与场景,并在这个过程中,续写和重塑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情感、审美与生命世界,这不仅是指向过去的,更是指向当代与未来的,这不仅是回顾古代的文学与审美生活,更是在创造未来的审美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文学的研究话语体系应当也必须与当代的文学文化话语体系一脉相承、紧密相连。这样的话语对接不仅仅只是学科与知识的传承,更是思想与生命的传承。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理应关注人生、关注生活、关注心灵,关注当代现实生活,关注古代文学的审美世界与当代社会精神生活的传承关系,关注它们为当代人与当代生活提供怎样的精神滋养与文化资源。只有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能“接地气”,才能走出古代文学只是“文学研究者的”文学研究这个单一化格局,才能与人民大众与当代生活融会起来,才能切实的参与到当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创造与创新之中,才能让这一“古代的”文学现象创造性的转化为“当代的”思想资源,并在当代的文学与文化语境的阐释中获得创新性发展。
三
弘扬古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创新古代文学的研究话语,其根本目的还是要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创造贡献智慧。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情感、审美与生命,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是有着鲜活思想与丰富智慧的文化形态,对于中国人的身心养成与精神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与创新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西方古典文学不同,中国古代文学创造的情感世界,重点展示的不是人与神衹、人与自然环境的情感关系,而是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尤其是君臣、亲子、夫妇、兄弟、朋友、亲族、同胞之间的人际关怀,以及由此展开的人生境遇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古代诗歌中,送别、赠答、感伤、婚恋、爱情、怀旧、咏怀、感遇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主题:“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杜甫《羌村》三首其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等等。
与西方古典文学不同,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感世界中,很少有凶暴、残忍、野蛮、邪恶的极端情感情绪,有的只是幸福、悲伤、苦难、喜乐、忧郁、欢畅等正常的情感情绪,人间世情百态在文学作品中被深情咏叹、细腻描绘、深入体验、反复咀嚼,这些都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情感形态、情感故事、情感方式和情感内涵。应当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就是展示、记录、承载中华民族情感的历史,也是后人不断咏叹、吟诵、感受、体验中华民族情感的历史,这个巨大的情感世界,拥有巨大的情感力量,也拥有巨大的情感智慧,它对于健全我们的心灵世界,丰富我们的情感情怀,认知中华民族的个性与气质,感受中华民族的情感正能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情感智慧的重要来源,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精神。“礼”不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言语和仪容,对人的内在心理情感也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与“礼”不同,“乐”主要是通过内在情感的交流,达到稳定群体和谐秩序的目的,它不是“礼”那种外在的强制性约束,而是在个体感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感本体——一种和谐的“内秩序”:“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使亲疏贵贱长 *** 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乐者……所以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记·乐记》)
“乐”所追求的是身心和顺、秩序井然、彼此和谐、相互均衡,因为要塑造和谐的情感,要陶冶性情,所以要求不同的艺术形式匹配相应的情感和道德形态:“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礼记·乐记》)并要求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艺术效果。可见,周孔之礼乐,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利于和谐秩序的极端情感排除在艺术形式之外了,从而,自然的情欲在文学艺术中升华为人际间的和谐情感,自然的感官也升华为充满世态温情的艺术感受,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塑造、陶冶、建构合乎理性、秩序、和谐的情感本体,也就是一种完美的中庸式的情感人格,它外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趣味、美学传统与人生智慧,而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诗歌的内涵与形态,最为精准、细腻、全面的呈现了这一情感本体对古代社会与人群的情感滋养与智慧熏陶。
然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儒家的礼乐精神不可能永远一统天下,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思潮在不断更新着古代文学的内涵与主题,丰富着古代文学的情感智慧。事实上,无论是超然物外的老庄学说,玄礼双修的魏晋风度,还是妙解般若的佛理禅趣,修养心性的宋明理学,最终总是要落实在情感这个本体上,落实在审美的文本里。当作家在追问生命的本体意义时,同时也是在追问情感和审美的本体意义,多元文化的思想智慧就这样在文学情感的世界里彼此渗透、相互渲染,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感世界,虽有绝望却不致毁灭,虽有自由却不致疏狂,虽有浪漫却不致滥情,虽有藐视礼法、睥睨群雄,却不致离经叛道、反复无常,这里既有个体的强烈情感抒发,又有社会理性的自觉遵循,这里蕴藏着难以言尽的思辨与智慧,蕴藏着个体对自然、人生、宇宙的敏感、追问与深情,它们共同沉淀在含蓄蕴藉、温情敦厚的文学文本当中,共同汇聚成巨大的民族情感本体,显示出巨大的情感智慧,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培育、个性养成、心理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沾溉之功,其泽甚远。
中国古代文学还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古代的优秀作家们不仅拥有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有高超的审美创造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就审美创造的过程而言,这是言与意的智慧,就审美创造的感受而言,这是滋味的智慧,意境的智慧。
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言,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皎然《诗式》),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他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究竟如何才能创造出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言是文学手段,意是文学目的,文学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手段重要而忽略了目的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手段到达目的,一方面又要通过否定手段来强化目的。对创作者而言,文学创作最终呈现的美,不是“言”这个手段之美,而是“意”这个作品之美。对接受者而言,要领悟到这个美、这个意,就要披文入情,唯意是求,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之美而忘记了“意”这个根本之美。
因此,当作家创造出文学作品之后,当读者开始全身心的关注作品之美而完全忽略了文学手段之美时,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才真正全部实现,这样的文学审美创造才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手段只有充分的否定了自己,才能实现文学作品之美,对手段否定的越彻底,对作品的创造就越成功。这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智慧与审美创造观,其思想渊源依然要追溯到儒道两家的文辞观与言意观中,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天道》),“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显然,言与意的审美智慧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滋味与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审美范畴,它是从文学品鉴与接受的角度,对文学文本审美感受的高度概括,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与西方美学不同,“味”这个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并不专指感官的味觉或嗅觉,而是指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基础上,感官愉悦与审美、精神愉悦的共同感受:“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十二章》)“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荀子·王霸》)“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言诗也。”(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杨万里《诚斋诗话》)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五官的感觉是相通的,感官的享受与精神的享受也是彼此相融的,与西方文学家们不同,他们并没有将感官的 *** 与精神的美感机械的割裂开来,而是有机的统一在一起。“滋味”说反映了中华民族注重体验、注重经验,注重整体宏观感受的审美思维方式,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是古代文学对“大羹之味”“无味之味”“至味之味”的崇尚与追求:“大羹必有澹味”(王充《论衡·自纪》),“至味不慊,至言不文”(刘安《淮南子·说林训》),“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有味之味”是有限的味道,“无味之味”才是最全面最无限的味道,才是味道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四十一章》)的境界,它难以言明,也无法言说,超越了具体的语言、感官、形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是有形与无形、具象与抽象、有限与无限的高度契合,说到底,就是心与物,情与景,境与意不分彼此的完全交融,即“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晞文《对床夜语》),“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王夫之《唐诗评选》),这与西方文学创作推崇的典型论大相径庭,是有着中华民族思维特色的审美智慧。
中国古代文学还创造了一个生命的世界。生命是文学的主体,也是文学的主题;生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也是文学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命意识、生命活力、生命智慧的文学史。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有大量歌咏人生苦短、生命易逝的篇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它们展示了中国古人特有的生命意识,展示了他们对时间和生死问题的领悟。显然,短暂的生命,流逝的光阴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无限眷恋,对生命不朽的热切向往。而面对短暂的生命,儒道两家表现出不同的生命智慧。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儒家看来,只要“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不必理会死亡。因为“人生活一天,便要作一天应作的事情,对于将必至的死,不必关心,不必虑及,更以死为息,为一生努力之最后静息,如此则又何必恶死?”①真正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如何在短暂人生中赢得永恒和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是儒家的生命智慧,也是它看待人生的基本价值原则:承认死亡的存在,但以德行功业文章的不朽来抗拒死亡的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个体生命永存的象征:“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古风》其一)可见,儒家生命智慧的核心在于:关注存在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体寿命的长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孟子·告子上》)
道家的生命智慧则不同。道家看人生的出发点是“道”,道的特点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缓急相摩,聚散以成……穷则反,终则始。”(《庄子·则阳》)在道家看来,只要顺应大自然的循环变化,加入到宇宙的运行秩序中,就无所谓生死的变化:“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庄子·庚桑楚》)既然对死亡的超越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么就将这种超越落实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中:“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因此,庄子讲的“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人的本体,他把人作为本体提到宇宙论高度来论说,也就是说,它提出的是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同一性”②。这个所谓的人的本体,就是庄子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就是古代作家如李白等所向往的神人、至人般的绝对自由:“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身世如两忘,从君老烟水。”(李白《金门答苏秀才》)对李白来说,“道”与淳真高洁自由奔放的人格是同义语,追求道,就是追求在时间(无生不死)和空间(羽化登仙)的拔俗超世,使自我进入空灵的自由境界,在诗歌中则表现为遗世独立,仙袂飘举的傲然风骨:“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四十),“凤孤飞而无邻”(《鸣皋歌送岑微君》),“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
在古代文学的创作中,儒道两家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智慧常常汇聚一气,彼此冲撞又相互交融,文学家的精神世界既有壮怀激烈的人生奋进,又有飘逸洒脱的超越追求,这两种主题、两种情怀交织在一起,使他们的诗文迸发出既雄阔壮美又超迈高举的万千气象:“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搅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而这,不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生命智慧的特有魅力么?生命是短暂的,时间是永恒的,死亡是必然的,人生由此开启了生命之忧,生命之思,但只有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的忧思才能焕发为激昂的青春,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时间才会被赋予情感的厚度,情感才会被赋予时间的长度。于是,在文学创作的咏叹中,短暂的生命、短暂的时间被唯美化、情感化了,在文学文本的吟诵中,死亡的忧惧转化为有意义有情感的生命歌咏,从而死亡不再恐怖,时光不再短暂,而是转换成为艺术之美,生命也因此更加灿烂,这就是古代文学的生命智慧。
四
中国古代文学,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又繁荣兴盛的发展之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凝练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学传统与中华文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文学发展与文明进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我们要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贡献古代文学的思想智慧,就应当进一步坚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的学术理想,树立为党和人民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的学术信念,坚守注重传承、追求创新、严谨求实、不务名利的学术品格,深入研究、系统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思想内涵与精神传统,深入领会、深刻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要义与生命活力,发自内心的尊崇、尊重、尊敬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推动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走向时代化、大众化和国际化,这是我们秉承中国文学理想,坚定中国文学自信,推动中国文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应当积极推动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当代社会,走进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不断增强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要注重将知识普及与价值观传递相结合,国内普及与国际传播相结合。要注重精准普及、精准传播,要对古代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准确提炼、萃取,将书本知识刻印在记忆和心灵深处;要充分发挥古代文学在抒情言志、塑造形象、写意传神、营造意境方面的美学优势,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人格魅力、情感魅力、艺术魅力感染青少年、感染大众,将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输送到我们的血液里、根植到基因中,深入到内心里,不断强化我们对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体认、体会与体验,努力做到知行合一、言行统一,激活深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基因,使我们从中获取知识、汲取营养、吸取智慧,增强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内在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我们秉承中国文学理想,坚定中国文学自信,推动中国文学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宏伟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焕发着蓬勃生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当代的文学文化的创新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与广阔天地。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家国情怀与美善理想,彰显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在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话语体系资源,借鉴外国文学科学方法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中国古代文学丰富多元的思想内涵,深沉博大的生命智慧,饱满鲜活的情感情怀,异彩纷呈的美学风范,要赋予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价值标准、道德准则,使之在当代社会持续保持强大的审美感染力与文化感召力;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于文质论、言意论、形神论、复变论、风骨论、意境论、美刺论等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古代文学思想话语体系进行原创性的理论革新与理论创新,以此推动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走向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文学与中华文明走向新的历史性辉煌,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文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努力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繁荣与发展贡献中国文学应有的智慧。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担当,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肩负的崇高时代使命,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应该坚持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
(康震: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
长安街直播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华网、央视频、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马嘉均;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