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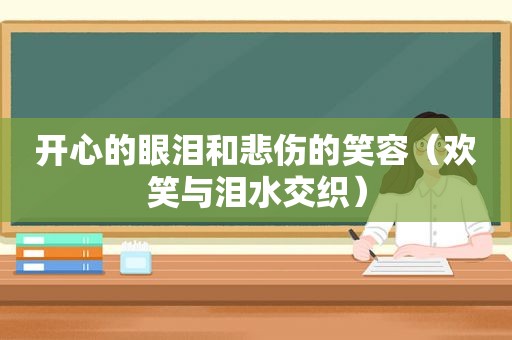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音乐界发生了一件对以后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歌曲《乡恋》事件。
提起《乡恋》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是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基本上人人都听过或听说过这首歌。这是一首在中国音乐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被一致公认为“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但有些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是怎样产生的?小小的一首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01
1979年,张瑜和郭凯 *** 演的《庐山恋》轰动一时,那蜻蜓点水的一吻,让无数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为之迷醉,但也引来了各种媒体的口诛笔伐。
34岁的词曲作家傅林创作的歌曲《小螺号》,使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的程琳从一个二胡演奏演员转变为一个歌手,却受到主流媒体的点名批评,认为这首歌是受了港台靡靡之音的不良影响。
1979年10月,43岁的画家袁运生在北京首都机场创作了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由于大胆画入了三个裸体沐浴的傣家少女,因而使这幅壁画饱受人们好奇和质疑的目光。
当年《大众电影》第五期的封底上只是刊登了一张接吻剧照,居然在社会上弄出了轩然 *** 。
而在文学界,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一方面荣获了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一方面却正在被当地媒体大加挞伐,天津作家蒋子龙的心情在赞扬和批判中有如坐过山车……
可以说,1979年和之后的几年中,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先锋的创作与守旧的教条互不相容,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而歌曲《乡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产生于1979年末。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有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电视导演,叫马靖华。
马靖华
他的作品往往是自己写脚本、自己导演、自己担任摄影师、自己撰写解说词并且自己担任片中插曲的歌词写作。他的纪录片突破了以往纪录片单纯描述景物或者单一线索平铺直叙的模式,突出了以人文色彩的和谐作为主轴线,营造出独具匠心的文化氛围,这样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
从1978年起,马靖华开始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拍摄长江源头和上游的风光。这次拍摄的素材,之后被编辑制作成两部电视风光片:《岷江行》和《三峡传说》。赵忠祥由于在片中担任解说,曾有一段时间随同导演马靖华一起在长江拍摄。
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记录了长江三峡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有关长江的地理、历史、文化知识等内容以及沿岸独特的民俗和神话传说。这部风光片由马靖华自编脚本,自己导演,自任摄影,自撰解说词,并担任片中插曲的歌词创作;由著名作曲家张丕基担任片中的配乐和插曲的作曲。
到了1979年12月份,电视片《三峡传说》基本制作完成,只差为片子配音乐和插曲。
按照拍片的计划和要求,在插曲《你好啊,峡江》之外,另一首插曲是女高音独唱歌曲。表达了长江在流到秭归,来到了“生长明妃尚有村”这个奇妙的地方,不免发出对我国一位奇绝女子王昭君的思念,从艺术角度上反映出王昭君在离开故乡、远去长安时对于乡土的依依恋情。在电视片中的画面上是一个古装美人,在山青树茂、水碧花红的峡江上广舒长袖,独抒胸怀。第二首插曲就是在这时配唱的一首歌。
张丕基
其实这首歌导演马靖华已经写好了歌词,作曲家张丕基也谱好了曲,这首歌叫《思乡曲》。歌词是这样的:
雁南飞,人北往,山中的小路多迷茫。
离别了可爱的村庄,抛下了童年的梦想。
何日才能再相见,生我养我的家乡。
一片思乡的情意,飘向那遥远的地方。
叶儿落,秋风凉,离乡的人儿心惆怅。
难分难离难上路,再把家乡望一望。
愿你山色春常在,河水清清花儿香。
愿你多情常托梦,别让亲人思断肠。
何日才能再相见,生我养我的家乡。
一片思乡的情意,飘向那遥远的地方。
对于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中插曲的创作,马靖华曾在访谈节目中谈到,当时想创作出一首能在听众中广泛流传的歌曲。为此,在选择演唱者的时候,马靖华和张丕基都希望能找一个听众最喜欢的歌唱家来演唱。而在当时的歌唱界,听众最喜欢的歌手非李谷一莫属。
就这样,当时在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的李谷一接受了马靖华和张丕基的邀请,走进了为《三峡传说》配唱的录音室。
02
李谷一,女, 1944年生于昆明,祖籍湖南长沙。
李谷一
1959年,15岁的李谷一就读于湖南省艺术学院舞蹈专修科,学习舞蹈。由于全国遭遇了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原定为三年的舞蹈课程,李谷一只学了两年,学校于1961年被迫下马。随即,17岁的李谷一被湖南省花鼓戏剧院选中,进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开始了她十多年的戏剧生涯。1964年,20岁的李谷一因主演首部花鼓戏电影《补锅》,使李谷一在戏曲界一举成名。
1967年,李谷一师从比她年长四岁的金铁霖教授,开始学习声乐,专攻民歌演唱,并先后得到声乐教育家沈湘、郭淑珍等名师的指导。
1974年,时年30岁的李谷一通过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审听后推荐,在中央乐团经历了前后三次的反复考试,最后经国家文化部批准,被中央乐团录取,成为中央乐团的独唱演员。
到了北京,进入中央乐团后,李谷一又向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渝(京剧电影《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扮演者)、齐淑芳(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常宝的扮演者)、高玉倩(京剧电影《红灯记》中李奶奶及京剧电影《平原作战》中张大娘的扮演者)、李维康(京剧电影《平原作战》中小英的扮演者)等名家学习京剧的行腔、吐字和京剧唱段;而“在西洋方法上,有周小燕、黄友葵老师给我上过课。”李谷一回忆道。
不断地学习使李谷一的演唱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79年12月21日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李谷一开始为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录制插曲《思乡曲》。
这时,时针已指向午夜,录音室里灯火辉煌。刚刚录完《思乡曲》的李谷一站在一旁心情复杂。单就个人的情趣来说,她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容纳了丰富的声乐技巧,感情庄严,曲调高亢,为演唱者展开广阔的音域,适合她的胃口。但这首歌曲高和寡,演唱难度大,恐怕除专业演员外,一般人唱不了。所以她凭直觉感到,这首歌很难在群众中传唱。
尽管词作者马靖华、作曲张丕基、演唱者李谷一三个人都是业内翘楚,创作上也很尽心尽力,但导演马靖华听到歌曲《思乡曲》的小样之后,却感觉与电视片搭配的效果并不甚理想,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不希望这首插曲有那么多的声乐技巧,那么艺术化,只希望歌曲简单,朗朗上口,容易让群众跟着唱,即使不懂歌唱技巧,也可以轻松唱出来。所以配唱录制刚刚完毕,录音棚里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这难道是歌唱离别故乡的感情吗?太激烈了。我需要的是轻柔的、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马靖华说,并希望对歌曲进行修改。
而作曲家张丕基则埋怨歌词写得不顺溜,很难谱曲。此时他正患重感冒,并且已是五易其稿,“几乎没招了”。听到马靖华的话,一副毫不妥协的神情:“我情愿不要音乐,也决不修改!”
李谷一刚刚唱完这首歌,自认为这首歌除去她和某些专业演员,别人一般唱不了,这不能不算做是个遗憾,所以认为导演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李谷一向作曲家说:“老张,再写一个吧。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保证给你唱好。”
最后,大家经过连夜反复商讨,节目组采纳了时任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宋培福和当时的总录音师曾文济的建议:词曲都推翻重写,由编导马靖华改写歌词,作曲家张丕基重新谱曲。李谷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是个音乐小组,有六个人,我们就说,能不能写一首区别于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一种旧有的写作方法、歌唱方法,写一首琅琅上口的,群众一听就喜欢听,一听就能唱的歌曲。”
这时,指针已指向凌晨3点。于是,李谷一返回了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赶写歌词;张丕基回家休息,等词写好后重新谱曲。
辛苦的夜晚,短暂的宁静。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一次重写,竟导致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 *** 。
第二天早晨7点多,张丕基还在酣沉的睡梦中,就有人来敲家门,是剧组把马靖华连夜赶写好的歌词送来了。睁眼一看,7岁的小女儿把一张纸放在床前。他匆匆浏览一遍,感觉很顺。这一稿,把歌名从《思乡曲》改成了《乡恋》。歌词的内容,是写王昭君离开家乡秭归,踏上漫漫的和亲路。深情的王昭君,一步一回头。家乡的山啊家乡的水,从此告别江南路,终生胡马依北风。歌词把秭归的山水幻化成为昭君心目中的亲人: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我的情爱,我的美梦,
永远留在你的怀中。
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
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心里萌动着创作的冲动,“首先这歌名就好——《乡恋》;其次处理方法也好,用拟人的方法,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土的依依恋情。” 张丕基靠在床头轻声地哼吟。他这次灵感来了,变得有些身不由己,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反常态地从心中流淌出松弛的、平易的、低回的旋律。于是他飞身下床,来到办公室,曲子一挥而就,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谱好了这曲《乡恋》。
张丕基谱好曲子后,立刻交到导演马靖华的手上。马靖华惊异地说:“呵,这么快!”作曲家说:“词顺就谱得快。”两人相视而笑,昨夜的一场争论已经释然。
03
至于创作的手法,张丕基说,他给《乡恋》谱曲的定位是要“洋”一点,用的是“探戈”曲式;而在配器时运用了当时国内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下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乐器在曾经都是禁用的。工作人员最后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的国内第一位电吉他演奏大师陈志。
另一方面,他们当即派人前往中央乐团,把歌谱送到李谷一的手里。李谷一拿到新的歌谱,与《思乡曲》相比较,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另一种境界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谷一说,“这首歌主要描写古时候的一个美人王昭君,离开自己的故乡秭归。她离开故乡几千里,不像现在我们一火车或者一飞机就到了。我拿着歌谱一看,马上情绪就进去了——我是从湖南到北京的,故乡的离别之情以及伤感什么的,这个都有。那时候(从湖南到北京)坐火车要坐28个小时,我不是慷慨激昂地雄赳赳气昂昂离开的,而是哭着离开湖南的。回想着故乡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情,那种情感就融在歌里。所以《乡恋》这首歌我是用轻声的感觉来唱它,因为它带有情感。”
1979年12月23日晚,北京瑞雪纷飞。
位于复兴门外大街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内,米黄色的天花板和深褐色的墙壁散射着柔和的灯光。李谷一站在房间的一角,穿着一件绛紫色的毛衣,身段轻盈,举止从容,而脸色略显疲惫。当弦乐器和电吉他奏出过门的一刻,大家都屏住呼吸。人们担心的是,李谷一接到歌谱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毕竟太仓促了——她能够表达出导演和作曲家所期待的要求吗?
这时候,李谷一唱了:“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真挚、委婉,充满深情,平白如话;轻盈如行云流水,婉转似深情倾诉。导演所规定的情景,作曲家所描绘的意境,都被她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得比想象中的更好。那缠绵悱恻、不绝如缕的乡思,那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的离愁,感人肺腑,撼人心弦。没等曲终,她已是泪流满面。
当乐曲结束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如痴如醉。张丕基看到了李谷一眼中的泪花:“你哭了!”李谷一回答:“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
而导演马靖华竟然忘了发出指令关掉录音机,以至于把张丕基和李谷一的这两句对话也录了进去。直到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保存的歌曲《乡恋》的母带中,仍然保留着这两句话。
多年后,李谷一告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记者:“歌曲《乡恋》所述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艺术境界,歌曲所倾诉的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乡思打动了我,所以演唱起来非常动情,一气呵成。”
当年的最后一天,即1979年12月31日的晚上8点左右,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全国的观众按照惯例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观看美国科幻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然而短暂的广告过后,大家没有等到《大西洋底来的人》,却等来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而《乡恋》这首歌也随该片一起播出。
有些观众没有看到心目中的“麦克•哈里斯”,失望之余而离开了电视机,从而错过了一个见证历史时刻的机会。而仍在坚守的观众,当听到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的歌声出现时,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被她的歌声所感染。听惯了她明丽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突然听到她“含着嗓音唱歌”,大家既惊讶又惊喜。有一个女工小声说,“李谷一唱歌怎么跟说悄悄话似的。”她的话无意中道出了这首歌“轻声”、“气声”的特点。
放眼全国,上海总是站在时尚的最前沿。而随着《三峡传说》的播出,上海人也是最敏感的。
就在第二天,即1980年1月1日元旦,上海的《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里面的歌曲十分优美动听,得到大家的喜爱。之后,人们便四处打听和寻找这首歌。
就在人们四处打听和寻找这首歌的时候,1980年2月,歌曲《乡恋》入选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当时的《每周一歌》栏目,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18点到18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的影响力特别大,耳目一新的词、耳目一新的曲、耳目一新的配器、耳目一新的演唱,霎时让《乡恋》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
与此同时,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把《三峡传说》中的配乐、插曲,包括歌曲《乡恋》录制成唱片、磁带公开发行。短短的几个月,唱片、磁带销量数以十万计,无论是在热闹喧嚣的大都市,还是小城镇,《乡恋》迷人的旋律和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总不绝于耳、“声声”不断。张丕基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排队买东西时都在哼唱这首歌。
而有谁知道,随着《乡恋》的流行,李谷一却从“歌坛新秀”一下变成了“黄色歌女”,演唱《乡恋》却变成了罪孽,以后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
04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一般来说,歌曲的词要写得很革命,曲要写得很响亮,而描述思乡、离情的歌曲基本没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像“恋”、“美梦”、“情爱”这类表现人们心灵最软处的歌词,几乎没有音乐作品去触及;而在歌曲《乡恋》里,却把这些让当时的人们脸红心跳、如春心萌动的词汇都一起在这首歌中迸发了出来。此外,在谱曲时,《乡恋》也不再是过去 *** 的四二、四四拍的机械硬节奏,大量的休止符、切分音被不断运用,“探戈”的曲式以及柔美婉转的旋律使《乡恋》在当时的歌坛让人耳目一新。而在演唱中,李谷一更是加入了“轻声”和“气声”,情到深处的抽泣腔更加重了依依不舍的离情,使人们第一次听到一种类似于耳边娓娓倾诉式的歌唱,这与当时主流的“高强响硬”的演唱方式是大相径庭的。
在演唱这首歌时,李谷一的声音飘渺迷离,旋律优美深情,她在演唱中运用了“轻声”与“气声”结合的唱法来处理,再加上她那良好的气息支撑与咬字的精确与松弛,仿佛让人们身临其境。所以,《乡恋》这首歌一经播出,就像一股清爽的风,吹拂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让听众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美妙享受从而引发出强烈的感情共鸣。
而这种唱法,也成了后来内地流行唱法的先驱——《乡恋》开始风靡后,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唱歌时模仿李谷一轻声细语的样子。会唱的人用气托着声音唱,不会唱的人则喘着气唱,这也成了最初通俗唱法的一个最浅显的标志。而许多更年 *** 的歌手,又从李谷一的创新中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创新;更有些人专门模仿李谷一的唱法,以至于社会上经常听到“李谷二”、“李谷三”之类的称呼。所以,许多年来直至现在,李谷一是中国音乐界一直公认的内地“流行唱法”的第一人。
在当时,李谷一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乐道的一个名字。而在演唱歌曲《乡恋》时,因为在唱法上有了这一小小的创新,更使得李谷一的歌声沁入到广大群众的心底。但与此同时,这种唱法也招引来一片窃窃私语和各种非议之声。有不少的人都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走了板,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不少好心的人出来向她发出警告:“应当止步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于是,歌曲《乡恋》因为“新”的唱法而遭到了非议。因为按照当时歌唱类型的划分,这首歌的唱法,既不属于美声唱法,也不属于民族唱法,而是更倾向于港台的那种流行唱法,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是碰不得的。于是批评之声也随之而来,而非议最多的,就是李谷一所采用的轻声、气声唱法。
说到这首歌的演唱方式,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李谷一用的是“气声唱法”,一直以来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宣传中,一提到歌曲《乡恋》,就说李谷一用的是“气声唱法”,而李谷一却很认真地纠正说:“诸多听众都说这首歌用了气声,其实没有什么气声唱法,就是轻声,或者可以说半声。”
录制这首歌的时候,适逢国家刚刚提出改革开放的决策。身为一个歌唱者,李谷一认为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响应改革开放创新的召唤,也为了使这首歌更加感人肺腑,根据旋律和歌词的走向,我就尝试着用半声演唱,因为全声太过生硬了。”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李谷一每次举例说明气声唱法的时候,她提到《绒花》、提到《妹妹找哥泪花流》、提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及《知音》等歌曲的片断,但她从来都不提《乡恋》,因为《乡恋》用的不是气声,而是轻声。
本来,在此之前,李谷一已经是那个时代最有大众知名度的歌手之一;而她为多部电影配唱的主题歌、插曲,更是为广大观众、听众所喜爱,以至于在电影界有“每片必歌、每歌必李”的说法。这种由李谷一几乎“垄断”电影插曲配唱的奇特现象,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
在1979年上映的故事影片《小花》里,李谷一演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还有电影《泪痕》的主题歌《心中的玫瑰》等歌曲时,就大胆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这一突破,使我国的歌坛立即为之耳目一新,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荡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那舒缓的轻声和颤动的气声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虽有批评者认为此歌曲唱法不妥,但碍于《小花》、《泪痕》等电影属于反映革命战争的红色革命范畴题材,虽然歌曲的唱法有些创新,反感者却不好说出更多的话来,只能暗自嘀咕,无法公开指责、批评。
而此种唱法后来运用到《乡恋》中时,却情形突变。
05
那些平时对李谷一“气声”唱法嫌弃和看不惯的人,由于对她在电影歌曲配唱中频繁使用气声唱法已经“忍无可忍”,这时就更是怒不可遏了。那郁积已久的李谷一的唱法问题,在新旧观念、新旧隔阂、新旧矛盾、新旧分歧的碰撞下,统统在这首歌曲上爆发了。尽管李谷一一再坚持在《乡恋》中运用的是“轻声”,而不是“气声”,但是那些人还是把《乡恋》与“气声”唱法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于是一时间,电闪雷鸣,风雪冰雹,一齐向她袭了过来——
198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在讲话中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港台有个邓丽君,内地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2月起,《北京音乐报》辟出专栏对歌曲《乡恋》进行讨论,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虽然名义上是“讨论”,但之后便发展为批判。而仅在2月至3月间,就连续发表了11篇文章。
1980年2月10日,距离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仅剩不到一周的时间。《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了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的一首插曲》。文中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指的就是《乡恋》。李谷一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应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首歌确实是一首‘情歌’,但它表现的是对故乡的‘情’,对故土的‘情’,而不是男女之情的‘情’。”
在这篇文章里,“莫沙”全盘否定了《乡恋》的创作,称歌曲《乡恋》的创作者们“热衷于搞邪门歪道,是安于模仿的懒汉”、“缺乏民族风格,缺乏特定的时代特点,格调和情趣完全不对头,相当的不协调”、“带有浓厚的殖民味道”等等,整篇文章充满了“杀气”。如果说还有什么客气之处,只不过是没有点马靖华、张丕基、李谷一三个人的名字。
《北京音乐报》继莫沙的《毫无价值的模仿》后,又接连几期几乎整版刊登对李谷一演唱《乡恋》的争议,如《歌唱小议》中说,李谷一每段歌词要用四、五次“大喘气”,比如“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一句里就有“大喘气”三次之多,叮叮咚咚的电子鼓敲得莫名其妙,等等。
于是,报刊上开始大量刊发对《乡恋》的批评文章。
1980年三月号的《人民音乐》把主题定为《探讨当前音乐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十多位音乐界名家名人对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思潮,从创作、演唱、社会影响等不同角度谈认识和感想,自然是以批评为主,虽多为不点名,但目标明确。
此后,在持续三四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恋》的全国性大讨论始终热度不减。
这时候的争议、批评已经与电视片《三峡传说》的内容无关,而是将李谷一与《乡恋》划为等号——《乡恋》就是李谷一,李谷一就是《乡恋》。
对《乡恋》这首作品,有的说它“娇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它“格调不高,在气质情趣和人物的品德等方面都不够健康”;有的说它“很像目前海外歌星们演唱流行歌曲的路子”;也有人说“这首歌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 *** 等资本主义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是灰暗的、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就这样,一时间,《乡恋》成了“大毒草”,而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歌唱家”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成了一个不需要签证,一夜之间就打入祖国大陆的“李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1980年3月25日,针对各种批评和打压,李谷一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还是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邓丽君跟我是两码事,她唱她的,我唱我的,她唱的方法跟我完全不一样。”然而,那些反对她的人并不买账。
1980年4月,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了“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史称“西山会议”。在会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
张丕基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杀气腾腾”。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
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她在会上反驳了一些横加在她身上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和思路,并且一再地声明:“我在《乡恋》中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
可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她的辩护,而且说得很具体:作词和作曲的问题都不大,毛病就出在唱法上。甚至有人劝李谷一改变唱法,重新录一版《乡恋》,却遭到这位倔强的湖南妹子的拒绝:“如果重唱重录,改变唱法,那李谷一就不是我了,那首歌也不是《乡恋》了。”
而据张丕基回忆,在这次会议之前,某省的电视台还曾约他作曲,后来一听说“西山会议”的情况,就毁约了。
由于受歌曲《乡恋》的牵连,作曲家张丕基以及为故事影片《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作曲的王酩也受到了批判。善良的作曲家王酩曾劝李谷一“曲线救国”——先写检查应付一下,歌曲照唱。而直爽又倔强的李谷一却丝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观念:“因为我没错,我就不信唱首歌能把国家唱垮了。”
就这样,当几个高大的男人如王酩、张丕基等都写了检查后,看起来相对弱小的李谷一却依然“顽固不化,死不认罪”。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谷一的丈夫肖卓能不无担忧地对记者说:“要知道,李谷一当时的举动是多么悬呀!她真是豁出去了。”
而此后不久,1980年4月间,中央乐团的领导给正在外地随团演出的李谷一写了一封信,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就请她另谋高就,这里已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舞台了,只好请她找适合她发展的地方去。“就是说,如果再要继续这样唱的话,你就回湖南去。”李谷一回忆说。
在当时的舆论批评中对歌曲里面的打击乐也就是架子鼓也反响强烈,那个时候的架子鼓在歌曲中的伴奏还是很少有的。记得有个所谓评论家这么说:“歌曲没有革命斗志,听了容易使人意志消沉,喘着粗气,真担心上气接不上下气,还有那个架子鼓在间奏之间一阵乱敲,像在瓷器店里砸碗一样,噼里啪啦,像什么东西,糟踏了歌曲……”
06
就在各大媒体对《乡恋》的批判、声讨声中,各级电台、电视台迫于压力,或者说是为了避嫌,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歌曲《乡恋》的播放,广大群众在此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从电台、电视台收听到《乡恋》这首歌。
而面对这些批评、责难,李谷一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没有更多的时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应付这一切,因为她实在是太忙了、太累了。
当时她所在的中央乐团实行的是半独立的经济核算,乐团的开支主要依靠综合乐队的演出收入来维持。所以,中央乐团每年都有一定的演出任务。而李谷一作为全国著名的歌唱演员,这时一直随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而演出的任务却异常地繁重。一年多来已经演出了200多场,甚至曾经有过50多天唱72场的记录。
据李谷一回忆:“那时候,尽管受着批判,还要保证团里的演出。1980到1982年期间,我每场演出必唱八首歌,观众要求返场,还得加唱四首歌,总共十二首歌,相当于一场个人音乐会,而且,经常一天要演两场。为此,在那两年当中,我的声带四次出血,但还要坚持演出。当时,为了保证演出,特别是到外地,团里派位医生跟着,每天要给我注射六至八针药品。”
除此之外,她还要给电影和电视剧配唱主题歌和插曲,几乎没有一点间歇。比如,就在为电影《小花》配唱插曲的前夜,她还在秦皇岛舞台上为观众演出。她的节目整整提前了2个小时,就是为了能够赶上火车返回北京。当赶到北京的家时,已经是午夜12点了。而她在第二天清晨8点就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棚。上午录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下午录一首《绒花》,第二天上午,又搭乘火车返回。下午6点钟赶到北戴河,7点就已经在舞台上演出了。
而在当时的1980年3月,正当全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对歌曲《乡恋》进行批判的时候,她却在北京刚刚结束了演出,就一路南下到了江浙,48天里演出了45场。除了4月份在北京参加了几天的“西山会议”,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外地演出。几天前还在天津,而刚进入5月就又到了上海,接下来还要到沈阳、大连、西安等地,年末还要赶到广东、广西。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李谷一的身影。
与冷酷的打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观众对她的支持,全国各地的观众勇敢地站在了李谷一一边。巡回演出场场爆满,呼唤《乡恋》的声音更是震天动地。
记得李谷一在天津体育馆的一次演出,唱了很多歌,观众却不满足。最后,全场有节奏大喊:“乡恋!乡恋!乡恋……”要知道,当时的北京,对《乡恋》的批判正如火如荼;而此次演出的节目单上并没有《乡恋》这首歌。李谷一谢幕多次,却无法退场。最后只得应观众的要求,演唱了《乡恋》。当音乐响起,李谷一刚唱了第一句,突然,全场起立,与李谷一一起高唱《乡恋》。李谷一唱遍全国,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阵势的全场大合唱。曲终之时,全场齐声欢呼,而李谷一则是泪流满面。
从此以后,李谷一无论在哪里演出,哪怕在演出曲目中没有安排这首歌,她也会应观众的要求演唱《乡恋》。“当时,到各地演出,中央乐团节目单上不写《乡恋》,可观众不答应,不唱《乡恋》下不得台,我在返场时就场场唱这首歌。”李谷一回忆说。
进入5月份,李谷一随中央乐团赶到上海,在上海体育馆作巡回演出。人们听说有李谷一参加演出,深夜2点就有人冒着细雨排队买票。在当时,一般的音乐节目很少在体育馆里举行,因为场子太大,如果卖不出那么多票,场上稀稀落落的,现场效果就不会很好。但是那天,18000个座位的上海体育馆,全场爆满。
李谷一身穿深红色的长裙,最后一个走出来。她虽然步履轻盈,姿态优美,但是稍微用心便会看得出来,她的脸色略显疲惫,心底藏着波澜。她的歌唱得依旧动人,歌声一出,台下便悄然凝虑,针落有声。她倾吐出来的,是人们都能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真实情感。
这一次没有让观众失望,最后一个节目,报幕员报出了《乡恋》,全场欢声雷动。歌曲结束,场内人群的情绪达到了沸点,掌声如春潮一般在体育馆里激荡。像在天津体育馆的那次演出一样,李谷一多次谢幕,却无法退场。最后,她只好像运动员似的绕场一周,以答谢观众对她的一片盛情。
这种时候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乡恋》,那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又要顶住多大的压力啊!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李谷一道出了心声:“群众那么喜欢听我唱,一些权威们越批判我,我越不服气。”她又说,“我今天之所以还有勇气唱《乡恋》,主要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随后她当着记者的面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大木桶来,里面装的都是读者的来信,有七、八百封。李谷一说:“我是含着眼泪读这些信的。他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干部、老人、孩子……通过这些信给我送来了莫大的温暖和支持,给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唱的歌,流的泪,受的委屈,比起这一片像海一样的深情来,算得了什么呢?”
07
就在当时几乎所有舆论都对李谷一及《乡恋》的一致批评和批判声中,却也传出了另一种声音。《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理由二人出于职业上的敏感,暂时搁下了其他选题,准备首先采访李谷一。这次采访,不是一般地采写李谷一的成才之路,而是直接切入当时争议的焦点——《乡恋》,着重于《乡恋》这首歌曲引发的争议。
邓加荣
1980年5月,邓加荣、理由乘机飞赴上海,在上海体育馆观看了李谷一的那场“绕场谢幕”的演出,现场体会了观众对李谷一、对歌曲《乡恋》的极大热情。而当报幕员报出《乡恋》时,他们二人惊讶地对视了一下——她居然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唱《乡恋》?
之后,他们二人在上海采访了李谷一,到月末,又从上海返回北京。接着在北京又访问了许多与李谷一有过接触往来的同志,其中包括《乡恋》的作者马靖华、张丕基和《妹妹找哥泪花流》的词、曲作者凯传、王酩以及李谷一的声乐老师金铁霖等人。
经过近5个月的奔波、采访,198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邓加荣和理由采写的长篇通讯《李谷一与〈乡恋〉》。文章肯定了李谷一在音乐领域的探索,认为这与整个时代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她的唱法表明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
这篇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写给记者和李谷一的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装一麻袋”。这些来信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干部、教员、军人、教师、科技工作者、文艺界同行,什么年龄的都有,小至十几岁的中学生,大至退休的老人。
邓加荣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光明日报》火得厉害。大学生看报纸,不是一份报纸传着看,而是将报纸裁成条,大家交换着看。”
面对这种情况,《光明日报》在11月9日开辟了专栏《对“李谷一与〈乡恋〉”一文的反应》,摘要选登了一些来信,并加编者按语说:“10月8日本报第三版登出《李谷一与〈乡恋〉》一文之后,引起强烈反应,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封读者来信,现摘登几封如下。”
读者来信绝大多数是支持李谷一的,喜欢她的演唱,不同意对她的创新和突破采取压制态度。有个银行干部说:“我不晓得音乐,不知道什么是‘轻声’、‘气声’,只知道群众喜欢听李谷一的歌,只知道李谷一的歌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能给人美的享受。”有位大学生说:“我第一次听到李谷一唱《乡恋》时都呆了,真像沉浸在梦境里似的。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打动人心的歌呢!”有位中学教师说:“不允许搞‘创新独白’,只准长歌颂雅,不准演员采风,稍一离格,即为异端,这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吗?如果天天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连一首《乡恋》都要打入冷宫,甚至枪毙,恐怕中国的歌坛上,就永远只能欣赏‘大海航行靠舵手’了!”
当然,《光明日报》同时也刊登了一些反对者的来信。有人说《乡恋》只是一首一般的歌曲,“上海、天津体育馆里的狂叫,也不能拿来作为《乡恋》受群众称道的例子。几千封支持的信,也说明不了问题。”认为《光明日报》对李谷一是过分地渲染,“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称呼,叫做‘捧杀’。”
从歌曲《乡恋》一开始出现争议时算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边是报刊杂志上不时地接连出现反对与批判的文章;而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对《乡恋》表现出的巨大的热情和支持:只要有《乡恋》的音像制品就会大卖——中国唱片总公司的《三峡传说》唱片被不断地再版,并且被制成国内第一张立体声唱片发行;太平洋影音公司因为出版李谷一电影电视歌曲专辑《乡恋》,被有些媒体指其“站在反动立场”,但因销量一再突破,而使此专辑先后两次荣获“云雀奖”。
1981年11月,有人在《人民音乐》上发表长篇文章,指责长篇通讯《李谷一与〈乡恋〉》的作者(邓加荣和理由)“所获得的社会效果是运用夸大和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并声色俱厉地警告作者说,“如果按照作者所提倡的新的美的探索继续探索下去,其结果将不是实现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的音乐美的创造,而是对这种音乐美的损害。作者写作该文所表现出的作风,则是对我国优良的新闻道德美的损害。”
不仅如此,在一家影响全国的大报上,音乐界一些权威人士组织了名为《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专题论坛,连续发表了数期。期间,有不少音乐界权威人士纷纷写文章批评李谷一唱法、批评《乡恋》、批评长篇通讯《李谷一与〈乡恋〉》。有位专家写文章说:“有些歌唱演员为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对此,一些人非但不帮助人们分辨真善美与假丑恶,反而大加赞扬,似乎这才是当今中国乐坛的正宗,这就使得通俗与庸俗、轻快与轻佻、洒脱与放荡、委婉细腻与矫揉造作等混为一谈了。那些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喝彩,不仅污染了我们的音乐论坛,也会使被捧者(指李谷一)误入歧途。”
根据《文摘报》2018年4月17日转载的郭超的回忆文章《〈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中披露:“自此,《乡恋》成为‘禁歌’,电台不再播放,李谷一演出时可以唱别的歌曲,但不能唱《乡恋》。”用现在的话说,从1981年11月起,《乡恋》被彻底“封杀”了。
08
《乡恋》成为“禁歌”,依照李谷一那种直爽、泼辣、倔强的“湘妹子”性格,她的心里是不服气的,她在努力地寻找机会为《乡恋》“翻案”、正名。
《乡恋》成为“禁歌”的2个月后的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那时还没有“春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 *** 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 *** 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虽然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但为《乡恋》正名的努力却没有成功。“后来是国家主席 *** 同志来了,听完笑眯眯走了,未置可否。”李谷一回忆道。
1982年6月,人民音乐出版社曾经发行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书的内容犹如书名一样,讨论了那时候歌曲的意识形态,什么是黄色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叫做精神污染?
关于所谓的“黄色歌曲”,书中提到,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等。”
于是,这本书很快就派上了用场——用《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里对黄色歌曲的定义来衡量,歌曲《乡恋》几乎全部符合黄色歌曲的标准。
就这样,歌曲《乡恋》被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3年的除夕。而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则成了《乡恋》解禁的日子。
09
时针回拨到1983年,那一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电视春节联欢晚会”,这届春晚可以说是为后来的春晚奠定了基本形式。那时候的春晚舞台小,与现在的春晚不同,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距离很近,因此互动也更多。
黄一鹤
当时,在筹办这届春晚时,作为全国最有大众知名度歌手的李谷一,自然成为晚会总导演黄一鹤的邀请对象。但是,由于春晚演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李谷一在深圳有演出任务,所以,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并不同意她参加此届春晚。后经过协商,黄一鹤作出了“在春晚结束后,以警车开路接送机场,不影响李谷一大年初一登上深圳舞台演出”的承诺,中央乐团这才答应李谷一参加央视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
那时,《乡恋》是受批判的禁歌,所以在晚会的节目单中,李谷一演唱的曲目中并没有《乡恋》这首歌。在这届春晚,李谷一成了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是《拜年歌》。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李谷一在台上一出现,观众就开始打电话点播《乡恋》。不一会,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晚会总导演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
这让黄一鹤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黄一鹤回忆说。
当时,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也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端着盘子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这些点播条之后摇了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点播《乡恋》的,吴冷西看了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
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不时掏出手帕擦汗。“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握了一下拳头,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
根据李谷一的回忆,对于吴冷西没有当即拍板,而是考虑了许久,她非常理解他的顾虑,“这首歌正被批判,如果让我唱了,他这个广播电视部部长可能要掉乌纱帽的。”
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兴奋极了,他是知道吴冷西在冒着多大的危险的,但这时已顾不上太多了。黄一鹤赶紧通知准备播放,却发现现场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人员,哪里有《乡恋》的伴奏带。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多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回来了,跑了一头汗。
在晚会上,李谷一在节目单上被安排演唱了6首歌曲,其间临场又外加了两首对唱歌曲,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其实我当时唱得满头大汗,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很老的剧场,非常小,非常热。”李谷一回忆说。
当一个个电话打爆后台的时候,李谷一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此时正在台里被人要求与袁世海演唱京剧。而当担任主持人的姜昆播报由李谷一演唱《乡恋》时,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她所熟悉的歌曲《乡恋》的伴奏音乐已然响起。多年的酸甜苦辣一下子涌上了她的心头——经过了多少磨难和委屈,虽然以前也曾在舞台上应观众的要求演唱过《乡恋》,但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今天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乡恋》了,于是,熟悉的旋律脱口而出:“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演唱中的李谷一百感交集,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1983年春节后,全国各地的许多观众写信给电视台,称这台晚会是“人民自己的”,而播放这台晚会的电视台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在总导演黄一鹤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用了“人民”两字,这是最高的评价。
从本质上来讲,春晚的演出气氛是讲究喜庆和合家欢乐,从而决定了其宽容和包容的演出性质,所以当时还属于禁歌的《乡恋》能够在春晚演唱,能够在春晚被“解禁”,现在看来,虽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得到了证明,而《乡恋》的“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这一说法,经过时间的沉淀,也已被中国音乐界所公认。
就这样,针对歌曲《乡恋》和李谷一的争议与批判一直持续到1983年的下半年,才逐渐平息。从1979年年底演唱歌曲《乡恋》开始,到1983年下半年《乡恋》走出风波,李谷一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这样一首小歌,批判四年之久,真是罕见。”
10
综合当年报道,对于《乡恋》这首歌,一开始只是争论,后来就变成了批判,焦点针对的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一种新的演唱方式、新的文艺形式,而在此背后,则体现了国内当时在意识形态里新旧思想之间的激烈斗争。用李谷一自己的话说:“(《乡恋》这首歌)歌不大,唱法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里头灌注了新的思想内容,所以在当年来讲叫‘捅了娄子’了,动了那一根‘筋’了,(体现了)新旧思想的一种对抗:一个拽回去一个拽前进。”
伴随着歌曲《乡恋》一路走过的风风雨雨,李谷一总结道:“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看来《乡恋》或许是一首小歌,但在当初它起到了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碑的作用。”她又说道:“《乡恋》真的不是一首歌,它成为了一个‘事件’。”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1979年和之后的几年中,文艺界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先锋的创作与守旧的教条互不相容,用著名词作家乔羽的话说,“《乡恋》的争论是文艺界的‘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当时的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李谷一与《乡恋》风波,正是体现这一交锋的标志性事件。
随着“革命意识”这一简单命题的打破,不仅仅是音乐领域,而是在整个文化领域,都开始大步朝着“以人为本”、“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的新时期迈进。尽管这些领域的思想解放与《乡恋》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文化领域的思想革新是历史的必然。《乡恋》的创作革新,恰恰预示着文化领域逐渐进入了开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