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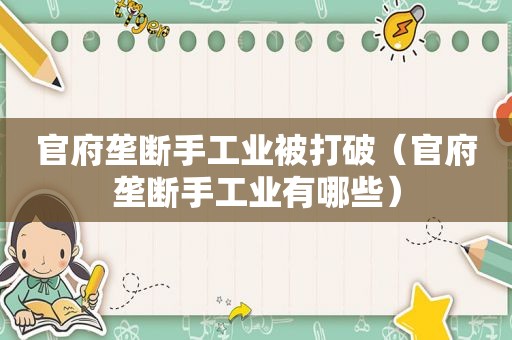
我国书籍最早都是官府典籍,后人称为官书。官书至迟殷商就有,到西周进入繁荣时期。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出现了不属于官书的经籍与子书。总的看,先秦书籍的出版学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点:不向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篇籍无定本。先秦书籍这三个特征,源于官书制度,影响及于经籍与子书,到汉代才渐见消失。官书作者为何不在自己作品上署名?原因盖在,当时社会上尚未形成将作品在精神上或名义上视为作者己有的观念。到秦汉以后,社会上有了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观念,作者署名才渐成习俗。在官书制度下,“私门无著述文字”[1],所有作品属官府所有,不归作者己有,章学诚说是“立言为公”[2]。既是“立言为公”,就不能产生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观念,因此作者不署姓氏。官书的读者可能知道作品撰人的官职,如大史、大卜、诅祝、医官等,一般不知道具体作者为何人。官书不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传统观念,不能不影响后起的经籍与子书。需知在不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社会上,修订作品无需征得作者同意,不经作者而修订作品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也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其结果,篇籍无定本就难以避免。凡经一次修订或增删,修订后的新本就取代旧本传承后世。不断修订,就是不断以新本取代旧本传承后世。先秦作品在汉代以前大都没有定本,就是因为在不向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的社会上,作品流传时被不断修订的缘故。经过不同时代多次修订而流传到汉代的先秦作品,再也不可能是某一人的作品,只能是某学派或某群体的集体著作。这类集体著作,在同一作品中存有不同时代的文字,作者是不同时代的许多人,就是学界常说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结合不向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的历史环境看,出现“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正常现象。以后,有人断言是“伪书”。其实,主要是用秦汉以后才有的社会观念,即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观念,去衡量长期流传在秦汉以前的作品。这样对待先秦古书,岂止是误解而已。为探讨出版诞生,下面仅说明先秦书籍不向公众传播。
首先,官书不准公众传播。
大致以春秋为界,春秋以前所有书籍都是官书;从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出现官书与非官书并存的局面。一般说,书籍作为媒介工具都可以公众传播。官书不向公众传播的根本原因,不在书籍自身,而在官书制度。
官书制度源于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大概起于三代,以西周为鼎盛。西周的经济制度是无所不包的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3],就是无所不包的国有制。在这种国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君权。君权除了统治与支配政治、经济、军事,也统治与支配文化。为君权掌管文化的,是巫、史、祝、卜等文化官员。鉴于巫史官员执掌并创造文化这种历史现象,一些学者称之为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官府全面垄断文化。春秋以前,所有学校都是官学,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官学之外,从未有民间私学。官学由官府执掌。执掌国学的机构有大司乐、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等,执掌乡学的机构有大司徒、乡大夫、乡师、州长等。因此,官府机构就是教育机构,教育机构都是官府衙门,所谓“政教合一”。教师都由官员兼任,没有不是官员的教师,亦官亦师,所谓“官师合一”或“以吏为师”。在官学中受业的学生都是贵胄子弟,学习目的是世袭做官,民间子弟不准入学。清人章学诚说是“官守学业(守,官员职守;学,师长传学;业,弟子受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作文字。”[4]凡此,就是所谓“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结果,必然是“书在官府”。天子将包括典籍在内的典章文物一概视为己有,史官就是天子的典书之官。这样就产生了官书制度。
官书制度,是按礼乐等级垄断书籍的制度。春秋以前,除了官府典籍,再没有其它书籍。天子是典籍的最高垄断者。天子按礼乐等级,向诸侯分配包括典籍在内的典章文物。例如西周初年,伯禽封鲁,成王的封赠除有土地、人民、财物等,还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5]“祝、宗、卜、史”为文化官员;“典策”为典册或典籍,就是现在所说书籍。伯禽是摄政王周公之子,所以成王封赠的典章文物,比康叔封殷、唐叔封夏要多。[6]当时,拥有什么样的典籍与典章文物,代表贵族等级的高低,是贵族的一种特权。贵族从维护礼乐等级与自己特权出发,不准自己的典籍随便复制,更不准公诸于众。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7]。从这件事可知,吴国自泰伯立国数百年后到季札之时,仍不拥有鲁国那样完美的诗乐。公元前540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8]从这件事可知,晋国虽与鲁国同为姬姓诸侯,然而拥有的典籍远不如鲁国丰富。鲁国的诗乐与典籍经过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仍不能流传到吴国、晋国呢?吴国、晋国为何不能拥有鲁国那样的诗乐与那么多的典籍呢?根本原因在礼乐制度。鲁国的诗乐与典籍是天子按礼乐等级封赠的,鲁国不能将它们复制后随便赠送别国,其他诸侯也不能随便复制而据为己有。允许随便复制,就能公开流通。若是如此,季札与韩宣子何必千里迢迢到鲁国“观周乐”或“观书”呢?先秦官书,在官府产生,在官府使用,在官府修订,在官府传承,总之由官府垄断,不准公开流通。秦汉以前公开流通的官书,大概只有《诗》《书》。《诗》《书》是官学中人人要学的教材,如此才成为例外。在数量惊人的官书中,《诗》《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先秦官书是三代以来中华文明的结晶,成就卓著,数量惊人。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三部分共279家,4186卷,大都为先秦官书或直接从官书演变而来。“数术略”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9]又说:“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10]数术之书,本是史卜之官的职务用书。汉代所谓“旧书”,就是史卜之官传承下来的古书。官书中的典章文献,由于诸侯不断私自毁灭,很少能留存下来,故而只有少量著录在“六艺略”。官书传承到汉代,屡经社会变故,散佚很多。尽管如此,从《汉书·艺文志》仍可约略看出先秦官书数量之多。官书著作在政治学、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医药学、天文学、数学等许多领域,为我国传统学术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汉以前,官书不准公诸于众,从未进行公众传播。章学诚《校雠通义》在说明先秦为何没有目录著作时说:“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11]其实还有另一原因是,因为书籍尚未公众传播,客观上不可能产生目录著作的需要。有人以为春秋时“铸刑鼎”[12],就是典籍公诸于众的开端,这里存在误解。铸刑鼎,仅仅是将某一种刑书铸于铁鼎,公诸于众,其用意是表示按刑法办事的一种决心。刑书属于刑典。将一种刑书铸于鼎是有可能的,将刑典全部内容铸于鼎就是不可能的。刑典为六典之一,将六典全部内容铸于鼎更是不可能的。将铸刑鼎解读为典籍公诸于众的开端,或允许典籍公开流通,未免无限夸大。需知按周代法度,刑法是不能公诸于众的,因此孔子用“失其度”与“乱制”如此严厉之词[13],批评晋国铸刑鼎。自铸刑鼎后,赞成刑法公诸于众的只有法家一家,多数仍不赞成。多数不赞成,所以刑法并没有因铸刑鼎而都公诸于众。春秋铸刑鼎的作用主要是引起了律法公诸于众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将律法“颁行全国”之事要到汉以后才有。《荀子·荣辱篇》指出,有关官员谨遵前代传承下来的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王念孙注:持,犹奉也,言官人百吏谨守其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父子相传,以奉王公也。)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14]从“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可知,官书到战国后期仍不准自由复制,仍不能公开流通。
当史官文化瓦解而出现文化下移时,周文化主要是下移各地诸侯,周典籍也主要是下移到诸侯手里。从孔子、墨子都读过官府典籍看,大概从春秋后期开始,官府典籍允许某些民间著名学者阅读。流布到民间的官书,并非没有,数量很少。医书较早从官府流到民间。汉以前,民间称医书为“禁方”[15]。从资料看,汉以前的民间医书只在医家内部秘密传承,没有公开流通。秦以前流布民间的重要官书有《周官》。可是《周官》在民间传承情况,在汉代就一无所知,可见《周官》在汉以前是秘密传布。尽管官书并未公诸于众,从历史发展看它是中国书籍的源头,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丰硕成果。官书的卷面版式、装帧等经验,都为后代继承并发展。毫无疑问,没有官书就不能有经籍与子书,也不能有秦汉以后的文化繁荣与书籍繁荣。只是因为官书在汉以前没有公众传播的缘故,真实面目被历史尘埃深深地掩埋起来,因此今人怀疑其真假,否定其存在。这是令人惋惜的事。
其次,经籍与子书在民间师徒范围内代代传承,是书籍从官府垄断走向公众传播的重要步骤。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年间书籍领域最具革命性的事件是经籍与子书相继崛起。经籍与子书都是不受官府控制的民间书籍,是官书制度中产生的异端。最早冲击官书垄断的重要人物是孔子(前551——前479)。孔子的六经原本都是“官书”[16]。六经成为孔子私学的教材以后,就不断流向民间。因为是官学教材而流布于贵胄间的《诗》《书》,成为六经后便大量流布民间。《易》与《春秋》本是严禁外传的官府秘典。[17]孔子修《春秋》赞《周易》是将官府秘典作为私学教材,进而流向民间,最具反叛官府垄断的意义。孔子冲击官书制度的另一表现是,发展民间学术与民间著作。春秋以前,“私门无著作文字”。历史上最早又最重要的私家著作,是经籍中的传记作品。儒家传记作品,都肇始于孔子对六经的解释,最后完成于孔门弟子的不断补充与发展。传记著作的兴起,是民间学术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孔子后的墨子,是直接论述书籍与书籍传播作用的第一人。战国年间,以诸子为代表的民间学术在与官方学术抗衡中,取得节节胜利,促使民间书籍发展壮大,进而成为有力冲决官书制度的生力军。
鉴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书籍从官府垄断走向公众传播,不可能一帆风顺。孔子的功绩主要是使书籍开始在民间师徒之间代代传承,这是一大进步。东汉范升说,《左传》“出于丘明,师徒相传。”[18]可见,汉代人还记得经籍在先秦是“师徒相传”这个事实。今天,经学史、教育史都指出,六艺与诸子在先秦都是“师徒相传”,无有例外。西汉初年以前,解释五经经文的传记大都靠口传。传记口传这件事,足以证明经籍为“师徒相传”,因为唯师徒才可能口传。孔子传授《易》与《春秋》的对象仅限于门下的少数弟子[19],连门下弟子都没有普遍传授,传授更难超出师徒范围之外。汉代学者纷纷记录了五经从孔子到汉代的师徒传承谱系[20],也说明汉以前为“师徒相传”。汉以前私学以家法为尚,是经籍或子书“师徒相传”数百年的重要原因。余嘉锡说:“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21]凡家法都按门派建立,按门派传承;弟子可以发展家法,但不更改家法;弟子一旦超出老师家法而另立新说,需另立门户,以传承新的家法。总之,有以家法为尚,便有篇籍的师徒相传。以家法为尚的“师徒相传”,篇籍流布范围以门弟子为主,很难超越门弟子的藩篱,所以具有半封闭性,尚不是公众传播。
先秦子书与经籍一样都是“师徒相传”,或以“师徒相传”为主。清人俞樾认为,《墨子》书中《尚贤》《尚同》等十篇出现大同小异的三种文本,这是墨学文本在“墨分为三”之后,分别在墨家三派中长期传承的结果。[22]墨学三家因为各有各的家法,因此同一墨学文本由三家传承到汉代时,已经是三种不同的文本。这种现象也说明,以家法为尚的“师徒相传”具有半封闭性,彼此间没有交流。如果彼此有交流,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三种文本。此外,子书大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大都成为数百年学派的集体著作,这种现象也说明子书在汉以前为“师徒相传”。古今学者一致认为,今本《庄子》三十三篇中,只有“内篇”七篇为庄子所著,“外篇”与“杂篇”共二十六篇都是弟子后学的作品。唐代杨倞指出,《荀子》的《大略》《宥坐》诸篇出于弟子之手[23]。实际上,《荀子》书中弟子后学的篇章,远比杨倞所说要多。《商君书》《韩非子》等书中,都是既有诸子自己的作品,也有弟子后学的作品。有些子书中,还可以查到诸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留下的文字。因此,清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如今所见先秦子书多数不是出自诸子一人之手[24]。从著作权看是诸子学派的集体著作。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子书在师徒间世代传承时,弟子后学为了维护家法与发展家法,或者修订先师留下的经文;或者将先师口授、遗闻轶事记于竹帛,进而与经文一起归诸家法;或者解释经言,笺注经文,日后这类文字与经文混合;或者弟子后学将自己作品与先师作品都作为家法保存,如此等等。凡此,对以家法为上的师徒相传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这样做在“立言为公”与不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社会上,不可能引起有关作品真伪的任何疑问或纠纷。[25]于是,当子书篇章通过师徒代代传承而到汉代第一次公诸于世时,里面先师文字与弟子后学的文字,先师作品与弟子后学的作品,早已混沌不分;少数或可区分,多数无法区分。汉代校书者只能将同一家的作品校理后合为一部书,再以诸子之名命书(汉以前,子书以篇为单位传承,尚未以诸子之名命书),行布于世。后人所见子书都是汉代校定的面貌,它接近先秦原貌,又不完全一样。今天从著作权看,汉代校定的先秦子书大都是诸子与弟子后学的共同著作,是数百年学派的集体著作。这是子书篇章按家法在师徒间长期传承的结果,以伪书视之乃千古冤案。
“师徒相传”的出现是书籍传播的一大进步。然而,“师徒相传”具有半封闭性,它是先秦书籍从官府垄断走向公众传播的重要步骤,也是一种过渡形式。
最后,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问世,在先秦书籍走向公众传播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先秦书籍走向公众传播的障碍,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来自社会,官书制度获得统治集团的坚决维护,如《荀子》说“三代虽亡,治法犹存”[26],这是公众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障碍来自书籍自身。为与公众传播相适应,要求书籍领域建立两种新观念:一为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的观念,另一为篇籍定本的观念。否则,公众流通秩序无从建立。建立这两种新的社会观念,并非轻而易举。战国年间活跃于官民间的诸子,成为推动公众传播的基本力量。墨子(约前468——前376)从“先王之书”[27]即官书中,首先发现了书籍媒介超越时空的传播作用,秦汉前以《墨子》赞扬书籍传播的精彩言论最多。墨子以后,孟子(前372—前289)以说诗为由,首倡“知人论世”之说,强调接受作品必须了解作者及其时代。这是从阅读接受的角度,对作者不署名这古老传统提出挑战。从资料推测,大概在战国中后期,有些子书悄悄流布到师徒范围之外。韩非(约前280—233)在《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28]所说“商、管”“孙、吴”都指有关篇章,今人不可以为是到汉代才有的那种子书。韩非的话说明,有不少子书篇章突破了师徒传承的藩篱,自发走向公众。战国末年,吕不韦仿效“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而著《吕氏春秋》[29]。荀子(前313—前238)是战国后期最活跃的思想家,在齐“三为祭酒”,[30]门徒遍天下。从《史记》记述“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可知突破“师徒相传”而自发走向公众的子书,不限于韩非所说,至少还有荀子作品,或者还有其它。战国中后期,子书在作者署名与篇籍定本这两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条件下,纷纷自发流向公众。在此基础上,吕不韦(?—前235)率领众多门人所著《吕氏春秋》于公元前239年问世[31],成为走向公众传播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折点。
出版史考察《吕氏春秋》问世,关注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作者以自己姓氏命书。或曰《吕氏春秋》,或曰《吕览》,都以“吕”命书。“吕”,代表作者吕不韦。以作者姓氏命书,《吕氏春秋》比刘向早,其中包含了作者署名的意思。它说明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新观念正在悄然形成。第二,作者初步具有以定本问世的观念。在古代,一般根据书名、序言、篇章目录、全书卷次等,鉴别是否是定本。《吕氏春秋》问世时,有书名,有序言。它的序言称《序意》,内容为吕不韦“答良人问十二纪”。历史上的作者自序以《序意》最早。这些表明作者初步具有以定本问世的观念。第三,以“一字千金”为新书做宣传。“一字千金”云云颇有抄作的意味,目的是吸引社会上读者的注意,这说明作者初步具有公众读者的观念。《吕氏春秋》问世集三种新观念于一身,即作者署名观念,定本观念,公众读者观念。这些新观念尚待完善,却为空前未有。因此,《吕氏春秋》问世是先秦书籍走向公众传播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战国末年,《吕氏春秋》集三种新观念而问世,尚属个别现象,它代表了难以阻拦的历史新潮流。总的看,官书垄断与公众传播两种势力的争斗,胜负未决,成败未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行“挟书律”,禁私学,焚书坑儒,暂时扑灭了公众传播之火。官书制度在腥风血雨的反攻倒算中,全面复辟。书籍公众传播在汉以前并未完全实现。
注释
[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页。
[2] 章学诚:“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69页。[3] 《诗经·小雅·北山》。[4]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51页。[5] 《左传》“定公四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6-1537页。[6] 《左传》“定公四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537-1530页。[7]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161页。[8] 《左传》“昭公二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226页。[9] 《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75页。[10] 《汉书》卷30,第1775页。[1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页。[12] 《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274、1504页。[13]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504页[1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9页。[15]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庆年七十馀,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 《史记》卷10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705、707页。[16]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51页。 章太炎《经学略说》:“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页。[17] 章太炎《经学略说》:“《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47页。[18] 《后汉书》卷36《范升传》。《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228页。[19]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孔子之授六经,以《诗》《书》《礼》《乐》为寻常学科,以《易》《春秋》为特别学科。故性与天道,弟子多不得而闻。” 《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孔子仅将《诗》《书》《礼》《乐》作为一般教材传授给学生,对于深奥的《易》是个别传授,犯时禁的《春秋》未纳入正式课程,仅仅是和学生谈谈而已。”《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40页。[20] 有关资料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等。[21]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管子》条。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4页。[22] 俞樾《墨子闲诂·序》:“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俞序”,第1页。[23] 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大略》《宥坐》引杨倞注。“(大略)此篇盖弟子集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宥坐)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集事,故总推之于末。”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第485、520页。[24] 举例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62-63页。) 严可均:“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谓不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严可均:《铁桥漫稿》卷8《书管子后》,《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页。) 孙星衍《晏子春秋序》:“《晏子》书非晏子自作也。盖晏子殁后传其学者,采缀晏子之言行而为也。……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孙星衍:《问字堂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7页。) 余嘉锡《古书通例·绪论》:“古书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或定著于写书之官。”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25] 引起作品真伪这类纠纷的一个客观条件是,社会上有了视作品为作者己有的观念,时间需在汉以后。[26]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第59页。[27] 见《墨子》的《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公孟》等篇。[28]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1-452页。[29] 《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30] 《史记》卷74《荀卿列传》,第2348页。[31] 据《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岁在涒潍”云云。“维秦八年”为公元前239年。【责任编辑:周小莉】
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 ),江苏武进人。中国著名编辑学家,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3年,全国十家直属中央的综合大学学报奉命复刊,山东大学《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空缺),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文史哲》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辞去学校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绝意仕途,埋头读书。1996年退休。著有《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学术著作,另有文艺学、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