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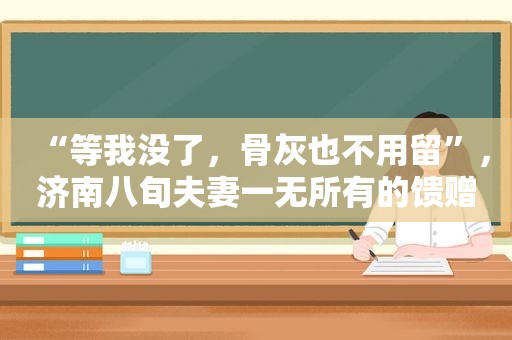
✎编 者 按
复归于无之后,爱人之间所隔的不再是生死。
2021年11月18日,5点25分。李彩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去世之前,她一直饱受着病痛的折磨。关节炎折磨着她的膝盖,癌细胞已经扩散,侵蚀了她的胃。
她的老伴,已经86岁的乔润生平静地办理着妻子的身后事——确认,签字,和相伴了50多年的老妻告别。在去世后的半个小时内,李彩华的遗体被送往了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使用。
“等我没了,也把遗体捐了,骨灰也不用留。”
乔润生很瘦,弓着背坐在沙发上,身影瘦弱的像个孩子,
“我就一点要求,就是墓碑上把我们俩的名字写在一起。”
签订遗体捐献协议后,乔润生和李彩华老人拿着证书合影
告别
一切都是按李彩华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
“要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会?要不要设灵堂?要不要留骨灰?”负责遗体捐献的工作人员问。
乔润生显得干脆,
“不要,都不要了。”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正如老人设想的一样,人生最后一站,她去的不是墓地,而是医学院的实验室。在老人身上有用的器官摘除移植后,遗体会成为医学生们珍贵的样本,这些初学医的学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告别。
在去世之前,时间和疾病一步步夺走了她的健康。在关节病变的越发严重后,她从无法走路,到慢慢无法起身。
身体一点点的坍塌下去,一切都要依靠老伴乔润生。少年夫妻老来伴,俩人相扶持着走过了五十年的金婚,伺候走了两边的老人,也养育成人了三个子女。
人生的“任务”逐渐完成了,年纪却也慢慢大了,还来不及享受生活,身体却慢慢坏了。在腿还勉强能动的时候,只要天气好,乔润生都会用轮椅推着李彩华出来在小区附近转一转。
乔润生老人翻看照片
这是一片老小区,距离不远就是济南的英雄山烈士陵园。挨着小区有个特殊教育学校,面向盲童、唐氏儿等招生。夫妻俩都喜欢孩子,就常常在学校附近看孩子们玩耍。
“有些孩子从出生就没见过光。”
乔润生说,跟着特教学校老师了解到,一个健康人的角膜可以帮助四个盲童重见光明。在无意中了解到遗体捐献后,两人去参观了遗体捐献的仪式和解剖现场。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并向遗体鞠躬致敬。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在下第一刀之前,老师会告诉学生,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30号、31号
遗体捐献后,意味着自己的身体也要被动刀子。
“不害怕。”
乔润生说,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活了大半辈子,俩人觉得生老病死是规律,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参观过遗体捐献的全部流程后,两位老人决定百年之后捐献出自己的遗体,
“就让学生去练练本领,学好了将来能救人。”
老两口的决定遭到了儿子的激烈反对。一向很孝顺听话的儿子想不通父母的做法,他还保持着“入土为安”“厚葬”的传统观念,也怕别人会对着自己指指点点,“是不是不舍得给父母的身后事花钱?”
为了做通儿子的工作,老两口用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遇到吊唁和丧葬的事,乔润生都尽可能的让儿子代替自己出面。他坚信“厚养薄葬”,生前尽孝,好过死后痛哭——一年后,儿子同意了父母的决定。
老夫妻的遗体捐献证书
2005年11月22日,乔润生和李彩华夫妻,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两个人分别成为济南市第三十位、三十一位遗体捐献者。
如今老伴儿先自己走一步,乔润生没有留骨灰,也不准备在自己走后留下骨灰——在遗体的医学价值完全利用完后,骨灰由殡仪馆自行处理,复归于无。
捐献者的名字,将以墓碑的形式存在于陵园之中。支开书页的花岗岩上面写满着捐赠者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将按照端庄的宋体,工工整整地按捐赠的年份排列。乔润生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和老伴的名字写在一起。
按照习惯,墓碑上生者的名字会涂上红油漆,去世后再把油漆洗去。
“我们是夫妻,还是要在一起。”
乔润生说,
“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谁都改变不了,但是要正确对待,能有用的总比一把火烧了强。”
乔润生在整理资料
老伴儿
老妻离开之后,家里一下子就空了。
老妻的卧室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被子没叠,在床上铺得平平整整,仿佛主人随时会再过来休息。出了卧室是一条不到两米的走廊,走廊的墙壁上还留着两排不锈钢的扶手,这是李彩华刚生病还能自己走动时,孩子给安装在墙上的。每次走过,乔润生都会想起老妻扶着扶手,小心翼翼在家里走动的样子。
这是单位集资建的老宿舍楼,老房子的格局是房间大,客厅小,以前李彩华喜欢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现在她走了,电视也不打开了,怕落灰就找了块毛巾罩了起来。
书房里,有老妻的照片;厨房,还摆着祭奠用的水果;大衣柜,还是俩人婚后不久添置的“大件”,当年千里迢迢从东北牡丹江运回来,乔润生又重新给漆了一遍。快50年的老物件了,显得还是新簇簇的……人没了,东西点点滴滴,都是影子。
昨夜凌晨两点,乔润生醒了一次。凌晨四点,又醒了一次——夜太长了,天总是不亮。有时候醒了,乔润生忍不住会去老伴的床上坐一会,有时候也能忍住不去——人已经没了。尤其是夜里,看见空的床,更添了感伤。
他是个精瘦的老头,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写字。之前常常参加一些文友的聚会,在老伴卧病在床后,生活的全部重点就转移到了照顾老伴。
乔润生和老伴的遗照合影
每天早上把老伴抱到轮椅上,把轮椅推到客厅后,再从轮椅抱到沙发上。李彩华中午要午休,吃过午饭后,乔润生就再把老妻从沙发抱回卧室,午休过后再抱回来。一直等吃过晚饭,老伴在沙发上看电视到9点,再重新抱回卧室。
乔润生年轻的时候就瘦,随着年纪增大肌肉量减少,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肉包裹在细瘦的骨头上。虽然李彩华体重不到100斤,但对于乔润生来说还是力不从心。每一次挪动,都需要两个人共同配合的力量。起身前,先用一根绳子绑在床头上,李彩华拽着绳子挪动上肢,乔润生再抱着她,一点一点地将妻子的身体挪动到轮椅上。
不到100平米的房子,一次来回的挪动就像一次“长征”。这样一天四次从卧室到客厅的“长征”,乔润生抱了十二年。
每天夜里李彩华休息后,是乔润生一天之中的“自由时间”。他会做三个小时左右的文件整理、誊抄以及写作。由于俩人休息时间不一致,为了不吵醒老伴,李彩华住主卧,乔润生自己单独住对门不到十平方的小卧室。为了方便照顾老伴,李彩华床头上有个呼叫器,另一头放在乔润生床头。夜里醒了,李彩华就摁一下呼叫器,乔润生也摁一下告诉妻子自己已经醒了——起床给老伴翻身、喂水,或者喂药、 *** 、抱着上厕所。一晚上总要醒三四次。
现在晚上没人再叫他了,乔润生还是习惯性的把呼叫器放在枕头边上,晚上醒了,下意识的去看看呼叫器响没响。
“年轻的时候她照顾我,年纪大了我照顾她都是应该的。”
乔润生说,妻子跟着他没少受苦,妻子是东北人,跟着他来到了山东。年轻时日子艰难,自己曾经当过服务员、工人、在农场修过果树,妻子也一直跟着自己操劳。年轻时他在铁路工作,经常出差几天不回家,妻子要上班,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辛苦可想而知,“跟着我,她没享到福。”
两人年轻时候的照片
一缕香味
在李彩华病情严重后,今年6月份,乔润生终于听从孩子的安排,请了一位保姆。
保姆胡方芹手脚勤快,做事干净利落,但在照顾李彩华的时候,乔润生基本不让她来帮忙。
“早饭都是大叔做。给大姨煎鸡蛋、煮麦片、海参。我就做个午饭,抱大姨的时候帮一把。”胡方芹感叹,虽然李彩华一直卧病在床,但是身上一点异味也没有,“大叔照顾的可好了。”
对于老两口捐献遗体的决定,胡方芹不能理解,但觉得“真是很感动,我回去跟亲戚邻居都说过这个事。”胡方芹想了想,双手在膝盖上拍了一下,
“咋说呢,就是真挺感动。”
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感情令人动容。乔润生把老妻的一张小像摆在卧室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洗手上香。妻子生前喜欢干净,乔润生就给妻子燃上檀香。
“买了十盒檀香。”乔润生觉得芭兰香的味道更好,就托孩子再去网购几盒,“她肯定也更喜欢这个香味。”
乔润生为妻子上香
虽然没办葬礼,但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还是按照传统送来了帛金。乔润生手写了一封感谢信,又把帛金悄悄塞到信封里,带着两瓶酒送还给了邻居。遗体捐献后民政部门会发放一点慰问金,乔润生拒绝的有点生气:
“我不能要,葬礼没花钱,我更不能靠着这个挣钱。”
留一点用处
乔润生盼望着,老妻的眼角膜可以捐给盲童,让黑暗里的孩子重见光明,而这也一定是妻子的心愿。
“我有时候看着小区里玩的孩子就想,他们长大了说不定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或者人物,给国家做贡献。”
乔润生说,妻子离开后,他把妻子的旧衣服洗干净捐到了小区的旧衣回收处;能用的物品也基本捐送;妻子之前常坐的一个旧沙发放到了小区楼下,供附近玩耍的邻居休息。
排解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书、抄《黄帝内经》、整理自己留存的资料。退休后乔润生一直致力于研究民俗文化,书房里有整整三面墙的民俗研究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手写了一本关于民俗的书籍和一部民国纪实小说,孩子给他打印了出来,他一直想着有生之年能够出版出来,
“人活一辈子,唯一能留下的就是文化。我什么都不留,也不要,就想着能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这也算一点用处。”
乔润生手写的部分文稿
乔润生说,人去世后,一切都会归于虚无,自己若是能留下一点资料供人参考,也是“老有所为”。
在跟记者聊天的时候,乔润生会偶尔陷入短暂的停顿和沉默。一个把身后事都已经看淡的老人,还是觉得人生会有遗憾,
“她走的早了点。就算是在床上不能动,也是个伴。”
乔润生没有给妻子烧纸钱,也拒绝一切“世俗”的纪念仪式,虽然他不相信会有来生,但是依然想着自己会用另一种方式,和妻子永远在一起——在不久之后,刻着妻子名字的纪念碑会静静地立在陵园中,在那块碑上,他的名字就刻在旁边,空出来的只有死亡日期。
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张琪
来源: 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