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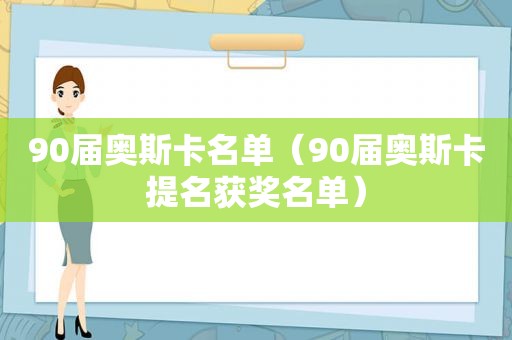
对90岁的奥斯卡来说,有些事情在发生变化,又有些事情没有变。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落下帷幕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水形物语》压倒呼声颇高的《三块广告牌》,最终摘得“最佳影片”大奖。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它具备了一切我们可以预测的、奥斯卡喜闻乐见的元素,比如女性主角、黑人角色、弱势群体、包容一切的爱......
奥斯卡的政治正确越走越圆熟,以致于当我们看到某部电影时,就知道它是否为奥斯卡定制、以及它得奖的企图心有多大。但对于一个90岁的顶级电影奖项来说,我们内心总觉得,奥斯卡不仅仅如此,它似乎应当具备更多的开拓性、更多的生命力。我们用这篇推送,跟大家聊聊奥斯卡,以及它背后折射出的电影文化现状。在本文作者看来,奥斯卡的生命力,不在于这些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套路,而在于那些更敢于表达人的复杂性、更有真诚表达欲的创作上。
撰文|吴泽源
(影评人)
第90届奥斯卡奖,在昨天揭晓了战果。奇幻片《水形物语》战胜《三块广告牌》,获得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大冷门。
其实大家的惊讶,确实有道理,因为《三块广告牌》里面内心纠结的人物、充满两难困境的剧情矛盾,和尖锐中略带温情的整体气质,都一直是奥斯卡评委最爱的特点。而像《水形物语》这样略带cult气质的奇幻片,则很少会成为奥斯卡评委的心头好。如果把《水形物语》与《三块广告牌》放到2016年之前的任何一年进行竞争,那么在一百次对决里,《三块广告牌》至少能赢九十次。
两大热门《水形物语》与《三块广告牌》
但在进入特朗普时代后,奥斯卡的口味正在发生变化。自由主义价值所遭受的冲击,和好莱坞内部爆出的重重黑料(韦恩斯坦、凯文·史派西的性丑闻,和伍迪·艾伦的疑似性丑闻),使得奥斯卡奖在这两年里,愈发地强化着它的政治属性。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策,奥斯卡奖做出的回应,是加倍地鼓励将少数/弱势群体作为主角的电影;而对于自家起火的后院,奥斯卡奖的对应策略,是鼓励那些“德艺双馨”的影人,并将有道德疑点的影人拒之门外。
于是对于这两年的奥斯卡奖来说,它固有的叙事脚本,也在被自我颠覆。《月光男孩》与《水形物语》都是以黑马的姿态,登顶最佳影片,但我们也没必要入戏太深,认为这是《爱乐之城》和《三块广告牌》的失败。因为归根结底,奥斯卡颁奖典礼只是好莱坞内部的一场动员大会。如果真的以为它的颁奖结果能够改变现实,让世界变得更好,就有些天真了。
“政治正确”vs“匠人精神”,
获胜的似乎总是前者
每年的奥斯卡竞争,都会有一个清晰明快的中心矛盾,而在大部分年头里,这个矛盾,都是“政治正确”与“匠人精神”的对决。毕竟对于好莱坞影人来说,它们是最能为他们带来自我实现感和虚荣心的两种特质,因为前者证明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后者则显示出他们对艺术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奉献精神。
我们能回忆起很多出这样的脚本:2010年的《拆弹部队》vs《阿凡达》,2014年的《为奴十二年》vs《地心引力》,2016年的《聚焦》vs《荒野猎人》,2017年的《月光男孩》vs《爱乐之城》。虽然在这几次竞争中,政治正确与社会良心都获得了胜利,然而在社会写实类电影风头较弱的年份,好莱坞对匠人精神的自我陶醉,就会淹没整个奥斯卡颁奖季。我们还能记起2012年《艺术家》与《雨果》的怀旧之争,也能记起《鸟人》与《少年时代》在2015年用两种独辟蹊径的方式,唤起好莱坞影人的艺术自豪感。毕竟,作为一场动员大会,奥斯卡奖用这种方式让业内成员重新打满鸡血,完全无可厚非。
去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闹出了乌龙事件,《爱乐之城》最终不敌《月光男孩》,错失最佳影片。
然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奥斯卡的天平,也在愈发地向着政治正确方向倾斜。投资仅有四百万美元的《月光男孩》在去年掀翻充满怀旧情结的歌舞片《爱乐之城》,本身就是个显著的征兆。而今年的三部强力种子,个个都在题材与政治取向上,占尽了先天优势。
《三块广告牌》展现了美国在特朗普时代的分裂境况,并提出了弥合的可能性;《逃出绝命镇》解释着美国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并通过反转结尾,让被压抑的少数族群得到了宣泄;《水形物语》虽然是奇幻片,却在人物设定上,亦步亦趋地遵循着政治正确的信条:片中所有的正面角色都是边缘群体的代表:聋哑人、黑人底层劳动者、同志,以及苏联移民。而片中所有健全的白人,都被塑造成了反面形象:辞退同志的老板、歧视黑人和同志的甜品店店员、极右的将军,和为将军干脏活的变态保安。
多样化图景,与矫枉过正的倾向
通过对《三块广告牌》、《绝命镇》和《水形物语》的表彰,奥斯卡奖在努力地摘掉它在之前数十年里被扣上的“老白男”帽子,并突出着好莱坞近些年里不断强调的一个关键词:“diversity”(多样性)。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确实是对题材多样性的一次有力陈列:名单包含了黑人电影(《逃出绝命镇》)、女性电影(《伯德小姐》)、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同性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由墨西哥导演拍摄的奇幻片(《水形物语》)。《敦刻尔克》、《至暗时刻》、《 *** 》,属于改编自真人真事的传统“主旋律”影片;而即便像《魅影缝匠》这样的异类,也带有着几分对男权秩序的颠覆意味。
通过这种多样化的图景,好莱坞似乎在许诺着不同族群走向平等的光明未来。本届影后弗兰西斯·迈克多蒙德(《三块广告牌》)在领奖时,提倡大牌影人在与片方签署合同时主动加入包容条款,使片中出现公平比例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作人员。这一条款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对其加以坚持,那么电影世界就会走向大同:在大部分电影中,男女比例都会达到接近1:1,而这正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
《奥斯卡80年》
副标题: Absolute Oscar 1929-2008
作者: 环球银幕杂志社
版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年
然而如果我们定下心来,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类1:1比例的理想状况,对具体现实忽略到了有点可笑的地步。你能想象像《落水狗》和《教父》这样的男性向经典电影中,被硬塞进一大批女性角色吗?你又能想象在《伴娘》和《公主日记》这样的小妞电影里硬生生加重男性角色的戏份,会得到怎样的效果吗?
奥斯卡奖和好莱坞对政治正确的追求,无疑有着良好的出发点,然而它们在具体执行时所显露出的刻板化、教条化倾向,却令人哑然失笑。我们都知道,奥斯卡奖的结果,从来都不单纯是对影片艺术水准的裁决,因为在其中,暗含了太多按资排辈的行内规矩,和太多相互权衡的政治考量。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奥斯卡奖不要变成一个完全政治化的奖项,因为这些参赛的好莱坞“员工”们的第一身份是艺人,而不是社会标兵、道德楷模,或者政治活动家。
作者导演得到表彰,
但作者电影还会回来吗?
从表面上看,在今年的奥斯卡竞争中,自编自导、对作品艺术质量有着完全控制权的“作者导演”,获得了可观的表彰。五位提名导演乔丹·皮尔(《绝命镇》)、克里斯托弗·诺兰(《敦刻尔克》)、格蕾塔·葛韦格(《伯德小姐》)、吉尔莫·德尔·托罗(《水形物语》)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魅影缝匠》),都为各自的影片编写了原创剧本;反倒是斯皮尔伯格(《 *** 》)和雷德利·斯科特(《金钱世界》)这样的老派技匠型导演,在今年的颁奖季里失了宠。这不禁让人好奇:好莱坞的更新换代是否正在完成?作者电影的春天,是不是要回来了?
现实远没有这么乐观。传统意义上的作者电影,仍然在被不断挤压着生存空间:马丁·斯科塞斯已经开始为Netflix拍电影(《爱尔兰人》),而大卫·芬奇、大卫·林奇和史蒂文·索德伯格,也纷纷转行去拍了电视剧(《心理神探》、《双峰》、《尼克病院》)。就连拿了最佳导演奖的吉尔莫·德尔·托罗,都说过《水形物语》是他的背水一战,不成功就退休。好莱坞在颁发奖项时会向作者导演露出笑脸,然而在决定要不要为作者导演的梦想投资时,它的“身体”却总是会很诚实地说不。
《 *** 》剧照。
所以,在笔者个人看来,好莱坞的 *** 声浪,其实完全找错了对象。如果说好莱坞电影的艺术品质在日渐下降,那也绝对不是出于性别秩序和种族秩序的不平等,而是出于资本与技术对“人”的抛弃。为了降低风险,增加回报率,超级英雄电影和特效大片依然大行其道,而展现复杂人性的电影,则被资本排挤到了产业边缘,在大多数时候,投资方宁可花几亿美元,打造一个潜在的大片系列,也不愿意为没有特效却有所表达的电影,掏出几千万美元。
《制造大片》
作者: [美]爱德华·杰·艾普斯坦
译者: 宋伟航
版本: 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 2016年6月
事实上,好莱坞影人最该 *** 的,是资本和技术的联姻。它们用各种眼花缭乱的宣传手段,决定着观众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并通过低龄化的无脑故事,让观众停留在永恒的童年时代,拒绝对复杂人性以及意识形态进行任何实质性反思。这样的现状,也在让导演和演员的表达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对着无处不在的绿幕,变成特效大片中可有可无的附庸。
可惜的是,奥斯卡虽然标榜着自身的艺术取向,然而在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指望它反对资本与技术的潮流,实在有些不现实。美国电影的希望,隐藏在那些被奥斯卡所忽视的独立电影中:与《水形物语》、《三块广告牌》与《绝命镇》相比,《好时光》、《佛罗里达乐园》和《鬼魅浮生》,具有着更多的生命力。这些回归人性本身的“轻工业”电影,才是美国电影所值得期待的未来。
▼
直接点击 关键词查看以往的精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