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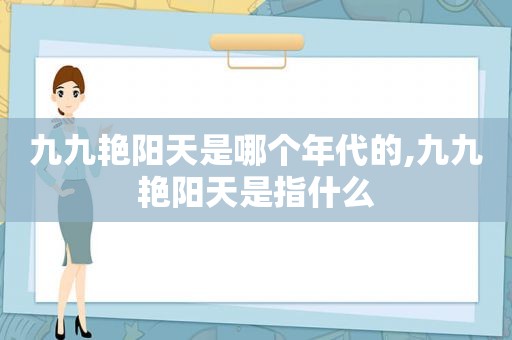
2月,因为疫情被关在家的周深和他的粉丝——李维嘉妈妈来了一次网络见面会。
应粉丝之邀,周深唱了多首老歌,其中一首《九九艳阳天》被网友疯狂点赞。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呐,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优美的旋律在周深婉转而富有层次的演唱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那片广袤的土地上。
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英俊青年高如星,没有想到自己作曲的这首歌会在半个多世纪后仍被传唱。
甚至一度在2月14日情人节这天,被恋爱中的人们用来互诉衷肠。
而在这样一个与爱人相伴的日子,高如星却因迫害与世长辞。
高如星葬于烈士陵园
他深爱的妻子王云霞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余生都未修复内心的伤痛。
2005年,78岁的王云霞面对节目组,失态落泪: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儿子的家是我儿子的家,我的家是我的家。丈夫在的时候,我跟丈夫是一个家,丈夫走了我心里是一个家。因为我心里老有他,走路、吃饭、上街、说话,甚至他有病他开玩笑他给我唱歌……我到现在还觉得像昨天。”
1958年,描写革命爱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轰动上映,插曲《九九艳阳天》与影片相映生辉,旋律明快悠扬,令人过耳不忘,一时风靡全国。
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之于人们各有着不同的意义。
对于作家白桦来说,这似乎是他逆境中一道暖阳。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58年4月的一天下午。
片中那首插曲使我没来由地泪如泉涌,为什么呢?
也许因为它的旋律出奇地温婉,也许是因为歌词惊人的纯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一落千丈的处境。
我在影片的字幕上看到作曲是高如星,我知道他。”
写下《九九艳阳天》的高如星刚刚29岁,这是他人生中最顺遂得意的时候。
高如星是小学文化,没进过音乐学院,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
文艺圈的人们把他看作天才。
不仅如此,还觉得他穿风衣特帅。
“因为他特洋,这个人怎么那么土又这么洋。”
或许正是音乐赋予了高如星这样的气质。
高如星出生在革命老区晋西北兴县,那是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
令人惊奇的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蕴含着丰富的民歌资源。
高如星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
就连树上小鸟的鸣叫,也能引发他的创作灵感,随即哼出动人的旋律。
1944年,抗日战争正在山西大地激烈进行。
15岁的高如星参加了八路军“战斗剧社”,学习文化,学拉提琴,随后正式参加了乐队演奏。
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 *** 政委去慰问在大风雪中艰苦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
慰问团一路走,一路慰问演出。
高如星是主要演员,他一会儿拉提琴,一会儿敲大鼓,还会跳踢踏舞。
就这样过了二郎山、大渡河,来到西康省康定城。
一行人要再往前走,不料大雪封山,只好在康定待命。
百无聊赖中,高如星把大家召集起来:“我和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 *** 》,你们听听行不行。”
《藏胞歌唱 *** 》是男女声二重唱,这种形式在当时很少,之后在筑路部队演出,很快在全国传开,并且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
孟贵彬与曹家定演唱《藏胞歌唱 *** 》
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被大大激发。
他想让自己的歌曲挂在战士的刺刀尖上,一起去冲锋陷阵。
军队生活像一块肥沃的土壤丰富着高如星的创作灵感。
“我脑子里有许多许多美好的动听的旋律。”
他仿佛一个音乐痴子,一心一意沉浸在音乐里,让优美的旋律从笔尖流淌。
不久,总政歌舞团以 *** 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的东欧各国。
高如星在苏联
高如星自然在其中,且负责整理全团队伍。
他把大小车和各车人数,安排得井井有条。
为了和苏联十几位司机搞好关系,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不久就能流利的对话。
在莫斯科的国土上,这个曾在杂草丛生的贫瘠土地上放羊的孩子震惊极了。
莫斯科到处是高楼大厦,一切都显得富丽堂皇,他在这儿听到了《喀秋莎》《山楂树》《伏尔加船夫曲》,见识了柴柯夫斯基、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
对音乐的痴爱更猛烈的击中了他。
他把发的零用费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与苏联留学生交上了朋友。
这一时期,高如星写下了近20部电影音乐。
然而,纯真、炙热在给高如星带来才情和名气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1961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高如星不要和苏联学生走得太近,他不听:“我们和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嘛。”
高如星战友
后来有位朋友偷偷告诉他被怀疑是苏联特务,他觉得不可以理喻:“真是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全是音符,怀疑我什么。”
现实很快给了他教训,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离开八一电影制片厂,调到武汉军区文工团。
这时,一切还不算坏,他还可以继续音乐创作之旅,而且遇到了迟来的爱情。
1963年,高如星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借过去写电影《汾水长流》的插曲。
在一次北影厂聚会上,高如星认识了电影演员王云霞。
大约是男才女貌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吸引,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意。
王云霞因为参演《红河激浪》,卷入政治斗争,变成留党察看“内控”人员。
她问高如星:“你敢接触我吗?”
高如星说:“我怎么不敢接触你呢。”
彼时,王云霞三十六七岁,高如星三十四五岁。
王云霞考虑到自己比高如星大,还有两个孩子,始终犹豫。
他跟她说,这种东西是千年一缘。
高如星的坚定打消了王云霞最后一丝顾虑,两个处境相同的中年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高如星会给王云霞唱民歌,各地的民歌,一唱能唱两三个小时,王云霞听着一点儿也不腻,觉着怎么那么好听呢。
王云霞说的话高如星总能听得进去,高如星说的话王云霞也总能听得进去。
在无常的岁月里,两人孤单的人做了彼此的港湾,成了彼此的知己。
王云霞母亲病重,生活十分困难。
高如星把《汾水长流》所有的稿费全部给了王云霞母亲。
高如星的善良,也坚定了王云霞要和他相守的心。
经过很久,他们的结婚申请才批准下来,这时候高如星已经回武汉了。
只有三天的假期,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她拿着结婚批示赶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那三天给了她后来四十多年无尽的怀念。
高如星为王云霞写了一首歌,是《枪之歌》中的一段:
“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高如星唱这首歌给她听,唱了整个剧本。
王云霞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听着他唱。
等到两人饥肠辘辘,才出去找了个小西餐馆。
王云霞记得离开武汉的那天,她心中不舍,从火车上跑下来抱着丈夫,她说:“我不哭,不流眼泪,我等着你。”转身上了火车,眼泪就哗哗的流。
这次相聚后又是长久的分别。
王云霞返京后随歌舞团辗转各地慰问演出,高如星继续留在武汉创作《枪之歌》。
王云霞有时不免为自己无辜被留党察看感到愤怒委屈,高如星总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
他们一直期盼着那天到来。
不能相聚的日子,他们每天给彼此写一封信。
如果知道后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宁愿余生都如此,哪怕只是偶尔相聚。
《枪之歌》公演后大受欢迎,好评如潮,高如星因此受到大人物接见。
这份荣誉,日后成了高如星罪状之一。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
高如星首当其冲,被造反派逼迫交待《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
造反派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
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 *** 肺里面,在如此剧烈疼痛下,他仍然愤怒反驳,斥责他们诬陷。
被打断的肋骨插入肺部,导致肺部感染发生癌变。
到这时高如星才被允许去医院看病,但要求他必须戴上手铐。
生性清高的高如星不肯接受,认为这种待犯人的方式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宁可放弃治疗。
1971年的那一天,天气还很寒冷。
远在他乡的王云霞突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她走了十八里路,从茶厂走到一个小火车站,奔赴武汉。
电话中她未得知丈夫生死,来到医院,医生说高如星还没起床。
她如释重负,他还活着,但高如星已经吐血吐得很厉害了。
王云霞说,那一下子自己连哭都不知道了,原来人到最痛苦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
临终前三天,高如星让妻子搀扶他去照相:“云霞,你把我的军装领章缝上,把军帽帽徽戴上,咱们俩到小照相馆照一张相。将来你告诉咱们的子女,就说他爸爸是堂堂正正的 *** 战士,是好人!”
这天之后,高如星的生命加速流逝,王云霞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弥留之际,高如星的小侄女忽然说:“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
高如星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是回应。
小姑娘朗声唱起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呐,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歌声中,高如星慢慢闭上了眼睛,年仅42岁。
王云霞抱着骨灰盒哭了三天,她写了张纸条放在了里边:等着我,我会到你这来的,永远的。
给高如星 *** 是在十年后之后,武汉军区代表说,高如星是优秀的中国 *** 党员,是年轻有为的战士,是优秀的作曲家,一切不实之词都要全部推到。
逝去的人已经逝去了,活着的人却把伤痛刻到了骨头里。
王云霞还留着结婚时人家送的一个搪瓷盘子,黄色的底子,中间是几朵红艳艳的花,盘子除了边上磕掉一点瓷,还像新的。
王云霞拿着盘子特别喜欢这个盘子,它比别的东西都鲜艳一些,能象征着人心灵当中有花。
在卧室里,有一件包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这是高如星唯一留下的东西,每年王云霞都掏出来晒晒。
从1971年高如星过世至今,这件军大衣没洗过。
“因为洗了就没有味道了,总要带点原来的温暖的味道,让你感觉到不一样。”说这个话时,王云霞把衣服紧紧抱在胸前,仿佛生怕它溜走了一样。
王云霞心中的最后那个家是医院,因为高如星在那儿。
一间小小的病房,一张病床,病床旁边摆放了一张竹靠椅,靠椅是王云霞歇息时用的。
因为相聚那样难得,即使是这样的时光,对于她都是无比幸福的。
2018年5月,王云霞逝世了,享年91岁。
在思念中活了47年后,她去找高如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