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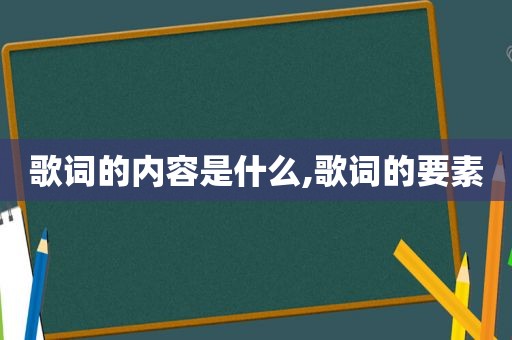
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日前,在热播综艺《乘风破浪》的第三场公演中,几位嘉宾翻唱了郑智化的经典曲目《星星点灯》,歌词却被节目组擅自改动,“肮脏的一片天”变成了“晴朗的一片天”。7月3日晚,郑智化本人发微博回应:“关于我的经典歌曲‘星星点灯’,被乱改歌词一事,我感到震惊、愤怒和遗憾!”
也许是对综艺改歌词这一隐形惯例不满已久,郑智化的发声激起了网友的共鸣。《北京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指出,“这次改编的最大可能恐怕还是为了表现某种‘正能量’。但问题在于,我们对于‘积极向上’的理解何至于如此狭隘?一首老歌难道不应该基于其特定背景?修改后的歌词消解了作品本身的深沉力量,反倒显露出一种苍白。”也有人从著作权方面指出类似行为的不妥之处,随意删改他人音乐作品涉嫌侵权。
另一方面,改歌词的行为在国内外都并不罕见,近年来的国内音乐综艺习惯于更改所有具有“负面”含义的词汇;国外音乐流媒体的算法也会过滤掉与性和暴力有关的字眼,创作者必须提前自我审查,以确保不会被市场抛弃。这似乎也侧面印证了流行音乐“只是娱乐产物”的看法,它只需要被消费,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在乎。
那么问题就是,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看做是严谨的文学作品?歌词的价值又应该如何判定?通过对此进行梳理,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理解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并且思考当某些歌词消失,作为听众的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音乐也是严肃的文学作品
关于音乐是否能被看做是文学作品,可以从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说起,在一些人看来,这是此奖项在1901年以来最激进的一次选择,进而引发了一场“歌词是否属于文学”的辩论。
对于诺奖的选择,出言讽刺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作家质疑道“那我是不是也能获得格莱美了?” 。但是,包括斯蒂芬·金、乔伊斯·卡罗尔在内的多名作家都对这一结果表示了认可,并称迪伦为“吟游诗人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美国前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则认为,虽然大部分音乐歌词都无法达到文学的水平,但是鲍勃·迪伦属于前2%的创作者,即使没有他的口琴和独特的沙哑嗓音,他的歌词也足以作为诗歌独立存在。与之稍有不同的是,多家外媒从歌曲本身出发,强调迪伦作品中的“诗性”不能与他的音乐表演分割开来,是表演本身带动了听众,并让歌词产生了超越语言符码的价值。
正如乐评人张铁志在著作《时代的噪音》中所说,迪伦歌曲中的力量并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分析,而是他用简洁有力的词句,抓住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美国的民歌运动本就孕育着浓厚的左翼理想主义色彩,迪伦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了许多时事歌曲,并真正影响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走势。1962年,迪伦在格林尼治村的咖啡店写下了名曲《随风而逝》,当人们听到“还要多久,某些人才能获得自由”,自然知道他指的是种族不平等,“炮弹要在空中呼啸而过多少次,它们才会被禁止”则明显指向了核武器。迪伦本人也曾经坦言:“现场面对面才是硬道理。我知道观众期望的东西与反应的方式,那是极为自发的。”
以流行音乐表达批判思考的做法并非迪伦的专属,许多人都把音乐变成了一种知性的文学表达工具。被誉为“非官方桂冠诗人”的摇滚歌手卢·里德(Lou Reed)经常在歌曲中回应诗人波德莱尔的生活哲学,他希望以个人化的表达反抗帝国主义中好战的鹰牌政治家们,并邀请听众以新的方式感受音乐,他提出:“你可能读过这种东西,那么为什么不用耳朵来听呢?阅读时你觉得很有趣,跟着它一起摇滚肯定也很有趣。”
在上世纪70年代,朋克音乐的兴起见证了另一场反抗独裁主义的起义,乐手们坚持无 *** 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自给自足的DIY(do-it-yourself)创作道路,乐队往往拒绝与大公司签约,而是选择发展自己的地下演出、录音和宣发网络。美国历史学家凯文·马特森总结了这一阶段的朋克运动并为此著书,书名就叫做《我们不是来娱乐你们的》(Were Not Here to Entertain),足以说明创作者们的坚定立场。
所以,与其说音乐终于可以参与进严肃文学中,或纠结于“歌词是否与诗歌具有同等价值”,倒不如说文学的定义已经随着这些“非正统文学家”的出现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正如文学学者马汉广在《鲍勃·迪伦事件与文学边界》一文所提出的,诺奖之所以会选择迪伦,是因为今天的诺奖面临着一个新的使命:重建文学和大众的连接。文学已经不再具有封闭的、确定的本质特征,而越来越与种族问题、地域问题、性别问题等纠缠不清,它必须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中,也即文学变成了一种间性存在。那么,为了达到这种间性的连接,大概没有哪种表达形式能比音乐做得更好,更能够唤起听者的情感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用音乐介入政治的尝试才值得被认真看待。同样在70年代,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胡德夫在鲍勃·迪伦的歌声中受到了社会意识的冲击,他和李双泽、杨弦一起推动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希望重振本土的文化认同。在民歌纪录片《四十年》里,胡德夫也谈到迪伦对自己的影响,他引用《随风而逝》的歌词“还要多少次,碰到问题时你把头转过去就算了”,认为这种批判正是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所需要的。迪伦也让胡德夫获得了直面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比如在1984年海山矿难之后,他在歌曲《为什么》的歌词里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离开碧绿的田园,飘荡在都市的边缘?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涌进昏暗的矿坑,呼吸着汗水和污气?”
无独有偶,郑智化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老幺的故事》也是一首以海山矿难为背景的歌曲,他用比胡德夫更加私人的视角,讲述了一名矿工的儿子在父亲葬身于矿难后来到城市的故事,想要经过一番打拼获得成功,但最后发现城市里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作为一个广告业出身、初出茅庐的音乐创作者,郑智化在这首歌中完整地展示了自己的现实批判性和敏锐善感,以及性格底色中的悲伤与荒凉。公平地说,90年代出道的郑智化以自己的方式承接了一部分中国台湾地区民歌运动的文脉,追随着这样一条脉络,当《星星点灯》的天空只能是“晴朗”的,郑智化的出离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音乐创作遇上商业力量
音乐到底是严肃文学还是娱乐消费的争议,也带我们进入了另一重悖论:即音乐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与商业制作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创作者往往致力于写出代表生活真实模样的歌曲,但是当它开始广受欢迎,歌曲就会被商业体制吸收、歪曲甚至是篡改。
就像这次《乘风破浪》的公演,重点已经不在于歌曲本身是否保有往昔的质朴动人,而在于舞台布景是否迷人,姐姐们谁的咖位更大、表演更加纯熟,从而能比别人拉到更多选票。经过幕后制作人的重新编曲,《星星点灯》俨然变成了另一首歌,更符合节目风格和审美,也更适合作为一场视听狂欢加以呈现,既然如此,“肮脏的天”当然是极其扎眼的,必须予以“修正”。
事实上,如何在自主创作和商业机制之间寻求平衡,对每个创作者来说都是两难的问题,他们必须在跨国公司制作、推广和销售中存活下来,同时确保歌曲中真实的面向。这是一个永恒的斗争,就连鲍勃·迪伦也难以幸免——当他在60年代把原声吉他换成电吉他时,即使是他最忠诚的粉丝也骂他为了商业出卖灵魂。好在迪伦已经在自己过往的民谣生涯中证明了自己的艺术成就,也大可以留下一句“我不想成为谁的代言人,也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就拂尘而去。
而在海峡对岸的另一名歌手——经常被拿来与郑智化做比较的罗大佑,也可算是这场争夺里的赢家之一。80年代初,当民歌运动在中国台湾地区走向末期,年轻人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欧美音乐,罗大佑带着首张专辑《之乎者也》改变了人们对国语歌的看法,也用批判性的歌词讽刺了僵化的教育机构,以及对于爱情“天长地久”的烂俗想象。配合上整体企划的成功,这张专辑的影响力延续到了他之后的作品中,并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但是对于郑智化来说,当他不再书写小人物的悲喜,而是通过《水手》一跃成为大众偶像,《星星点灯》也就变成了他商业成功路上的最后一个高点。乐评人“爱地人”曾经评论称,《星星》同名专辑在大陆的大卖导致了他在创作方向上的迷失和混乱,由于当时市场的多元化已经可以消化更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另类”歌手,郑智化的发片速度越来越快,《星星》中的他变成了一个上帝的角色,“以励志的语法引导众生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担当起了领航灯的作用。”然而,郑智化的真诚创作让我们记住的是《老幺的故事》中那个夹在矿山和城市之间的迷茫男孩,是《青春启示录》里那个无助脆弱的灵魂。由于无法顺利转型,经历浮沉之后他还是做回了一个平凡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大众遗忘。
这样看来,《星星点灯》遭遇“正能量”改编或许就具有了另一重意味——《星星》已经算是郑智化最为商业化、最偏向温暖和励志的歌曲,即便如此,也难逃被综艺节目篡改的命运。当仅存的一点真情实感也被剥夺,而只剩下食之无味的“积极乐观向上”,不仅确证了这种娱乐的空洞和虚假,也早已背叛了音乐的本身。
参考资料:
《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1975~2005)》 林怡君 / 吴清圣 / 陶晓清 / 马世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2
《等待那个男人 : 卢·里德的人生与音乐》[英] 杰里米·里德 著 董楠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2
《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张铁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鲍勃·迪伦事件与文学边界” 文化视野 马汉广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