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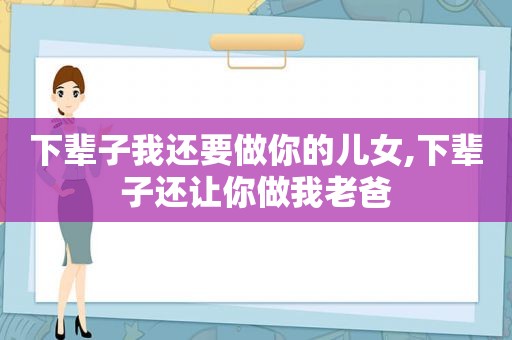
每次听刘和刚深情演唱的《父亲》,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这首歌,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这首歌,从来不曾放声唱起。
我是个喜欢唱歌的人,但从来不敢唱与父亲有关的歌曲。
以前,每每听到别人演唱崔京浩或刘和刚的《父亲》,原本可能很开心的我会立即变得沉默起来。
也曾试过在众人面前放声高唱与父亲无关的歌曲,可屡试不爽。往往是前奏还没有结束,我已无语哽噎。
是的,在我的情感世界里,父亲是一个让我倍感温暖的词汇,也是一个不敢轻易触碰的词汇。
这一切,只源于生父去世得太早。这一切,只源于早早地就失去了叫爸爸的机会。
后来结婚了,有了老丈人,可以经常喊一声“爸”了,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当然,我还是幸运的,我只是一度失去叫爸爸的机会而已,那份深沉的父爱,我从来不曾缺失。
那个应该叫一声老爸的男人,那个将我视为己出的男人,那个对我们兄妹五个恩重如山的男人,那个一直被我们兄妹五个叫做二叔的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他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他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默默担当着父亲的角色。
有了他,我们兄妹五个的母亲才了有依靠;有了他,我们这些过早失去生父的孩子才有了自尊而体面的童年;有了他,我才得以完成我的学业;有了他,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那个应该叫声老爸的男人,一生过得太苦太苦。
他有一个脾气古怪的父亲,年幼时经常挨打。即便长大成人了,他还要经常面对辱骂和棍棒的威胁。所以,在接纳妈妈和我们4个孩子之前,他曾长期一个人孤独生活。
我8岁那年,29岁的他迎娶了我42岁的母亲,还张开双臂迎接了我大哥之外的4个孩子。
那一年,大哥17岁,一直反对母亲改嫁,一心想帮母亲扛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无奈当年的他还没那个能力,母亲别无选择,而要强的大哥选择自己出去闯荡打拼。
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一份很重很重的责任,就这样压在了继父并不厚实的肩上。
为了那个家,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他付出得实在太多太多了,包括常年在山村小煤窑挖煤挣钱,最终积劳成疾,得上了怎么也无法治愈的尘肺。
犯病那年,他原本可以轻松一些,原本可以不再那么辛苦。
那一年,我军校毕业,有了一份不高但还算稳定的收入。
那一年,我和邻家女孩结婚,了却了他和妈妈的一桩心愿。
那一年,印象中一直很伟岸很健壮的他轰然病例,从此再也没能逃脱病痛的折磨。
该享清福的时候,他却病例了,而且病得那么严重,病到差不多生活不能自理。
连呼吸都不顺畅,连走路都很艰难,整整12年、前后迈出14个年头,那该是怎样一种痛苦和折磨?
那些年,为了给他治病,我没算过花过多少钱,我只记得他的痛苦,真的是感同身受,不忍提起。
那些年,远在东北当兵的我甚至不敢轻易往家里打电话,不忍心听到他在电话里一边喘着气,一边费力地告诉我他好多了。
我知道,在他的心里,我是他听话能干的小儿,我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
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担心,他是怕耽误我的工作。
可是,那时的我,工资不高,工作又忙,想回家看望他,一没时间,二缺经费,何况还想着把路费和回家的其他开销省下来给他治病,除了省吃俭用给他寻医问药,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我拿什么拯救这个被病痛苦苦折磨的男人?
清楚地记得,2011年9月28日晚,正在四川乐山出差的我,在岷江之畔,在乐山大佛对面,不经意听到有人哼唱刘和刚的《父亲》,我的感情顿时失控,一个人冲到江边,一个人嚎啕大哭。
那一刻,我想到了他,想到了那个应该叫声老爸的男人。
当时,他的尘肺已是晚期,已然没了治愈的可能。
那时的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一直不愿想象他还能挺多久,一直在纠结该不该改口叫他一声“爸爸”。
这个想法早就有了,一直没有实现的机会。或者不如说,一直没有那个勇气。
当时,我已经整整5年没回老家了。2011年“十一”长假期间,考虑我正在四川出差,离重庆开县不远,领导特批让我顺道回家看看。
那时的我,真想回去看看二叔和妈妈,看看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两个人。
就这样回去看看吗?是不是该做点别的事情?
那天晚上,在岷江边上嚎啕大哭之后,我给我的妻子、曾经的邻家女孩打电话,告诉她这我次回去要改口叫二叔一声爸爸。
我哭着告诉我的邻家女孩:我怕来不及了,我怕没机会了。
我的邻家女孩一如既往地理解和体贴:你想做的事情尽管去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邻家女孩决定带儿子于次日从沈阳直飞重庆,第二天再赶到万州和我汇合,之后一起回我们的共同老家,见证我改口叫二叔为老爸。
看似简单的事情,真就不那么容易,真的需要亲人的支持。
改口叫他爸爸,小妹肯定会百分百支持,我的两个哥哥和姐姐能同意吗?他们会不会有别的想法?
不征求他们的同意,显然不行。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他们,但我决定做一回不听话的弟弟。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要改口叫他爸爸。
这一次,我不能失去机会;这一次,我要牢牢抓住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大哥、二哥、姐姐无一反对,只是表示他们都已习惯叫继父为“二叔”,我自个改口就是了。
尤其是大哥,还给我讲了一个事。说母亲改嫁之初,他确实不同意,甚至直接要求2个弟弟、2个妹妹不得叫那个男人为“爸爸”,而是称其“二叔”。后来,大哥到外面闯荡数年后,得知继父对我们很好,他专门写信回家,建议我们兄妹五个改口叫继父为“爸爸”。但继父不同意,说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这就足够了。
2011年10月2日晚上,我决定正式改口叫二叔为“爸爸”。
这天晚上,我的堂兄、二哥、姐夫、外甥、侄儿等亲人会来我家聚会,共同欢迎我和妻儿的归来。
思虑再三,我觉得正式改二叔为爸爸之前,我应该到生父的坟前通报一声。毕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我们的父亲,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之为爸爸。
那天一直下雨,还伴随着二到三级的季风。我带着妻儿跪拜了亡父,并在心里默默向生父表达了我的想法。最后一个心理负担算是卸下了,我终于可以轻装前进了。
10月2日晚上聚餐时,酒过三巡,我让爱人给我盛满一大碗啤酒,提出要单独敬一下二叔。早已戒酒的二叔连忙推辞,说是自己不能喝酒,让我们几个尽兴即可。
见此情形, *** 脆站了起来,开门见山地说明自己这次回老家的最大目的:改叫二叔为爸爸。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原本比较激动的我竟然奇迹般地平静下来。
我向二叔表达了我们5个孩子对他的感激之情,央求他同意我代表5个孩子改口叫他爸爸。我说了很多很多,说得平静而动情。
看得出,二叔有些激动。不过他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甚至还边吃饭边听我在那里唠叨个没完。
等到我终于说完了,二叔开始说话,他同样说了很多很多,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5个孩子一直对他很好,一直把他当作亲生父亲,一直在竭尽全力为他治病。
二叔很动情地讲到,如果没有他的5个孩子,生病多年的他或许早已作古,荒草也许早就淹没了坟墓。
二叔明确表示,他不在乎什么称谓,以前叫什么还叫什么。
我了解二叔,知道他不想为难自己的孩子们,更不愿别人说自己的闲话。
我告诉二叔,别人愿说什么让他说去,这是您应该得到的尊重,您也完全配得上爸爸这个称呼。
二叔仍然坚持,妈妈和堂兄、二哥、姐夫纷纷劝说,仍然没有效果。一直到聚餐结束,二叔一直没有松口。
我没有放弃,搂着二叔的脖子,像小时候一样和他贴脸撒娇。姐夫和我爱人也一直陪在身边,不停地做着二叔的思想工作。
在我的软磨硬泡和家人的劝说下,二叔的防线开始一点点后撤,但始终不肯点头答应。
最后还是二哥出了个主意:管他同不同意,你喊完再说。
于是,我和爱人一前一后,正正规规改叫二叔为“爸爸”……
遗憾的是,3个多月后,也就是2012年1月30日晨,被尘肺折磨了14个年头的继父带着对爱人和孩子们的无限眷恋,在我和妻子的贴身陪伴下,在重庆市开县岳溪镇中心医院撒手人寰……
2011年9月29日晨于四川乐山,2021年1月16日晚完善于河北石家庄
刘和刚《父亲》歌词
想想您的背影
我感受了坚韧
抚摸您的双手
我摸到了艰辛
不知不觉您鬓角露了白发
不声不响您眼角上添了皱纹
我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
您只尝了三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央求您呀下辈子
还做我的父亲
听听您的叮嘱
我接过了自信
凝望您的目光
我看到了爱心
有老有小您手里捧着笑声
再苦再累您脸上挂着温馨
我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
您却持了十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央求您呀下辈子
还做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