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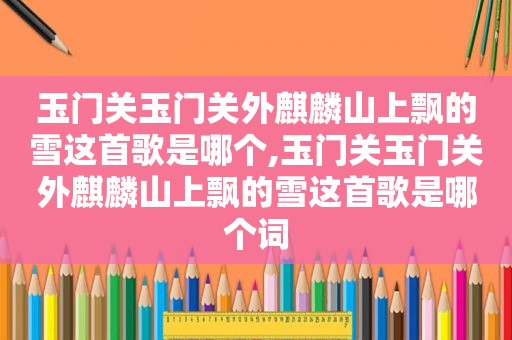
锅上的饭菜已经好了。
我大开城门,远远望着都抑制不住高兴,跑上前去迎。
思衡见我来,直接翻下马,“阿姊。”
“此行可还顺利?”
“顺利,只是……”
“切。”长孙泽骑在马上继续悠悠往城里走,“这家伙只顾着眼前的人,身后偷袭完全不顾,要不是若虚挡了一刀,如今就是一具死尸。”
我一惊,看向一边的陆筠:“你伤了?”
他眼角有笑意,却摇头道:“这才想起我来。”
本打算找补回来,结果人家也往城里走去。我舍了思衡,跟在马后面追,“你伤哪里了?要不要紧?疼不疼?”
人家也不理我。算是得罪了。
晚上我坐在窗边读施皓整理的案卷。他亦是一手乱七八糟的字,看得我颇费神。
只见瑶瑶蝴蝶般扑扑腾腾进来:“公主,太子过来了?”
她话音未落,就听见脚步声进来。小蝴蝶匆匆扑腾走了,还好心关上了门。
“伤了胳膊也要赶着去陪他们喝酒?这会儿是舍得回来了?”
我放下朱笔,抬首看他。这家伙穿起劲装气质都不一样了,有年轻将领的样子了。
他一进来脱了玄色的外衣,一眼便能瞧见左胳膊上的血迹,“将士们今日辛苦了,这杯庆功酒自是不能少。”
一早令瑶瑶备下伤药,我端着案盘过去,给他拆了此前草草包裹的伤口,重新上药:“保护思衡,你辛苦了。”
陆筠那道不深不浅的伤口,随意道:“我做姐夫,应该的。”
此言说得我一怔,手上动作也停了。
我还感动来着,然后听他道:“就应该让他挨这一刀,吃吃亏,往后便晓得要小心了。”
“怎么不让他挨呢?”我给他敷上药,他眉头不经意皱了皱,“疼么?”
“不疼。”
怎么会不疼?
我叹气:“又是个不知道喊疼的郎君。你们这群人啊,没一个受了伤喊疼。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你不说,旁人就真的当你不痛了。”
“疼,疼死了。”这家伙居然直接入戏了,说着撇着嘴倒进我怀里。整得我哭笑不得了。
还能如何,好声好气哄吧:“那我 *** 儿,我帮你包上,你别乱动。”
腻味着呢,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居然是长孙怡:“汝宁,找你有事商议。”
陆筠听了,下一瞬变回方才四平八稳的模样,坐正让我继续包扎。
我唤了她进来。
她看到陆筠在屋里,不知有些话该不该说。
“说吧。没事儿。”
“长孙将军的小厮,慕容氏追查到了底细。”
“嗯。”我抬眼看了她一眼,不知她今日为何支支吾吾的,以往不这样的。
她亦有犹豫,攥着个册子递上来:“小厮冬衣,系当年河东闻喜裴氏,原名裴冬。”
我收拾药瓶的手一顿,“河东闻喜裴氏?”
“是。”
陆筠见我神情有变,不禁问道:“怎么了?”
我扯了个笑给他:“非衣,阮非衣是河东闻喜裴氏的养女。”
裴冬是奸细,必然会令人怀疑到非衣身上,亦会扯出当年河东闻喜裴氏的旧案。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看过她递来的册子:“去查非衣。还有裴氏未被处死的族人,现下都在何处。至于她这个人,这几日便安置个空余的房间,别让她出去了。其次,去查裴冬是如何传消息出去的。”
“你不信非衣?”长孙怡蹙眉问我。
“非衣是我最信之人。如今到此处,知晓此事的人必会怀疑她。所以要查,彻底查清,还她清白。”
我不能有偏袒。
屋里还说着话,屋外瑶瑶再次进来。
见她犹豫,我先问道:“怎么了?”
“长孙将军方才听闻今日抓拿的奸细是他的小厮,这会儿正在外面等着。”
不是今日刚归来,先休息好么,哪个多嘴多舌的说出去了。
“让他进来。”
长孙也是刚刚卸了甲,但还没来得及换干净的衣服。
“坐。”我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下。
谁想这人竟到我面前来跪下了,“听闻阿棹扣押了我的冬衣。”
“对。”我答。
“为何?”他不卑不亢问:“可有证据?”
“自然是有的。只是同党还未全抓捕,不过也就几日的时间,届时一定给你公道。”我又拿过案卷,见他还跪着:“起来,坐。今日辛苦了。”
长孙泽仍是没动:“冬衣是我的人……他若有罪,我如何洗脱干系?”
“那是我的事。”我注视他的眼,没有一丝动摇,“你的事是打好仗。”
无端端屋里像冷了几分。忽然传来流水声,我侧目看,陆筠倒了一杯茶,起身将地上的人扶起来,递了茶上去。
陆筠竟抿唇笑了,回身指了指我:“阿泽,你的小厮出事,她比你着急。我最知道,你们这些武将,一遇到事,脑子里想的全是兔死狗烹那一套。不必这样想禾舟,她的心比旁人,干净许多。”
我不由眯起眼睛,这家伙怎么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
我清了清嗓子:“冬衣从前是河东闻喜裴氏的庶子,因着家族逆罪,贬入奴籍。你可知道这事儿?”
他并未回答,而是皱起眉:“闻喜裴氏,那非衣岂不是也……”
我给自己添茶:“所以啊,我比你着急。”
长孙泽不知道裴冬从前是裴氏,只知道是前年回京时家里给安排的。
说来我就炸了:“你是兵部的大将军,身边带的人,不查清楚么?”
他还委屈上了:“我又不是你们,整日与权谋为伍,行事要处处谨慎。我就是个兵,冬衣也就帮我端个茶倒个水的,哪有那么多讲究。”
还敢讲我们说一顿?我火气更盛,抄起手里的案卷就打他胳膊:“你少来说我们!你去问问冷凝,问问景凭,问问崔将军,有几个不知道身边人底细的?你还有理了?”
陆筠看我是真的动气,过来夺过手里的书:“倒也不必迁怒。”
敢劝我肯定一并骂了:“迁怒的就是他!如今,军情泄露,我方第一战折损数千兵力,冷凝重伤昏迷,眼下又牵出当年旧案,非衣都被我关起来了。问起来,他都不知裴冬是闻喜裴氏。还想什么’兔死狗烹’?我现在烹了你倒是给你痛快,来日若在朝中被奸佞设计构陷,怕是要死一家!长孙家一门忠心,怕是到头来都被他毁了!”
我越说越气,指着陆筠道:“还有你……”
他一脸无辜。我找不出错处,胡乱道:“别在我眼前晃悠。”
陆筠夺过阿泽还没喝的茶给我:“我错了,别生气了。”
我没接,坐回原来的位置上,寞然盯着地面:“冷凝若是有事……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冷凝昏迷的第五日,开始不进水食,喂进去就往外吐。
昔陶急得红了眼睛,端着碗的手都在发颤,“怎么办啊?”
祁钰立在一边,拧着眉,不知在想些什么。
“还有办法么?”我就站他旁边,非常小声地问,也不知他能不能听到。
他似乎也很艰难:“先让彭姑娘喂完,虽是往外吐,能喝多少是多少。等会儿我给他施一套针,看看有没有用……”
“若是施针无用……”我总归要做坏的打算。
“还请公主节哀……”他声音也轻极了。
我缓缓摇头,“节哀是很难了,他若马革裹尸,我该如何跟冷家交代?如何跟百姓交代?来日去到地下,又如何跟淳于交代呢?”
我看不开的。
瑶瑶看我不高兴,忽然向我行了一礼:“裴冬的案子还待审,公主要不先查案子?冷将军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平安的。”
她怕我守在跟前伤心,让我查案分分心。她说得是啊,我又不是医生,又不会照顾人,还是莫要跟前添乱了。
“去与长孙怡说,提审裴冬,阮非衣。另外,让长孙将军一同带来。”
根据施皓事先审查。裴冬平日都靠信鸽跟外面互通消息。无论有没有军情,每日皆须送信,若有一日断信,将视作暗桩被发现。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颗弃子?”我端了一碗刚出锅的油茶,一边喝一边嚼浮在上面的芝麻。
他没打算搭理,我让人也给他盛一碗油茶。
这人不识好歹,拿过油茶便摔在地上,还在上面吐了几口唾沫:“我呸,你也配?”
“我不配。那谁配?我着人去请。”我还没说完,长孙泽便踏着飞雪进来了。
他解了斗篷递给瑶瑶:“怎么?要我亲自审你?”
裴冬亦无丝毫波澜:“你们既然已经抓到我,肯定知道我是裴家人。”
“那是当年河东闻喜裴氏的案卷。”我指指案上的案牍,“这么说,你投敌与裴氏有关?”
“是你们,害死了我阿爷阿娘!”他本缚手在身后,这会儿挣扎想站起身。
“是他们自己害死了自己!”我提高音量:“当年裴严为吏部尚书,积年贪银十万两,致使大理寺刑部犯人饿死者十有八九。这也就罢了,御史中丞意外得知此事,欲弹劾裴严,可一家人一夕间惨遭强盗杀害。”
“那是强盗!与我裴家无关!”他眦目欲裂,大声吼道。
“裴严开始也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师父抓到了强盗头子,其人声称他的一家老小都被雇主关押起来,若是他泄漏半字,家人就会惨遭屠戮。”我走到他身前蹲下,直视他道:“你知道强盗家人的尸首在哪里被发现的么?在你家城北庄子里,有块儿新土被我们翻出来了。”
我从案前拿了一张纸下来:“这是裴严的认罪书。此案是我师父在燕京办的第一个重案,他相当认真对待,绝无半点纰漏。结案后,尘封这十数年,曾被无数次翻找重查,一切线索皆记载详实,没有任何错漏。”
“不可能!不可能!我阿爷断断没有认罪,他到死都不愿认罪,是慕容老贼逼他签的!他没有罪!是朝廷想息事宁人!”他声音大得震天。
他不信我情有可原,我唤屏风后的非衣出来:“找个你信的人跟你说。”
非衣奉命出来,亦跪到堂前,对着身边的裴冬道:“裴严 *** ,李中丞灭门一案,为三司会审,所有证人均到堂,这份认罪书,是父亲亲笔签的。汝宁公主没有丝毫欺骗隐瞒。”
裴冬见到非衣呆怔半晌,终是不相信她的话:“裴轻染,你全然忘了是他们杀了父亲母亲吗?你还替他们说话?”
非衣似是失了耐性:“裴冬,是裴严不听劝阻,铸成大错,才让裴家子孙受到牵连。如今,你叛齐,是想让裴家诛九族吗?”
“裴家活着的子弟亦一夕之间沦为奴婢。活着比死了还痛苦!全族唯你一人被赦免,你自然可以云淡风轻。你知道阿娘现在在右相府中做洗脚婢吗?”
非衣递上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我跟你熟么?我三岁被裴家收养,是为替代体弱多病的裴夏选入宫中做公主陪读。”
“当年要不是裴家收养你,你就饿死在裴府门口了!你忘恩负义!”他气急大骂。
非衣气得站起身:“我忘恩负义?我这些年照顾裴家子弟,令他们有安身之所,哪怕为奴我也替他们寻个宽和的主子。今日你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牵连我,还责我忘恩负义?”
我沉了脸:“非衣,是你安排他进长孙府?”
非衣合上眼,慢慢跪了下去:“是我。”
“你糊涂……”我取了另一个册子拿给她,“不过倒是不说谎……我从来不疑你,可这个案子,你一时半会儿怕是脱不了嫌疑……”
长孙府混进敌军的奸细,奸细是非衣送进去的。她如何脱得了干系?施皓呈给我的册子上,早已将这些记得清清楚楚。
我唯一疑惑的是,我在燕京三法司呆了超过十年,从未有人疑过裴家的案子,裴冬为何会怀疑有人从中作梗?我皱起眉问他:“谁告诉你裴氏无辜?”
这个人必是教唆他叛齐的人。
他见我如此问,突然怔住了,恍然却大笑不止,目光转向长孙泽,继而变得怨怼:“我是长孙将军的人,自然听令于将军。王庭感谢您的尽忠。”
长孙泽阴沉着脸,抽刀横在他颈边:“你敢污蔑我?”
“不是您让我传信给王庭的么?”他一脸惊诧。
我抽了长孙泽的刀:“他已是逃不过,自然会四处攀咬他人。”
“罢了。先将人押下去吧。”我叹了口气。
长孙泽尚且气得不行,我却在想,不可能随便哪个阿猫阿狗跟裴冬说了什么,就能让他认定裴家无辜。
我看了一眼做堂录的长孙怡:“裴冬平日接触过哪些人?”
她应声递给我张纸。我瞄了一眼,并未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在上面。
我摇摇头:“再查。”
长孙泽拉住我,一脸茫然:“你是如何抓到裴冬的?”
我得意地扬眉毛,故作神秘道:“那日,我们在屋内密谈,定下来攻打北夷防守不力的凤凰山。下发的公文上写的却是再次攻打玉门的计划。
“我在公文上动了手脚,每个人拿到手的公文都略有不同。你拿到的是主攻南门,有人拿到的是主攻北门。恰巧我们在玉门城内有内应,且看城防布控,哪个门防守最严,就知道是谁的人泄露了秘密。”
他恍然:“厉害。”
“至于战事……接下来怎么办?”虽然幕后之人还未浮出水面,但战事禁不起拖。
他拍了拍我胳膊:“玉门是个关口,绕不过去。”
“可不么,自古都道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绕不过的。”我叹罢,“明日我去玉门城里一探。”
“不可。”
“不可。”
长孙怡和长孙泽一同出声。
我还觉得稀奇了一阵,“无事,我跟着行商进去,要会个友人。”
念着长孙怡要跟慕容氏对接案子,我带了瑶瑶和梁军中的一名女将一同进城。
若说起这名女将,还与我家颇有渊源。她的祖母是梁国的开国将军之一明平西,是与高祖皇帝一起打天下的人。她的箭术百步穿杨,天下无人能及,从前我父亲领兵打仗时,亦得她教导。
“今日公主入玉门城有何事宜?”
明茗是被陆筠强行安排来的,不过似乎没有丝毫不乐意的样子。
“不过见个故人。”我不好意思笑笑,“你本是要去练兵,现在穿上裙子与我进城,不嫌闷么?”
她掀开帘子望着外面,反而很新奇:“我从小长在我祖母膝下,她以前就与我讲过玉门关,我挺想看看的。”
我笑眯眼睛:“今日可去不了玉门关。今日去城里。”
“我知道。”她似乎也没有沮丧。
曾娘的花楼开在城中最热闹的地段。我找到她时,她正在门口迎客。
“姑娘来这儿可是寻什么人?”
我没掀开幕离,而是故意问:“吃酒不可以么?”
曾娘的笑似乎僵了僵:“自然是可以的。”
我叹了口气,摘了帽子。
她吓得不轻,急急忙忙把我拉进屋里,一路上到三楼她的房里:“公主怎么进城了?现在查得这么严……”
她边说还边合上窗子。
我拉过明茗坐下,毫不客气地提了她的茶壶倒茶。
“我已经五六年没来过玉门城了,除了你,哪还有人记得我。”
她眼睛瞪得溜圆:“如今守玉门城的人是庆玉,他与你交过手!”
我知道。可是庆玉也不可能日日守在城门口啊。
曾娘说完话,才发现我身边跟了个生面孔的人:“这位姑娘是?”
“明茗,梁兵部员外郎。”我介绍道。
“明茗?姓明?是明老将军的……”
“孙女。”
曾娘了然。
曾娘从前在淳于敦煌的府邸中做管家,后来敦煌沦陷,她成了流民。不过好在有一手管家的好本事,混乱中接手了玉城里最大的花楼。
她是我在西北的暗桩,连慕容氏都没有人知道她的事。安插她就是为了将来有一日收复失地。
曾娘吩咐着外面的侍女去准备午饭,这才回来坐着,“公主可抓到奸细了?”
“抓到了。”我点头,然后将整个事情跟她讲了一遍。
那日我收到她从城里传回来的消息,关于玉门城内布防。我才得以抓到裴冬。
曾娘蹙眉问:“公主会不会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怎么说?”我倒很想听听她的想法。
“裴冬能信得过的人,并且相信的,无非是官府的人。朝中高官,或是三法司的人。那不就是与公主共事的人么。”
“你是想说非衣吧。”我喝了口茶。
“非衣难道不值得怀疑么?只是您不愿去怀疑罢了。”
我敲着桌子,“三法司查起来人太多了,动一发而牵全身。要查慕容氏的人,就不能用慕容氏的人。”
曾娘笑了:“公主抓到裴冬时,估计就已经晓得慕容氏怕是不能全然相信了。不然,今日前来,为何不带长孙家的那个姑娘呢?”
我看了一眼明茗,她有些不知所措地看我。
我是哭笑不得的:“还是太难操作了。想绕过慕容氏查三法司,怕是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
“慕容氏,自是有可信之人。不必全然绕过。”
她话音还没落,外面突然响起了喧闹。侍女慌张闯进来:“外面突然来了官兵,说要查齐国的奸细。”
“北夷怎么知道我们进城了?”明茗有几分慌神。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无奈地闭了眼睛:“因为慕容氏有奸细。慕容氏在西北的暗桩里,有奸细。”
正是因为如此,我的动向,他们都一清二楚。北夷若是抓了我,就有了跟我母皇讲条件的筹码。
曾娘开了窗子,让我们往外逃。我们刚刚踩在瓦上,便惊动了巷子里的北夷兵,个个抬头瞧我们。
来不及反应便开始踏着瓦跑,回头看了一眼明茗:“往城南跑,那边城防最松,瑶瑶在那边接应我们。”
风在我耳边叫嚣,身后是紧跟不舍的北夷兵,伴随着不知何处传来的钟鼓声。
待我甩他们数百米后,从房顶跃下,才想起来,我甩掉了北夷兵,却也丢了明茗。正慌忙时刻,忽然有个人讲我从墙角拉进旁边的屋里。我下意识要攻击对方,结果发现这人是曾娘。
我呼出一口气,听外面的北夷兵穿过巷子。
“明茗丢了。”
曾娘看着破败无人的房子,皱眉道:“我从东面追你来,没听见有人被抓,估计她现在还是安全的。”
“庆玉的目标是我,不是她。”
“对啊,你才是他们要抓的人。”她塞给我个包裹,“赶紧把衣服换了,在今晚以前混出城去。”
我迟疑了半晌,还是到旁边把衣服换了:“庆玉从前来敦煌城里跟我谈判过……”
“所以?”她不理解我的意思。
我缓慢摇了摇头,“没什么……”
换好衣服从后门出去,街上的兵似乎比刚才更多了。
等我低着头往南门走,守卫远比刚刚入城时多了三倍,检查得也比方才认真许多。
忽然有一队兵从东面来,口里喊着要对路上每个女人进行审问,尤其要盘问只会说汉话的女子。
不少进城赶集的汉女被抓了去。我头埋得更低,趁着他们盘问旁边的女子时,从人群中混过去。结果被一个将军装素的人拦住了。
我心跳得快到嗓子眼儿,抬头却发现不是庆玉,而是个生面孔。他不急不慌问我:“姑娘这是要出城吗?”
我抬头看他,也不着急地笑了笑,刚要用匈奴语说去探望父母。
谁想却被身后一个声音截住了:“你们是要找大齐的汝宁公主么?放了这些妇孺,抓我去就好了。”
我不敢置信地回过头去,看到明茗在人群中一字一句稳稳笑道。
明茗递了个眼神过来。我身边的将军也绕过我,向她而去。
我裹紧头巾,转身往南门外走去。
独自一人在屋中,炭火烧得过旺,身上浮出一层薄汗。
我垂眸瞧了一眼炭盆里的火星,门外诸将领们的对话就在耳畔。
海将军低声说:“明茗是明老将军亲自养在身边的姑娘,明家翘楚,当初陛下命我去讨要来,令其入朝为官,明将军都不舍。况且她新婚燕尔,临行前刚与御史台中丞成亲,因战事分离。现如今落入庆玉手中,生死未卜……”
我合上匣子,手指在其上敲了几下,思量片刻才唤了门口的瑶瑶:“将非衣带来。”
也就片刻功夫,非衣就进来了。我打量她好一会儿。她跪在前面一动没动,身上素素净净,头上也没个钗环。
我闲来提笔写字,就那句“春风不度玉门关”。
屋里极静的,仿佛能听见炭火燃烧的微响。
“非衣。你知道为何人们说身居高位者,‘高处不胜寒’么?”
她这才抬头看我。
这面孔太过熟悉,总角之年至双十年华都是她陪我在侧。
“可能身居高位,很少有人能理解其中艰辛?”她答道。
“非也。”我停了笔,起身走到她跟前,毫无形象地盘腿坐下。她似乎对我的态度有些惊讶,却没开口。
“因为身居高位,所以不得不肩负起更多的责任,顾及更多人的利益。故而,不能偏袒身边的亲戚故旧,时间一久,自然身旁就无人了。”
她微微皱眉:“我知道汝宁疑我,并非你本意,是不得已而为之。非衣不觉得委屈。”
我笑着摇头:“我疑所有人。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才知道什么人可用,什么人不可用。而且人心易变,今日可用之人,明日未必可用。”
“但我信你。”我将盒子交给她,“帮我办一件事。”
玉门城内没有传来别的消息,想来庆玉发现所抓之人不是汝宁公主。众人商议如何救出明茗时,我只是发着呆吃枣子。
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你们知道庆玉的母亲当年是庸城的守将之一,是被明老将军亲手斩杀的么。”
早前我还没想起来,如今才忆起。
所有人都沉默了,只陆筠问:“你如何知晓?”
“这些在书里都没记录。他母亲也没个正经名字,是庆项的外宅,后来凭着一身武艺成了北夷南边的守将。明将军破庸城时,她把庆玉藏到花楼里,自己赴死去了。”
众人依旧沉默,只有陆筠蹙眉追问:“所以问你如何知晓?”
我低头看了眼空空的手腕子:“庆玉当年入城假意求和,我和他商议的条款,吃了顿饭。他亲口跟我说的。”
海将军低声道:“如此,明茗落入他手中,恐凶多吉少。”
“……未必。庆玉……挺不一样的,不怎么乱杀无辜。就是不知道这些年变了没有。”
北夷入驻西北十镇,多行屠戮之事,唯独庆玉,手底下的人都极守规矩。
“人,还是要救。不过,我们先按兵不动,看庆玉提什么条件。”
我忽然觉得自己进入状态了。
庆玉提出让汝宁公主入城去商议。
我觉得他提这个条件的时候就没觉得会成功。我们一拒,便立马更换了条款。
“让他去玉城,还不如让我去呢。”我甩了那一纸公文。
“为何我不能去?”温思衡在旁边反复嚷嚷这句。
吵得我脑子疼,我终于不耐烦了:“因为怕你死里面,我没法跟禾音交代。”
“为何你们可以舍生忘死,但我却不行?”他难得与我针锋相对。
“庆玉为何让你去,你心里没有点数吗?”
他是和音的未婚夫婿,到底是个要紧的人物。
本来场面已经有几分失控了,但这会儿昔陶忽然在一旁开口道:“且让他去吧。总得有人去,他既然想去,便去见一见也好,你若不放心,我陪他一道去。”
我紧拧眉头:“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昔陶见我气急,笑了,“你是关心则乱。”
最终,没让昔陶去,而是换了淳于敛陪他去。就在太阳落山之前,他们一行人被迎进城中。
谁知第二日人便顺利归来。我着实诧异。不过没将明茗带出来。
温思衡气愤道:“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按着阿姊的意思,车马银钱皆可给他们,但守城不可让一分。谁知他咬死了,非要让我们将凤凰山还与他们。他们是在白日做梦吧。”
我倒觉得并不意外,庆玉可能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人。
“不急,且看看。”
当晚,我给玉门城内的曾娘去了一封信。
非衣是在第五日归来了,她其实并未走远,只去了一趟西都长安。不过那里慕容氏的消息网更灵通。
我捧着她带回来的消息一册一册读时,长孙怡也在一旁。
她颇为不解:“明明靠慕容氏就可以查到,为何要派非衣亲自去查一遍?”
我还没答,非衣呈上另一封信。
拿过一看,封面上是景充的字。
“师兄?”我有些惊讶。
信里的内容,让我大为震惊。
他在京中替我重阅了当年的裴公一案。他证实非衣近五年来从未调出过这份案卷,可信里提到了另一个人—-施皓。
五年来施皓曾两度调阅裴家的案子。正因其人涉及当前慕容氏在陇右的调度,景充留了个心眼儿,查了施皓此人。发现近三年间他调阅过几十起旧案,有些看似不起眼,但几乎个个都涉及家破人亡。
有像裴家这般判重刑的,也有未查清的悬案。
我看过之后便陷入沉思。长孙怡好像有喊我,但我没反应过来。
她过来拿过我手中信,读罢亦脸色大变:“施皓他陇右消息网,无端调阅这些刑部案卷做甚?”
我看着单子上景充抄写的密密麻麻的案件名称,整个人不寒而栗。
“他在策反。”
听说施皓被人抓住时试图逃跑,被长孙将军直接拧掉了胳膊。
这几日冷凝的身子转好,虽然还没醒,但好了许多了。
我卧在一旁的榻上,趁机松快松快,昔陶偏不让我睡,比我还急:“施皓落网了,可他手下那些人怎么办?”
“好问题。”我迷糊点头,“容我想想。”
当天晚上,陆筠正在榻侧研究接下来攻打的方向,我枕在书上睡得稀里糊涂。
外面忽然传来欢呼雀跃之声,惊醒之余嘴角还挂着口水。陆筠看了直笑,取帕子给我擦:“瞧着你五六日都提心吊胆不得好眠,今儿见你读书睡着了,就没喊你起来。”
外面的瑶瑶和长鸣都不要命地敲门,我们便出去应了。
果然不出所料,施皓的党羽来“自投罗网”了。我早想到他策反一众人,那些人得知他被抓,必然前来营救。于是早早布了个局,将人一网打破。
“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中计?”长孙泽想不明白问我。
“我不知道。只是猜的。你想,他都能将暗桩插到了你身边,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什么消息是他的人打探不到的?”
这些人,都是刀尖舔血之人,必然义薄云天,如何会不营救施皓?
来者有十五人,两条街巷打探者有九人,潜入府中做内应者三人,潜伏房梁伺机动手者三人。却不知我早将施皓关去了其他地方。
我懒得跟这些人多说,还能有什么新鲜的?无非跟裴冬一个德行,觉得自家是无辜的,觉得官府草菅人命。
“非衣,去对一下,他们里面有多少是慕容氏的人。”我吩咐道,“至于他们家人所涉案件,将案卷抄录调来,让他们且看看真的。”
边关的月亮真亮啊,照得梦都清明。
离开前,我只扔下一句话:“你们许是觉得,自家亲人必然受冤屈。可往往家中父母无论在外面多面目可憎,但回到家中依然会以慈爱待儿。这不意味着他们无辜。”
施皓的胳膊刚给接上,见到我来了,眼睛都没有抬。
非衣搬来椅子,我就坐在离他两丈远之处。
翻开手里的案牍,时间过得太久,纸页泛黄带着潮气:“景元初年,燕京施公次子施皑于城东……”
“他是无辜的!”原本不看我的这人,突然出声。
我将案牍合上,“这份案卷你八年来调出过十二次,想来比我更熟稔。所以……为何?”
“什么为何?”他愤怒看我。
“你若有冤情,可以上诉重审,你却未曾这般做。八次调阅此案,你有什么收获?”
他没有说话。
“你没有任何收获。你弟弟亲手杀的周姑娘,伤了郑公子,他对此供认不讳。案牍上也记载了,你为弟脱罪,声称是郑公子陷害于他。”
“就是陷害!”他圆眼怒睁,“郑公与家父朝堂上于陇右战事上有纷争,于是郑慊就找自己的侄儿勾引施皑的外室周嫣。施皑知晓此事,才失手杀了周嫣。”
“失手杀人?不是杀人吗?”
后面的故事我也知道,施皑被判刑后,施父不能自释,吊梁自尽了,施母也在数月后病亡。我师父好心将施皓收入慕容氏,如今倒是恩将仇报。
“我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可他郑慊却依然立于朝堂。凭什么?”他嘶吼问我。
“凭郑慊虽然手段下作,却不会触及家国法度的底线。施皑杀了人,你如何也无法替施皑脱罪,故而心怀怨怼,投敌北夷?”
瑶瑶帮我在屋里多燃了几盏灯,我能看清他涕泗横流的面庞。
“你们害得我一无所有,还要好心来施舍我。装出大善人的样子来救赎我们,真是异想天开……你以为只有我们这些人吗?哪怕今日你抓了来营救的人,可我们的队伍远比想象的强大。”
“我知道。”我点头,并不感到惊讶,“施皓,你要知道,人心本就复杂。慕容氏本就遍布天下,汇聚三教九流之人,其中难免有异心。可那又如何?北夷若是今朝被朝廷攻克了,你们这些投敌之人还能如何?还为谁效忠呢?邪不压正,天下不是只有诡道。”
他脸上的络腮胡子都在颤抖:“那郑慊,至今还在朝堂上。你跟我说什么邪不压正?”
“你做了这么多年刑狱,过手案件无数。什么是公正呢?所有人都得到公正吗?道德若是可以约束每个人,那要法律做什么?法律可以编写成道德那样么?它只能是最低点。”我也很无奈,我也很同情,但道理只能是如此,“至于北夷给了你什么好处,我回头打下来玉门,自去问庆玉。你到时会被压入京城候审,话说师父也很多年没见过你了。”
还记得十几岁时来陇右,当时强盗横行,我和施皓一起破了不少案子。也是夜半蹲哨的交情,我却从不知他心中有这般的怨怼。
也罢。往事去兮。
【本章完结】
预计三十六章全文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