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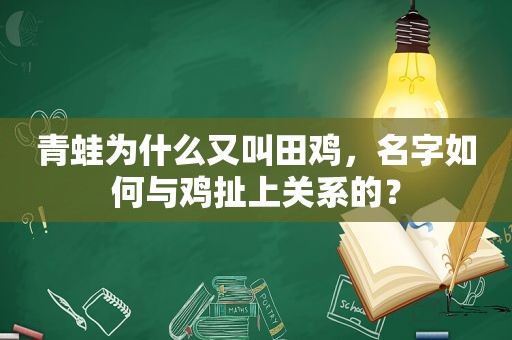
【科普版在前,专业版见文末】
[科普版]
注意:下文中,写在斜线//里的是国际音标,没有斜线框住的是各类拼音和转写。汉语拼音的g相当于国际音标的k,汉语拼音的k相当于国际音标的kh。阅读时敬请留意。
虽然文中使用了国际音标和各类术语,对一些读者比较陌生,但是内容引用了汉语拼音和各地方言,大家可以结合普通话和自己的方言快速理解。
前面有一些回答对田鸡的品种进行了解说,指出田鸡与一般的青蛙有所不同。但我们在考虑一个词汇的读音和来源等历史脉络时,不能局限于当代的解释。如同大家熟悉的“穷”,古作完结、极尽的意思(“欲穷千里目”),今作贫困的意思(“穷人”)。这就是词汇在历史使用中的嬗变。名词也会发生意义的改变或挪用,如“谷”(穀),本指粟,今多指稻谷;“脚”本指小腿,今一般指足部;“肚”,本指胃,今一般指腹部,仅“猪肚”等个别词汇保留原意(并且在“猪肚”这个词汇中保留了较早的读音dǔ[当古切],而dù[徒古切]是后起的读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析田鸡和青蛙的语义和读音的关系,不能按生物学或养殖学上的分类截然分开。
我先放结论:田鸡的“鸡”是“蛙”的另一个读音
在分析历史资料之前,提示大家一下。“蛙”(本作“䖯”),是一个形声字,形旁是“虫”,表示它的类别,声旁是“圭”表示它的读音。可是在我们绝大多数汉语方言中,“圭”和“蛙”的读音都差得太远了,好像看不出什么读音关系。不过,在有些方言里面,我们发现“圭”和“鸡”的读音倒是有些许关系。比如广州话:圭 gwai ~ 鸡 gai;潮州话:圭 gui ~ 鸡 goi;客家话:圭 gui ~ 鸡 gai。是不是通过“圭”,我们好像隐约把蛙~圭~鸡联系起来了?
好了,有了这个思路,我们把“蛙~圭~鸡”的历史正统音韵资料翻出来。
我们看到,在唐宋时期,蛙有两个读音,相互比较接近,后世逐渐合流为一个读音,接近/ua/;从唐宋以来,圭和鸡的读音一直比较接近,主要差别是一个介音u,术语叫“合口”。因此,我们要理清蛙~圭~鸡的关系,需要说明蛙~圭,圭~鸡,这两组关系。我们先说简单的圭~鸡,再讲复杂的蛙~圭。
一、圭~鸡的关系:合口丢失
圭和鸡,前面已经说了主要是一个介音u,即合口的差别,现代广州话就表现为guai~gai的关系。事实上,从古至今,丢失合口介音u,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随便举几个例子:
上海话:推 /the/,对 /te/,醉 /tse/
苏州话:税 /se/,瑞 /ze/,村 /tshen/
成都话:胯 /kha/,皴 /tshǝn/,炖 /tǝn/,(老派)轮 /lǝn/,寸 /tshǝn/,匡 /tɕhaŋ/
广州话:瘸 /khe/,尾 /mei/,役 /jik/
北京话:内 nèi,尹 yĭn,沿 yán,扽 dèn
上面这些字按古典韵书都应该有介音u,实际上各方言交叉比对,也能看出其中的介音u成分,但是在各方言上述用例中却各有特色地失落了合口成分。因此,假设有一个字读音曾经和“圭”接近,在历史演变中变得和“鸡”接近,不仅是有可能,而且也符合汉语音韵的历史变化。
普通话中的“季”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可作类比。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蒙古字韵》的时代,“季”还与“桂”同音,与“记”不同,到了《洪武正韵笺》的时代,“季”就变得与“桂”读音不同,而与“记”读音相同了。而在现代各方言中,“季”就表现为有些方言里和“记”同音,有些方言里和“桂”同音。
到这一步,我们推导出了一半:圭~鸡,有读音上圭有转向鸡的可能。
二、蛙~圭的关系:上古汉语
相信很多对古代汉语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汉字的历史读音与现代汉语不同。所谓某汉语方言保留了“古读音”,只是某些语音特征相较其他方言丢失的特征而言。比如广州话入声韵尾较齐全,苏州话声母清浊区分明显,厦门话没有f声母,北京话“森、心、深”不同音等等。那古代汉语读音是什么面貌呢,很多朋友是通过“上古汉语配音《封神榜》” 有直观感受的。这段配音大约有十年时间了,读音现在看来有一些问题,但是给大家的直观感受是大致正确的(配音的大神们现在依然还各种活跃哟)。
上古时代的汉语读音,我们已经不能完全复原了。但是根据后世的体系和其他历史资料,我们能找出上古时代汉语读音体系的大概框架。这也是前面《封神榜》配音的来源。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很多学者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把这个工作称作“拟音”。我个人自认是郑张潘派(郑张尚芳-潘悟云)。在郑张潘的体系中,“蛙”有两个读音(这和上面说《广韵》记载两个读音相对应):
/qʷraː/
/qʷreː/为什么会拟成这样,我这边没法全部解释,要涉及太多专业背景知识,我们这边只用来看看读音。
这里的/q/不是汉语拼音,是国际音标,学名叫“不送气清小舌塞音”,是喉部深处发音。和汉语拼音g的读音听感上略有点相似。 *** 语这个辅音很常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 *** 尔语、哈萨克语、苗语、羌语等都有这个辅音。这里放一个苗语的视频给大家作个直观感受。 其中43:05讲解的这个苗语拼音gh,即是/q/。
上面的小w就是所谓“合口”成分,大致与我们说的介音-u-类似。上面的r是一个弹舌音,一般认为是大舌音颤音。(不清楚的同学看这里,在1:20处)。至于/ː/,这是长音的意思。
这些音连在一起,读出来其实就很像青蛙的叫声,第一个像“咕啦”,第二个像“咕勒”。这也符合语言早期词汇以声为名的特点。(在上面配音《封神榜》里,2:05开始有“娲”,就拟作/kroːl/,已经有点像蛙叫了-_-|||)。
而“圭”呢,这是上古一直常用的玉器,我们的拟音为
/kʷe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上古拟音的体系内,“圭”和“蛙”确实是读音接近的(考虑到/k/与/q/发音部位和听感都接近)。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蛙”和“圭”联系起来。
三、蛙变鸡:文白异读
我们已经把蛙~圭~鸡联系起来了。不过,相信细心的朋友还有疑问:饶是三字有联系,蛙不是好端端地读wa吗,怎么又读鸡了?
我们在这里引入文白异读的概念。在汉语各方言中普遍存在一个字有两个不同读音,用于不同词汇的情况。特别是较书面的词汇与口语中的词汇读音有差异。我们举几个例子:
上海话:人(zen)民广场——上海人(nin);肥(vi)胖——肥(bi)皂
广州话:命(ming)令——好命(meng);近(gan)代——远近(kan)
成都话:惊吓(xa)——吓(ha)人;睡觉(jao)——睡觉觉(gao)[儿语]
厦门话:大人(/tai jin/)[尊称]——大人(/tua laŋ/)[成人];
北京话:日薄(bó)西山——薄(báo)[厚度];孔雀(què)——家雀(qiăo)[麻雀]
上面的例子里面,成对的词汇中,前者是文读后者是白读。一般来说,文读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体系传承,系统性较好。白读是民众的口语,口口相传,虽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自由度较大,有些情况下,即使有一些规律但也与大部队不同,所以也可以用“荒腔走板”来形容。比如长沙话“mia黑”,mia是墨的白读;广州话“瞓(fan)觉”,瞓是困的白读;北京话“来qiě了”,qiě是客的白读;成都话“ha儿”,ha是傻的白读,等等。
蛙字在读音/qʷraː/、/qʷreː/在历史上一直和其他字的读音一起成体系地发生历史变化,书面记录下来之后,就是体现在前面列表中各个历史时期韵书的记载。但是韵书没有记载下来的乡野口语却按自己的逻辑在演变。前面已经说了/q/和/k/很接近,/qʷreː/这个音变成/kʷreː/,是分分钟的事情。前面又说了合口容易丢失,于是变成/kreː/这一类的读音。好了,大家知道我们拟出来的鸡的上古读音是什么吗?是/keː/哦!下一步的合流就更加容易了。
当然,这里是把这个音变过程简化了,并不是明确说在上古或者在具体某个时期,蛙的白读音与鸡合流了,只是大致指出了蛙的白读音与鸡合流的走向。
白读的蛙与鸡同音之后,需要加以区别,于是有了“田鸡”的称呼。如同有些方言里,雁与燕变得同音之后,便用大雁和燕子来区分。
汉语历史音变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要充分理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是大家也可以在我上面的介绍中了解一个大概内容。
下面是思考题:
1. 北京话“脖梗”(脖子)的“梗”是什么意思?
2. 上海话“白乌龟”(鹅)真的是从乌龟来的吗?
3. 很多地区方言称蟾蜍为“癞格宝”或者类似的音,这是什么意思?
答案:
1.“脖梗”就是“脖颈”,梗是颈的白读
2.“白乌龟”不是乌龟,是来自“乌鬼”,乌鬼是鸬鹚的意思。乌鬼的鬼可能也不是本字,也许是与“雎鸠”这个词汇有关系。
3.“格宝”就是“蛤蟆”这个词的口语变音。不过可能关系没那么直接,这里不细说。需要说明的是蛤字与我们这里讨论的蛙作鸡也很可能是有关系的,想想“圭”(蛙)~“格”(癞格宝)。
[专业版]
《广韵》蛙有二读,其中之一“影母佳韵平聲二等合口”推导上古音/qʷreː/,在历史白读音中,小舌音塞音转喉音,丢失合口,介音r丢失或转半元音j,即迅速与鸡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