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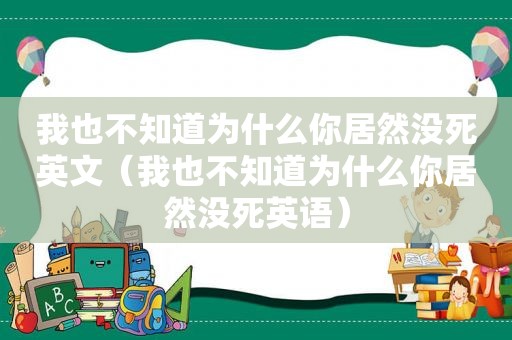
在入殓师的“职业文化”中,握手、递名片、说“你好”等都是他们的社交禁忌。
这些“不成文规定”折射出的,其实是人们对于从事殡葬行业人员的忌讳与误解。
长久以来,入殓师都被“不吉利”、“晦气”、“恐怖”等词汇形容着。这源于众人对该行业的陌生,同时也因对于死亡的天然恐惧。
在别人眼中,入殓师是谈起“死”字都可以轻描淡写的冷酷人物。
但站在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他们反而更容易看到生命的形态。
差不多10年前,武汉的地下摇滚圈里流行着一支名为“消逝的河流”的重金属乐队。
乐队的组建者叫杜威,70后,擅长创作及演绎死亡重金属类音乐,凶猛、疯狂、毁灭是其歌中最常见的元素。
每当夜幕降临,杜威都会背起吉他和成员走入酒吧,血脉贲张的音乐响起,他觉得自己是一头在人群中极速狂奔的巨大野兽,那是一种“灵魂出窍”的 *** 。
喝酒、蹦迪、唱摇滚,在城市很难被注意到的角落里,杜威尽情狂欢,这样的叛逆他只有在黑夜才会展示。而在天亮时,他将走出狂躁的酒吧,换上一身得体的衣服,然后走进一间极为清冷的屋子——殡仪馆,杜威在那里工作。
一半摇滚人,一半入殓师。
杜威的经历听起来极为分裂,可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生活组成并不矛盾,“摇滚”和“殡仪”其实都是人生。
入殓师 杜威
杜威打小就不爱学习,热衷于在学校打架斗殴,同学和老师都将其视为“危险分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摇滚乐正流行,恰好碰上了叛逆少年杜威。两者一拍即合,很多故事便有了开端。
一天,杜威收到了哥哥送来的唐朝乐队的专辑。音乐响起时,杜威瞬间浑身颤栗、呆若木鸡。盯着磁带封面上几位穿着黑衣的长发男人,杜威终于找到了与世界对抗的力量。
愤怒、反抗。
摇滚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杜威人生的重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在日后,也成为了他踏进殡葬行业的契机。
“摇滚青年”杜威(中间)
上职业高中时,杜威学习烹饪。本想日后做餐饮当大厨,结果打工第一天就因“脾气不好”把厨师长给揍了,他毕业就失业了。
为此,杜威和父亲爆发了一次极大规模的争吵。前者不满长辈的指手画脚,后者指责儿子好吃懒做。矛盾中,杜威愤怒离家。在朋友的酒吧里,他组起了乐队,继续从前的摇滚梦。
那时,杜威有一位名为彭坦的队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共同在日夜颠倒的生活里思考生命和死亡。
几年后,彭坦组成了达达乐队,而热爱“死亡重金属”的杜威,则走上了另一条表达与描绘“死亡”的道路。
杜威与乐队成员在陵园拍摄的合影
杜威不怕“死”,自小便如此。
儿时他喜欢体验“恐怖”,如若在路边见到小动物的尸体,他还会凑上前研究,想着可不可以用电击复活死去的生命。
杜威曾一度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可当得知父亲因糖尿病住院时,他的这份笃定被瞬间击碎,也是在那时,他开始认真思考“安稳”对于生活的意义。
1997年,在母亲的反复建议下,杜威参与并通过了当地公职就业资格考试。当“福利院文职”和“殡仪馆火化工”两个职位摆在面前时,杜威因不想和母亲做同事,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那一年,杜威20岁,热爱反抗,却主动进入了世间唯一不存在“反抗”的地方。
没有人能拒绝死亡。
小时候的杜威和母亲
在成为专业入殓师的这条路上,杜威表现得极为主动。
最初入行时,他会主动学习防腐整容技术,也会积极钻研遗体复原技巧。如今,即使是已经成为业内极有声望的前辈,他仍保持着提早上班的习惯。
早上六点,在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前,杜威会先通过“遗体专用通道”走向冷藏间,核对前一晚送来的遗体信息。
因为时间尚早,殡仪馆内人不多。初升的太阳也极为懂事,只小心停留在通道门口,便不再向前。
从远处看,杜威正一步步走向冰冷的停尸间,而身后光影划分出的就是生死两界。
杜威时常想,这其实也是“死亡”的表现之一:
太阳总会升起的,无论如何都会升起的,可有人永远停在了昨天。
作为一名专业入殓师,杜威的工作通常包括帮助逝者清洁、 *** 、化妆、穿衣,有时也要对遗体进行修复。这之后,逝者将被送入已经装饰好的木棺中,而后推入礼堂与家人、亲友一一告别。
入行多年,杜威对于这套流程极为熟悉,所以很难每次都在其中找到悲伤的情绪。
他不惧怕死亡,因为真正让他感到极为无力的,其实是“死亡”背后的故事。
正在为逝者化妆的杜威
在杜威面对的诸多逝者中,那些选择自杀的年轻人,让他难以释怀。
多年来,每当面对它们时,杜威都会忍不住在心里想象逝者生前的生活,然后再从外界传递出的只言片语,拼凑逝者决定作别人间的理由。
感情、事业、家庭、疾病,还有一些到最后也找不到的理由……很多东西都会成为压死这些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起先杜威不理解,后来听到的无奈太多了,他也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执拗: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战斗,有人守得云开见月明,有人却注定无法修成正果,一人一个活法。
根据这些故事,杜威写出《坠入湮灭之门》,在那里他说:
“万念皆可灰,深不可测。”
为“死亡”呐喊的摇滚杜威
对于杜威来讲,摇滚是一个无法割舍的信念。
2013年之前,杜威曾先后组成3支乐队,但最终都随着逐渐落寞的中国摇滚乐,慢慢成为了“消逝的河流”。
在还能留着长发、穿着破洞牛仔裤、背着吉他呐喊时,杜威时常会把一些工作中的感悟写进歌中。
那些歌词和曲调绝大多数阐述“死亡”和“人性”,极为露骨和大胆,却也实在震撼心灵。
唱摇滚的杜威(右一)
杜威始终记得一场工地高坠事故。
当时,一部满载粉刷工人的升降机在上升过程中突然失控。电梯在飞速上升到顶层34楼后,钢绳忽然断裂,箱体直接坠向了地面,在场19人无一生还。
事故发生后,遇难者遗体被火速送往了杜威所在的殡仪馆内。那一天,杜威与同事们运用专业手法将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遗体逐一清理、修复、穿衣。
在缝合伤口时,杜威的脑海中一直回荡着carcass(英国金属乐队)的某首悲伤的乐章。
在这些遇难者中,有4对离家打工的夫妻。杜威很难不去想象他们背后的故事,也无法忽略生者的眼泪。
站在死亡的阴影里,即使外界万籁俱寂,他也能听见一些来自心底的呐喊和哭泣。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但在意外到来前,人们永远相信“明天优先”。
事故电梯已经散架
电梯事故之后,杜威开始留意很多东西。关于逝者,也关于生者,于是“怜悯”开始如影随形。
一次,一位男性死者被送进殡仪馆。在核实逝者身份时,杜威得知对方是外来务工人员。按照规定,在家属赶到武汉办理相关手续前,杜威除了等待什么都不能做。
那天,逝者的妻子带着小女儿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来。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次会面,那天等待这个三口之家的不是团圆的喜悦,而是死别的悲痛。
逝者因意外去世,所以“遗体状态并不算好,支离破碎的”。杜威向逝者的妻子建议,可以待遗体修复完成后,再让小女儿与父亲“见面”。
当时,单纯的修复费用在3000到10000元,可家属却因意外涉及纠纷未得到任何赔偿。大几千的殓葬费成了母女迈不过去的坎,左思右想后,母亲决定放弃杜威的提议。
对于很多人来讲,体面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是一种奢侈。
杜威对这样的局面并不陌生。他原本可以尊重家属意愿一走了之,可在看到逝者的女儿时,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如果见父亲最后一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一定会给这个孩子带来一生的阴影。这些东西会永远阴魂不散地陪伴她的一生。”
逝者已矣,可生者的人生或许才刚刚开始。杜威想,总不能让孩子的余生都抱着悲伤和恐惧入眠。
杜威在采访中谈起那对母女
那一天,在得到家属的同意后,杜威以教学的名义免费修复了那位逝者的遗体。
遗体火化后,那对母女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杜威不清楚她们日后的结局,甚至无法知晓女孩在见到父亲遗体时内心真实的感受。
他并不好奇,也不遗憾。类似这样没有回报和回应的会面,他经历了很多次,已习以为常。
逝者无声,生者无言。
身为入殓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关尊严和安慰,也明白这份特殊职业带来的,注定是沉默多于感谢。
毕竟很少有人会想到,在“死亡”这件事上,比起逝者,生者其实更需要体面和慰藉。
在儿子出生之后,杜威“摇滚音乐人”的身份也逐渐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模糊。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杜威终究还是离开了乐队,也很少再唱暴戾的摇滚。
2013年,决定专心搞事业的杜威考取了“国际运尸防腐整容资格证”,成为了武汉第三位获得该资质的入殓师。
他渐渐成为了殡仪馆内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同时也见到了更多的“死亡”。
杜威曾写过一首名为《瞬间》的歌曲,以此来祭奠那些在飞机失事中丧生的人们。
那时他倍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也清晰地感知到,由生迈向死,有时仅需要一瞬间。
“有人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虚无。”
说出这话时,杜威刚刚从“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现场返回家中,后来这次任务成了他生命中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现场
2015年,东方之星轮船在南京驶往重庆的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于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事件最终导致客船上442人罹难。
接到紧急调派任务通知时,杜威刚刚在医院结束了糖尿病的治疗,预备和儿子共度“六一”。得到消息后,他火速赶往了沉船现场,他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阴雨天。
杜威到达事发地时,已是深夜,接下来他要在遇难者家属赶到前,尽力将逝者恢复到“正常的样子”。
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救援现场图源:新华社
工作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
客船沉没后,尽管救援人员已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搜救和打捞工作,但过程所需的时间仍不算短。到了第二天,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很多遗体已经出现了 *** 的情况,有些已呈现“巨人观”。
为了隔绝遗体 *** 后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杜威和同事们不得 *** 上最高防护级别的隔离服和防毒面具。
可尽管如此,在连续工作超过30个小时之后,现场的入殓师们还是出现了呕吐、头疼等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
杜威(右一)与同事在客船沉没现场
整整6天的时间,杜威与其他14位同事陪着442位遇难者走完了在人间的最后一程。
劳累之外,入殓师们感触最深的却是一种无法言表,程度远超想象的无奈和悲伤。
在那次任务中,杜威曾亲眼看到一位入殓师为悲剧中最小的遇难者——一名3岁的女孩整理遗容。因为害怕弄疼孩子,那位90后小伙子的动作很轻,梳理头发时,他“连手都是颤抖的,生怕弄掉小女孩的一根头发”。
终于,在3名入殓师的共同协助下,孩子最后一次扎起了辫子。
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救援现场
那次任务之后,杜威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安稳入睡:
“(在沉船事故现场)我看到有的老人手上还有扑克牌。我就想当时这个老人可能还在很快乐地打牌;有的老人还拿着老花镜,有的……反正各种姿态吧。”
即使过了很久,杜威对于那一天的所见所闻仍耿耿于怀:
“看到受难者一批一批地送到面前,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做什么,怎样的努力、尽力,我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那种感觉才是真的「绝望」。”
杜威(右)在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现场参与沉船事件遗体修复工作时,杜威38岁,进入丧葬行业18年。在此前的6500多天里,他近乎日日与死亡打交道。
在很多时候,杜威都以为自己已是“刀枪不入”,可在大灾大难面前,他仍无法停止悲伤。很多东西和情绪都在时刻提醒着他:
每一则短暂故事的背后,都是一段很长、很沉重的人生。
在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都是别人做梦都想见到的人。
成为入殓师之后,杜威时常被朋友以“心狠手辣”形容。对此,他一笑了之,不仅不否定,仔细想来还觉得“有点道理”。
毕竟在所有人都忌讳提起的领域内工作,确实是一个极为凶险的选择。
在人生四门课“生、老、病、死”中,唯有“死亡”无法回避,且不允许“从头再来”,如此众人才会恐惧和抗拒。
工作中的杜威(右一)
在武昌殡仪馆内有一个专门存放3个月还未被火化的尸体的房间。这些逝者有些是因为客死他乡无人认领,有些是因为涉及的纠纷还未解决,家属坚决不同意火化。
没有人知道他们何时会被亲朋认领入土为安。为了方便管理,殡仪馆会将这些遗体的相关信息写到白板上并逐一编号。
平日里,很少有人会涉足这里,只有杜威会“时不时就过来打个招呼,看看这些老熟人”。有时看着一连串文字和数字之后的“无名”二字,他也会百感交集。
来时“无名”,死后“无名”,生命还真的是个轮回。
杜威检查逝者遗体存放情况
从事殡仪工作多年,杜威见过人间百态。他看到有的人上一秒还披麻戴孝为逝者嚎哭,下一秒走出遗体告别间就拿起电话争论遗产问题。
站立在阴阳两界,杜威看人间,也看人性。
在4年前,武汉当地火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
受害人是一间面馆的老板,案发地则是他经营了多年的小店。出事当天,一位顾客因结账时发现每碗面条涨价5角钱,而与老板发生激烈口角。混乱中,顾客挥刀砍向老板,一条生命就此陨落。
在调查中老板的“老顾客”称:面馆开了很多年,价格一直没有变化,直到案发前一天才涨了价。
当时发生凶案的面馆
老板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时,已是身首异处,杜威和同事们要做的,便是将其“复原”。
当时,杜威和同事们花了整整5个小时才完成了对逝者的遗体修复工作。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后,几位入殓师都没有说话。
一碗面,5角钱,一条人命,两个家庭。
如果面条的价格晚一天变动会怎样?
如果二人没有发生争吵会如何?
如果当事双方都忍住了那句让对方忍无可忍的话,那一切会不会还有转机?
可是,人生哪里有“如果”呢?
受害者生前租住的房屋,屋内满是生活的气息
惨案发生时,受害人42岁,家中母亲失聪,父亲患有心脏病,12岁的儿子刚上初中。
那天,老板的妹妹陪同父亲从家乡赶到武汉。路上,妹妹谎称哥哥是因病去世的,老人虽并不相信,但在看见儿子还算安详的遗容后,他只是沉默了许久,然后转身离开,步履蹒跚。
父子一场,这将是老人家与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没有叮嘱,没有对话,甚至没有告别。
在后续的报道中,受害人的妹妹说:
他们的家乡在农村,哥哥经营的面馆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此之前,他做过苦力,离过婚,还因做买卖欠下几十万的外债。
哥哥是个勤快人,为了能多挣钱,他通常清晨4点便起床,晚上10点才收摊。事发前,哥哥好像有心事,但至于是什么心事,她不得而知,往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受害者老家的房子,他的母亲站在门口,那时还不知道儿子死亡的消息图片由当地村民提供
截至今年,杜威已成为入殓师24年。
在这几十年中,他看到有人离开这个行业,也看到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
如今,随着一些院校开始设立相关专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入殓师。在他们中,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是因为兴趣,还有的则是因为家人的后事办得并不理想,想借此弥补遗憾。
相比于老一辈从民间丧葬行业走出的入殓师,年轻的后辈身上多了一份科班出身的专业。
这些年轻人会试着揣摩逝者无法说出口的心愿,也会尝试以更柔软的心去体谅生者的悲痛。他们更加感性,也更喜欢去思考一些有关人生的话题。
杜威与年轻人交流经验
在和这些年轻人的相处中,杜威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其实都是为“生者”准备的。
人死了就像水溶进水里。所有的悲伤、痛苦、心酸、无奈都是生者给予“死亡”的定义。
为逝者还原未死之状,这是杜威及其他入殓师们的工作。
他们不是在装饰“死亡”,而是在抚慰“生命”。而那些所谓给予逝者的,宏大而壮观的体面,也不过是为了告诉活着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永远离去,请记得我最美的样子,然后放下悲伤,带着思念,勇敢继续往后的人生。”
在杜威经手的多个入殓工作中,一位女儿的“特殊要求”让他记忆深刻。
当时,年逾八十的母亲因病去世,女儿在入殓前向杜威提出请求,希望可以把母亲的面容恢复到30岁左右的样子。
杜威不解,追问原因。女人解释到:
自己的童年并不美好,父亲家暴,母亲忍受多年后,终于提出离婚,带着年幼的女儿外出生活。当时的日子很苦,母亲很累,就连老去的速度都比别人更快一点。
记忆中,母亲最漂亮的时候就在30岁。如果可以,她想再看看母亲最美的样子。
那一天,杜威用尽所学完成了女人的愿望。正式入殓前,女儿见到了“30岁的母亲”,她和母亲说了很久的话,而后静静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