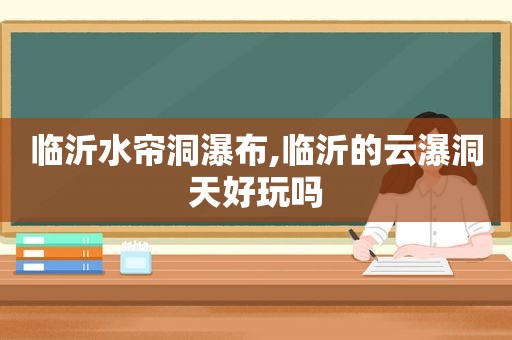本
文
摘
要

香港有这么几家理发店:
第一家名叫“乐群理发”,主打复古风格。它坐落在文创园区广场的一隅,墙上挂着猫王海报和许多黑白照片,墙角的电唱机正放着爵士乐。店主是个年轻人,他只剪六种复古美式发型。
第二家也叫“乐群理发”,它搭建在居民区的街巷口。店内空间十分老旧、局促。店主是一位脸色干黄的、头发快要掉光的老人。他剪的发型十分简易、很好打理,且价格实惠。
第三家叫“孔雀”,它是会员制的高级发廊。有富丽堂皇的装修,出入的都是达官巨贾、名人士绅。
第四家叫“温莎”,它以西方绅士的剪影为标牌,理发师傅们都穿着枣红色的制服,各司其职,服务到位,十分讲究。
你会选择哪一家到理发?
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飞发》,讲述的就是这样几家理发店和理发师的故事。
叙事:理发店与理发师
“飞发”在粤语中是“理发”的意思,原为“fit发”,把fit读得更轻灵,便成“飞”。fit的核心内涵是“使之合适”,把头发修整得合适,正好跟“理”相符。
葛亮称:“《飞发》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写一群人对自己行业的信仰与坚守,也在关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代际等问题。”前面提到的四家理发店,正是出现在不同时代的、由不同代际的理发师主导的产物。
葛亮:作家、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
小说从“我”意外到翟康然(阿康)的理发店开始,引出阿康的父亲翟玉成,继而牵扯出后者的人生旧事和父子矛盾。
翟玉成年轻时,发廊是整个香港最潮的地方。在女富商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名为“孔雀”的高级理发公司。但好景不长,一场席卷整个香港的股市风暴打碎了他的人生幻梦。破产的翟玉成只能选择在巷口开一家简陋的理发店维持生计,从此放下过去的光鲜亮丽,只剪最便捷、最普通的发型。
儿子阿康长大后,出于对父亲的叛逆和对新潮的追逐,他转投庄锦明的“温莎”理发店,父子关系因此破裂。学成后,阿康以父亲的店为名,开了自己的“乐群理发”。
“温莎”理发店是一家上海理发店。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上海理发师傅凭借“顾客至上”的原则甚至价格的高昂,形成了某种洋派传统的仪式感和壁垒分明的阶层标志。到“温莎”开店时,上海理发已过了盛时。但“温莎”在有限度地保留一贯的服务与形式的前提下,让普通人得以平价享受从未体验过的飞发排场,吸引到了许多顾客。
小说结尾,在翟玉成的弥留之际,庄锦明为他理了最后一次头发,随之决定关店退休。四家理发店,只剩阿康一间。
人物:匠人的技艺与选择
这篇小说最早发布在《十月》杂志,后来被收入葛亮的小说集《瓦猫》。集内的小说都是有关“匠人”的故事。小说中三位不同代际与流派的理发匠人,有着各自的“匠”的造诣。
翟康然在用推刀时,神情会变得肃穆。他把自己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同步到理发事业当中:黑色的头发,用灰度做出层次,使头发在薄与厚之间,展现优美的渐变、结构、轮廓和光泽。
翟玉成的剃刀,不似锋刃,而像丝绸,在黑暗中也能熟练且清晰地在客人的颈项、两鬓间游走,很快就修剪出界限分明的头发。
庄锦明剪头发,不用电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剪刀如同长在他的手指间,流水行云,无须思考,一气呵成。
修剪头发就是在剪裁思想与生活。三位匠人呈现出的不同技艺,不仅是基于师徒传授、经验累积,也是观念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深入到人物内心的自我期许,作用到他们的行为选择。
阿康师承庄锦明,受到“海派”理发追求时髦的影响,又因其摄影师的出身和审美,对理发有着区别于前代人的艺术化的理解。而他的父亲翟玉成,则是传统“广式”理发规则的捍卫者。他经历过诸多风雨,以务实为准则,执拗于非黑即白的法度。
小说中,阿康为“我”剃出的渐变层次,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老派的年轻。而翟玉成修剪后的发型,则得到了年轻学生的认可。理发业的时尚趋势,又落入了新与旧的循环辩证之中。
全球化中,各种流行与风潮在很短时间内就可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大时代的宏阔背景下,个体难免被时代裹挟、吞没。理发师在时代变迁之际的路径改造和秩序坚守,都是“匠人”的精神所在。顺应潮流,亦或坚守传统,并无对错之分,但行业的变迁和从业者的命运支撑起了大时代的走向。
城市:想象中的老香港
葛亮对理发业与理发师的叙述,指向的是香港的时代变迁。人物命运与时代动荡共振,钩沉出香港的风云过往。
岁月静默,唯器能言。葛亮说,“匠人”是历史的一枚切片,而“物”是这枚切片上那道深入肌理的锋刃。并非香港土著的他,在进行城市书写时,常常用一种“格物”的方式,将器物背后的时间、记忆与文化想象进行文字塑形。
香港北角一带的唐楼建筑、放着爵士乐的电唱机、“温莎”60年历史的皮质躺椅、理发师所用的老式剃刀……都是葛亮用以想象老香港的“物”。它们像一枚小小的切片,经过叙事与人物的放大,就能从中窥探到过去的肌理。葛亮在“格物”的基础上,挖掘出一段段真实而立体的故事,最终将遥远的怀旧感还原为身边的烟火气,通向一个由他所创造的具象香港。
不管是翟玉成、庄锦明和阿康的人生经历,理发业的发展变迁,还是北角街区的一隅,都是葛亮提取的样本,目的在于对香港这座城市的风貌与历史进行书写。
葛亮的“格物”策略在小说中有直接的呈现。阿康在听到上海歌后白光的歌声时,仿佛看到了他从未去过的老上海——摩肩接踵的大厦、外滩一望无际的灯光、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水、远方传来的鸣船汽笛声、拥在一起舞蹈的男女……在这里,葛亮的香港想象与上海想象实现了一次重叠。
想象中的老香港与现实世界,在小说的章节中反复轮转。凝望春秧街唐楼外墙上的斑驳痕迹,读者可将目光对准这里几十年前的光景:留着椰壳头的青年,伴着“叮叮当当”的电车声,走过面粉厂、南货店以及果栏,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小说还在故事的主干情节之外,增加了几个章节,以考据的形式介绍“飞发”含义、业内行话及“三色灯柱”典故。
这种过去与现在、故事与考据的不断切换,事实上造成了一种离间效果,将读者从叙事中抽离出来,让他们用旁观的视角去看待这枚历史切片。怀旧的距离感与现实的真切感,使读者透过语言和结构的表象、越过代际区别与审美差异,感触社会变迁的脉动、领略香港复杂的文化魅力。
像是北角官立中学的参天榕树与不协调的翻新运动设施,新旧杂糅、华洋交织,便是香港文化的核心特质。
你想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的?
阅读《飞发》,看看葛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