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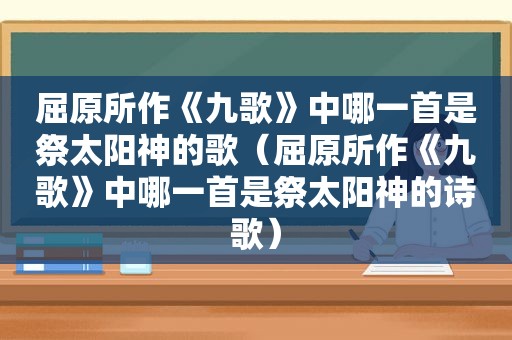
所谓东亚大陆的历史真相,还是很不清晰·。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今日对照考古史料,可以发现存在许多漏洞。起码楚国楚地的历史,就完全不清晰不明白·。屈原的九歌,就是证明。
屈原的《九歌》涉及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及国殇等十种神祇,与《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楚巫祭祀的神祇相比,两者差距实在太大,除“司命”相近外,其余无一吻合,因此,学者们对《九歌》中的神祇的来源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到底谁在编故事?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楚国故都郢(今湖北荆州西)发掘了数以千计的战国时代的楚国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战国竹简的出土,这些竹简文献为研究楚辞《九歌》中神祇的国籍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新材料。
其中天星观一号楚墓、望山一号楚墓及包山二号等三座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墓中出土了丰富的反映楚国贵族祭祀情况的占卜、祭祀类竹简,为我们揭开《九歌》神祇身份之谜提供了实证。望山墓主悼固生前占卜的主要内容有三:卜问事从楚王、大夫是否顺利,能否获得爵位;卜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侍候楚王是否顺畅;悼固的身体状况很差,有心脏病,哮喘严重,腿脚还有病,多次卜问身患的疾病能否好转。
悼固祭祀的神祇数量众多,可分为三类:天神有太、司命;地祇有大水、宫、宫地主、宫主、宫室、社、行、北方、南方;人鬼最多,包括祖先神灵、同辈或晚辈的亲友神灵及非正常死亡的殇鬼:老僮、祝融、鬻熊、简王、声王、悼王、哲王、二王、明祖、亲父、北宗、北子、王孙巢、王孙喿、栽陵君、逨、不辜、不壮死等。
1978年发掘的天星观一号墓西距楚国故都郢(纪南城)30公里,是目前已发掘的纪南城周边地区楚墓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座,棺椁形制保存完好,出土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七十余枚保存祭祀、占卜记录的竹简。
学者们注意到卜辞中有一个重要的纪年“秦客公孙央闻(问)王于栽郢之岁,十月,丙戌之日,醢丁以长保为邸阳君番胜卜贞,侍王……”,公孙央就是商鞅,因此断定天星观墓葬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61~340年之间,即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
祷告的祖先有“卓公”、“惠公”,祭祀的神祇有“司命”、“司祸”、“云君”、“大水”、“东城未人”等[2],可谓天神、地祇、人鬼俱全。与《九歌》中神祇近的有“司命”、“云君”,《九歌》中的其他神祇没有出现。
包山二号墓位于纪南城北16公里处,墓主是楚国中央 *** 主管司法的左尹邵陀,是楚昭王的后代,位居大夫行列,与屈原担任的左徒之秩相近,下葬于公元前316年,即楚怀王13年。墓主邵陀与楚王室同宗,又位居高官,其祭祀的神祇最具有代表性。
从以上选出的占卜、祭祀记录可以知道他祭祀的天神有太(蚀太)司命、司禄、日、月、岁;地祇有:后土、宫、宫室、宫地主、宫后土、野地主、地主、行、社、夕山、五山、高丘、下丘、大水、南方、户、灶、室、门;人鬼有:人禹、老僮、鬻熊、祝融、自熊绎至武王的楚国君主、二天子、明祖、没人、无后者、不歹古、兵死、昭王、文坪夜君、郡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夫人、邵良、邵{J2R409.JPG}、县貉公东陵连嚣。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楚国贵族崇拜天神太一、司命、太阳、月亮和岁星;祭祀的地祇特别多,有后土、社、地主等二十多种,包括土地、房屋、路、山、水等神祇;楚人特别重视祭祀人鬼,崇敬祖先、亲友神灵。总之,楚人有着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对活着的人都会产生影响。
======================================
那东皇太一究竟什么模样?我们先来从王堆3 号汉墓出土的一幅丝帛《“太一将行”图》说起。这幅帛画左侧题记中有“大一将行”(“大一”即“太一”,下同)的记载,其画面正中,头上有角的便是“太一”。虽学术界对此画到底画的是谁还有些争论,比如周世荣认为主像是“社神”,李学勤认为“大一”是“天一”,但在未有更明确的指向性的结论的得出之前,主流学术界仍认为此画中的主神既是“太一”。
B8%9B%E7%94%BB%E3%80%8A%E2%80%9C%E5%A4%AA%E4%B8%80%E5%B0%86%E8%A1%8C%E2%80%9D%E5%9B%BE%E3%80%8B.jpg
西汉,丝帛质地。 长43.5厘米,宽45厘米。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该帛画是一幅与“太一”等神祇有关的巫术图画。上部正中绘一个头戴鹿角的神祇,据其左侧题记推断,可能为“太一”神;如据其腋下的“社”字推断,则又可能是社神。
在这位神祇的下方,每边有两个神祇。“太一”胯下还有一黄首青龙,此龙的左右两侧还各绘一龙。整个画面表现神祇出行景象,具有浓厚的神话气氛。此帛画的寓意,学术界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它的用途是墓主人生前出征打仗前祭祷“太一”神,以祈求战争胜利的兵祷。“太一”一词出现在战国中期。
从传世文献来看,“太一”出现最早的应该是在《楚辞》等书中。至汉代成为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神。此帛画的出土证明了战国中后期以来“太一”崇拜的流行。
有学者经研究指出:近几十年以来,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战国时代楚墓中出土的一种形状诡异的镇墓神其实就是太一神。其理由是:镇墓神仅见于原楚国地区,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这种器物从战国早期到中晚期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并且始终都具有两个相同的特点:一、都插有两支鹿角。二、固定在方形底座之上。早期的形体简单,分头、颈、身三部分,头上无器官,大约还处于草创阶段;中期趋于复杂,有些还变为双头,有巨眼大口,长舌外伸;晚期头部由兽形转化为人形,其他特点保留。长沙是楚国故地,因此帛画的太一神就是从这种镇墓神的晚期形态演化而来,两者是同一神抵的偶象。镇墓神的长角是阳气的象征。口伸长舌有两个意义。一是象征地生万物,二是象征语言,太一是万物之本,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又包罗万象的正是语言。http://img.mp.sohu.com/upload/20170720/9f197d6a315e416496db420780fd5182_th.png
木雕双头镇墓兽,战国,荆州博物馆藏 木雕双头镇墓兽,战国,荆州博物馆藏
对于推断此类镇墓兽便是“太一”,其理由是:此类镇墓神仅见于原楚国地区,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种器物从战国早期到中晚期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并且始终都具有两个相同的特点:一、都插有两支鹿角。二、固定在方形底座之上。早期的形体简单,分头、颈、身三部分,头上无器官,大约还处于草创阶段;中期趋于复杂,有些还变为双头,有巨眼大口,长舌外伸;
=================================
1957年春末夏初发掘的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曾轰动一时。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座墓的发掘简报中说:“在镇(指长台关)的西北约四公里有一条小土岗,由西南延向东北,到十字港入淮河处为止。岗上散布着六个大土塚;传说的楚王城和太子城就在这条岗的东北部。”一号楚墓是这六个大土塚中的“第四座土塚”,(由东北端数起)[1]。这件口吐长舌、双眼鼓突、头插鹿角的”镇墓兽“就出自第四座土塚。
“镇墓兽”呈怪兽形,龇牙咧嘴,头身部扁平,为蹲坐状,兽头顶插两支彩绘鹿角,两耳翘起,双目圆睁,吐长舌至腹,胸部绘双乳,背面雕有四个对称的卷云纹,上肢上举,双爪抓住口里咬的蛇,又用红、黄、褐等色漆绘眼、舌、耳、爪和鳞纹等,面目狰狞。从背面的卷云纹上看似乎像虎皮纹,但是其红色的大眼睛和高耸的鼻子又不太像虎,从其全身鳞状来看似乎暗示是个龙身。“镇墓兽”的前肢、后肢不是蹄形,呈爪状,手长如人弯曲的胳膊肘状。可以看出:长台关“镇墓兽”是混杂了鹿角、虎、龙、人的各个部分[2]。
文化解读
“镇墓兽”由兽形首、鹿角和方形座构成,方形底座四周雕刻或彩绘花纹,身躯置于方座正中,与底座套榫组合;头部为面目狰狞、吐舌利齿、突额瞪目的兽形或人形,有单、双头之分;头顶插有一对鹿角,鹿角少则几叉,多则十几叉。从战国早期到晚期,镇墓兽的头部和身躯有直身屈身、单头双头、兽面变人面、无舌变长舌、无颈变曲颈或长颈、狰狞变和善、兽面由彩绘变雕刻等变化。这种种变化无非都是渲染怪诞神秘的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转变,到战国末期镇墓兽形状变得简单,几乎流于形式,以至慢慢地消失了。
“镇墓兽”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现于长沙楚墓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广泛展开,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楚墓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漆器“镇墓兽”。漆器“镇墓兽”一般一墓只出一件,出两件者极罕见,均出土于有棺椁的墓中。出土位置大多在头箱,也有见于边箱的。且同时有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随葬,说明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这表明漆器“镇墓兽”是当时楚国贵族的随葬明器。
目前发现的楚国漆器“镇墓兽”在造型上有虽然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但总体来说,它们的形象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是同一种用途的丧葬明器。漆器“镇墓兽”的质地以木雕为主,其早期往往裸漆并加以彩绘,到了中后期漆器“镇墓兽”的面部轮廓则由彩绘变为雕刻。漆器“镇墓兽”是除楚墓以外其它战国墓中不多见的特殊之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 是典型的楚文化标志性器物,也是楚墓区别于中原东周墓的一个显著特征[3]。据考证,它从春秋晚期的楚墓中开始出现,但数量很少,到了楚漆器发达的战国中期,漆器“镇墓兽”的数量最多。在战国晚期又很少见,直至最后消失。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与当时楚国兴衰的历史是一致的。此种器物外形抽象,形象怪异,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战国早期,楚人墓室中设置镇墓兽,是为了守护死者,引导死者走向彼岸。到了战国中后期,龙凤升天题材成为主流,“镇墓兽”助死者升天的作用削弱,主要起到守护墓主的作用。本来在死者身边担当帮助死者升天和守护死者作用的“镇墓兽”被驱逐出墓室,变换成专一担任保护墓主的守护神[4]。
==================
图9:彩绘漆雕“镇墓兽”
彩绘漆雕镇墓兽(图9),战国晚期 ,通高73厘米, 宽110厘米 ,荆州刘永台M25:1出土 ,上海博物馆馆藏。
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之一种。此种器物外形抽象,构思谲诡奇特,形象恐怖怪诞,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
此镇墓兽出土于荆州江陵藤店一号战国楚墓,斫木胎,座上插单面兽头,口吐朱漆长舌,双目外凸,兽头上插双鹿角。通体髹黑漆,方座上绘朱、白彩兽面纹,兽身绘朱彩S形卷云纹和菱形纹等。
镇墓兽的基本形态由鹿角、兽形首、方形底座三部分拼合而成。鹿角插在兽首顶部孔内,兽身插在底座方孔内,多作长颈、鼓眼、口吐长舌状。其形制有单头、双头、变形龙面式、变形人面式等多种,多数单头,少数双头。从出土镇墓兽的排比中可以看出其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演变规律,大致是兽面渐变为人面,无舌渐变为长舌,无颈渐变为长颈,兽面由彩绘发展为雕刻。此种镇墓兽是除楚墓以外其它战国墓中不多见的特殊之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战国早期的楚墓中即有,但数量很少,楚漆器发达的战国中期,镇墓兽的数量最多,到战国晚期又很少见。这种数量上的消长变化应与当时漆器的发展趋势及楚国兴衰的历史是一致的。秦汉以后,这类器物逐渐消失。
通过以上出土实物资料可以看出,目前已出土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的“镇墓兽”形制大多比较简单,形体较矮,一般通体施黑漆,大多用木料雕刻,单头单身,插于盖状的漆木方体底座上,面目简单模糊,没有出现长舌,被认为是“镇墓兽”的一种初始状态,虽然已具备鹿角、兽面、方座这三种基本特征,但兽面的五官没有成形,处于漆器“镇墓兽”的雏形阶段。
战国中期,在继承战国早期形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单头兽面和双头兽面“镇墓兽”,形体高大,形象渐至完善复杂。此时的面部五官已由模糊不清渐变为兽面,头部的形状由圆变方,眉目的表现手法为彩绘或者雕刻,运用雕刻手法制作的漆器“镇墓兽”均具有突眼,卷眉,龇牙的特点,通身髹黑漆,身较短,没有纹饰。鹿角上绘有黑色卷云纹 *** 纹。颈部修饰有龙纹;身和方座绘有“S”形纹和几何云纹。木雕双头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给人一种狰狞恐怖的感觉。与前一时期的简单粗糙造型不同,这一时期的“镇墓兽”制作精美、形体高大、色彩艳丽、纹饰繁复。它们大多通体髹黑漆,然后用红、黄等颜色彩绘,其身上多饰卷云纹和龙纹。
战国晚期,不再出现双头兽面的形制,且面目重新回复简单。“镇墓兽”依旧头部两侧插鹿角,只是面部不似龙面,而近似人形,眼鼻运用雕刻手法,眼睛已成一条线,呈弯月形,鼻扁平,口微张,不见龇牙,感觉温和了很多。直颈,身细长,方座梯形面较矮,这点与战国中期的兽面型方座相同,只是在纹饰上简单了许多,上髹黑漆,没有彩绘。这一时期的漆器“镇墓兽”虽然在湖北江陵楚墓、湖南长沙楚墓都有出土,但从造型上来看有了变化,江陵楚墓中出土漆器“镇墓兽”保留了长舌造型,而长沙楚墓则没有,以将其完全演变为人的面部及上半身。方座也恢复到原始状态,造型非常简洁,没有运用更多的纹饰来装点。
漆器“镇墓兽”始出现于春秋晚期,消失于楚国衰亡之际,跨越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头部的形象与早期的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雕刻代替了彩绘,面部开始雕刻有五官,尤其是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漆器“镇墓兽”,其凶悍形象更是登峰造极。到战国晚期,头部由兽面向人面转变,面部像人了,直眉弯目,看上去较为和善,只是湖南长沙地区缺少了长舌这一特征,而江陵地区所出漆器“镇墓兽”依旧有长舌吐垂。
趣味猜想
漆器“镇墓兽”不是实用器,而是当时楚人敬奉的一种偶像,属于丧葬用品。那么,它是作为一种什么形象被制作出来的,这种木质偶像到底有什么含义,它的随葬和墓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
可以证明,司马迁的三皇五帝之故事,属于司马迁先生的一家之言。起码楚国数百年的历史,不是这样,否则鹿角的太一东皇崇拜,怎会在东亚大陆南方的楚国楚地延续数百年·?
==========================
可以证明,司马迁的三皇五帝之故事,属于司马迁先生的一家之言。起码楚国数百年的历史,不是这样,否则鹿角的太一东皇崇拜,怎会在东亚大陆南方的楚国楚地延续数百年
若没有确凿的材料来证明《九歌》非屈原所作,那么《九歌》的作者问题可分两方面来讨论:一是屈原直接创作了《九歌》;二是屈原对古乐《九歌》进行有选择的加工改造。
屈原对楚地的神祇进行加工入曲,仅凭推测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而《九歌》中所描绘的诸神也不是毫无选择,这就需要了解楚国的祭祀活动和所祀对象,楚国巫风盛行、神祇众多,而存世文献中记载又较为模糊,亦难窥其全貌。
然而,近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却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材料,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楚墓、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和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相继出土,不但解开了楚国上层人物进行占卜祭祀活动的情形,而且使所祀诸神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依托,经考古研究者认定,望山一号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昭固,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10]天星观一号的墓主是官至上卿的番勅,大约生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公元前340年前后),[11]包山二号的墓主是楚昭王后代昭佗,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12]从这些考古的结论来看,以上三墓主所处的时代恰与屈原生活的时期大体相仿,这样就可以藉此了解屈原时代的一些祭祀情况,尤其是竹简中记载了当时祭祀的诸神体系,这和《九歌》中所描写的部分神祇是相吻合的,汤漳平1984年撰写的《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已经注意到这一关系,汤漳平此文主要依据是望山一号和天星观一号楚墓,两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所反映的祭祀对象包括了先祖和自然神,自然神的名目与《九歌》中的诸神异中有同,但是所祀神的数目却比《九歌》要多得多,将两者比较后发现,大体相同的只有“司命”,而云中君、东君可以和竹简的“云君”配套;湘君、湘夫人和竹简的“东城夫人”配套,河伯跟竹简的“大水”、“后土”配套,
====================================
可以证明,司马迁的三皇五帝之故事,属于司马迁先生的一家之言。起码楚国数百年的历史,不是这样,否则鹿角的太一东皇崇拜,怎会在东亚大陆南方的楚国楚地延续数百年
《九歌》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楚怀王执政的三十年之内,除《国殇》的基调慷慨悲凉外,其他十篇大体上还是比较活泼优雅的,显然是屈原得意时的作品,郭沫若的看法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有学者说二《湘》、《山鬼》等是沅湘较偏僻的地方才能接触到,是沅湘民间的舞曲,郢都并没有这类粗鄙的歌舞,实际上,江陵楚墓和荆门包山楚墓竹简是有力的佐证,三座楚墓均出土于郢都附近,并且《包山楚墓》中记载了部分山川之神,如二天子、后土、大水、高丘、下丘等,这就说明并不是只有在沅湘才能看到这些舞曲,郢都的祀典中也有祭祀地方神祇的惯例,所以汤漳平认为:“《九歌》中诸神在郢都大都出现,这就否定了屈原只有流放到沅湘时才能见到这些祀神歌舞的成说。”[17]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九歌》产生于郢都的可能性。那么,《九歌》是屈原放逐沅湘时期的作品就逐渐失去说服力,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九歌》作于楚怀王时期,出土文献的部分资料也起到了有力的辩证和推动作用。
二、《九歌》的写作目的及其主题性质探讨
《九歌》的创作目的及主题性质历来聚讼不已,
王逸《九歌》序云:“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18]
王逸认定《九歌》是屈原放逐沅湘时期所作,因而在《九歌》注解中不但蕴含了屈原的情绪体验,而且也包括了王逸自己的兴寄思想,也即是通过“讽谏”表达忠君爱国,王逸之说有经学背景下的局限,但对后世影响很大。
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和朱熹《楚辞集注》中分别得到发挥,如洪氏言《云中君》:“此章以云神喻君,言君德与日月同明。故能周览天下,横被 *** ,而怀王不能如此,故心忧也。”[19]
朱熹也指出:“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楚辞辩证》)洪、朱二人的观点显然与王逸“忠君说”一脉相承。
而明代汪瑗《楚辞集解》虽承前人陈说,但他却意识到阐释《九歌》不可字字联系到“忧国之心”,“以写己意”才是屈子本心,过于挖掘微言大义,反而有损对《九歌》的作意探究。
清代蒋骥在汪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具体篇目应作具体分析,这使得《九歌》研究逐渐回归到文本的探究,所以,后来的学人越来越重视文本的考察,不再固守通过注解阐释微言大义,马茂元《楚辞选》指出:“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它所抽绎出来的坚贞高洁,缠绵哀怨之思,正是屈原长期放逐中的现实心情的自然流露。”
马茂元的观点已经看不到忠君爱国的迹象,而是关照屈原自身的情感遭际。因此,自王逸以来强加给《九歌》的忠君爱国说在新时期的研究中逐渐淡化,关照文本所体现的内涵是揭开《九歌》作意的直接途径,而综合运用民俗、文化、宗教、考古等多学科知识是现今学人通行的研究方法。
===============================
闻一多是此期《九歌》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研究结合民俗而提出《九歌》的经典化过程,最后指出《九歌》是“楚《郊祀歌》”,进而在《〈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中将其用歌舞剧的形式加以表现,[22]在闻一多这里已经将《九歌》提升到国家祭祀的级别,如对《东皇太一》的考释。
游国恩的观点又有所发挥,直接标明为国家的祀典而作,而在游国恩看来这个过程是以民间乐歌为前提的,“《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并取古代乐歌为名”。[23]这些观点主要是围绕民间的祭歌展开,对《九歌》作意的探讨是有启发意义的。
进入新时期,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域学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萧兵认为原始的《九歌》是一种降神祭鬼的巫术性乐舞,内容包括了男女欢会、神人交游,并且常常用来招风祈雨,而《楚辞》时代的《九歌》和原始《九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内容格调也比较浪漫、放荡和粗犷。[24]由于带有楚地民间巫术乐舞的痕迹,所以《九歌》中表现出的格调是较为放荡浪漫的。
龚维英的观点也大体相同,原始《九歌》的功用是“祈雨”,并有男欢女爱的暗示,而经屈原加工后,功能扩大到关于战争的告捷。[25]
《九歌》的地域民间文化方面,林河的研究较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表《〈九歌〉与沅湘的傩》、《〈九歌〉与南方民族傩文化的比较》两篇重要文章,并出版专著《〈九歌〉与沅湘民俗》一书,主要从民歌、方言等角度研究《九歌》和沅湘民族傩文化的同构性,由此而得出了“沅湘间的傩文化是哺育《九歌》的母乳,而《九歌》又是沅湘傩文化的最先著录”,[26]使《九歌》的民间性进一步明确化,尽管部分学者结合民俗文化、地域特色、人类学等研究成果,在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下关照《九歌》的创作意图,也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影响力的观点
但是《九歌》中所描绘神祇的祭祀资格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学者已经指出如“东皇太一”这类高规格的神祇是不可能由沅湘普通民众来祭祀的,由此而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国家祀典说”。
=============================
《九歌》为楚国的国家祀典一说产生较晚,清代林云铭《楚辞灯》认为《九歌》所祀山川之神是国家常祀的神祇,并非沅湘间民众所能够祭祀。
闻一多虽将其定位于“楚《郊祀歌》”,实质上已经承认是国家级别的祀典,陈子展也认为《九歌》当奉怀王命而作,也即是为楚国王室举行隆重的祀典而作。[27]上文游国恩也说到《九歌》是在民间祀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以上观点均注意到《九歌》中神祇的祭祀资格问题,以此反驳沅湘民间的祭歌说,
尤其是近年随着考古文献资料的充分挖掘和利用,增强了“国家祀典说”的论证力度,而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出土,又一次掀起了出土文献与《九歌》的研究热潮,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中考释出“太一”,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也提供了线索,这批竹简中发现了一篇珍贵的道家文献《太一生水》,而墓主大约生活于孟子和庄子时期,和屈原生活的时代也较为相近,这就说明“太一”在当时是存在的,
另外《庄子·天下篇》中出现过“太一”,宋玉《高唐赋》也有:“进纯牺,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一。”
刘信芳继而将包山楚墓竹简中的神祇同《九歌》中的神祇做一对应,把“后土”释为“云中君”,把“二天子”释为“湘君、湘夫人”等,但其中有的考证也失之偏颇,如将地神“后土”考释为天神“云中君”显然是证据不足的,因此,作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二者之间尚存有许多疑点,有待进一步探索”。[28]刘信芳此文主要考察了包山二号楚墓的一些情况,在论证方面缺少统观全局的联系,尚有讨论的余地。
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弥补了上述缺陷,汤漳平于1984年已经对江陵的楚墓竹简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辩证,当时荆门包山二号楚墓还未出土,仅就当时掌握的出土文献资料做了初步的研究,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而包山楚墓的出土提供了更多的神祇,使屈原时代的祭祀情况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展示。
三座楚墓的祭祀对象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完备的楚人祀神体系,而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留下了汉初的祀神情况,汤漳平将三座楚墓的神祇、《史记·封禅书》的神祇与《九歌》中所描绘的神祇做一细致的对比研究,发现《九歌》中的十神显然是屈原选择了诸神中的一部分,这种选择是根据祭祀的需要,并且三者的祭祀顺序都是相同的,即先祭天神、地祗,最后祭祀人鬼。
由此结合墓主的王族身份和《国殇》篇的特殊性,说明《九歌》中所祀神的规格是较高的,不是一般民众所能够祭祀,因此汤漳平认为:“《九歌》神系是楚王室的祭祀神系,这一点应当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么,它的产生地点也自然而然地得到确定,这就是它产生于楚国的郢都,所谓沅湘民歌说应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无根之谈。”[29]汤漳平的两篇重要文章对楚墓竹简与《九歌》诸神之间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至少在考辨和推理的方面做了实质性工作,为《九歌》的主题性质和作意探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开创了出土文献与《九歌》研究的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