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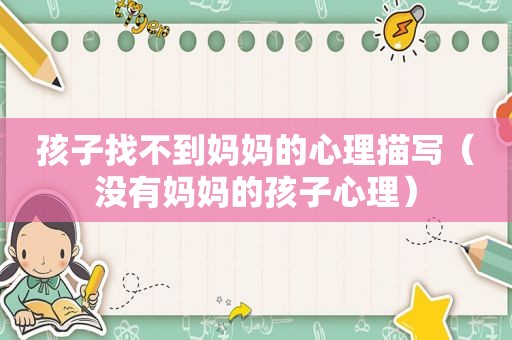
林迪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简笔画的狐狸,旁边挨着一只小松鼠,分别代表儿子和女儿。这是她为自己曾计划开办的家庭教育工作室设计的logo。
女儿一岁多的时候,就能在密密麻麻的通讯录里找到她的头像,点开对话框。因此她至今不敢换头像,怕女儿万一哪天有机会找她,却找不到她。
有一天晚上,她梦到儿子背出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他们得以重聚,孩子们把她紧紧抱住。她哭着醒了过来。
林迪手上的两个纹身。一个是儿子画的”妈咪“,是和孩子刚分离时纹的;一个是一只代表儿子的小狐狸,是在5月31日儿子生日那天纹的。
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正如一场美梦,她被残忍地叫醒了。
相恋,结婚,生子,争吵,破裂,分居,藏孩子,打官司,争抚养权。
这个情节似乎与一般的离婚案无异,只是当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两个女人,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在同性婚姻不被认可的情况下,林迪的 *** 之路异常艰难。她两次去北京,三次报警,结果连孩子的一面都没见到。最终她无计可施,将曾经相爱的伴侣告上法庭。
6月9日,是林迪见不到孩子的第197天。她还在等。
林迪每天数着与孩子分离的日子,漫长的等待让她时而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无尽路”上。
“最弯的路”
自从大学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林迪开始有意无意地让父母接触关于 *** 的信息,同时也感觉跟父母之间始终有一层隔阂,因为生活中很重要的那部分,没办法向他们敞开。
父母大概也感觉到了这种隔阂。2009年,他们主动跟她说,知道她是同志,也接受, “就希望你快乐”。
正是在那一年,林迪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了章敏。两年后,又在同一个朋友聚会上重逢,当时两人正好都单身,便自然地在一起了。
2012年,在章敏的提议下,两人决定从上海搬到北京,与章的父母一起生活。
林迪从来没去过北京。她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工作,亲友关系基本都在上海。当时她给已在苏州定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征求他们的同意,希望他们理解,自己和女友对未来的规划。
到了北京,林迪先找了份管理类的工作,做了半年,有点不适应,感觉不太能融入新的环境,就辞了职,跟章敏一起帮其父母打理生意,她主要负责做财务,章的父母给她们发工资,两人的生活和感情渐趋于稳定。
林迪说,2014年两人就有了生孩子的想法,那时身边有女同朋友通过借精方式生了小孩,她们作为孩子的干妈,也感受到为人父母的喜悦,觉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下定决心后,两人便开始备孕,同时寻找相关渠道。一开始她们想问身边的朋友借精,也有人同意了,但后来仔细一想,又担心以后会发生纠葛。最终她们把目光瞄向了丹麦的一家公司,那里号称有全球最大的 *** 库。
联系好这家公司与专业诊所后,她们在2015年3月抵达丹麦,按照计划,她们将在欧洲待上三个月,各自有三个排卵周期可以进行IUI(人工授精)。但在第一个周期里,章敏检查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第一次IUI只有林迪一人做。
做完后她们开始往南旅行,林迪几乎每天都会拍拍自己的肚子,笑着问:“说,你在不在里面?在不在?”十几天后在丛林里的度假村测出的验孕结果,给出了否定答案。
返回诊所的路上,林迪对章敏说,如果她能怀上双胞胎,自己怀不上也没关系。章敏纠正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人都怀上。
为了加深彼此的联结,她们从始至终都用同一个人的 *** 。但之后的两次IUI ,均以失败告终。
她们按原计划回国,决定改做成功率更高的IVF(试管婴儿),依然选择在丹麦的同一家诊所做。第一次IVF时,她们每人只有一个胚胎,最后都没有着床。再度失望而归。
2016年春节前,她们第三次远赴丹麦,做第二次IVF。取卵后第三天,两人各自植入两个受精卵,余下四个继续培养成囊胚。结果,囊胚培植失败,肚子里的4个也没有成为她们期待中的宝宝。
至此,她们已经努力了整整一年,叶酸也吃了一年多,没有一天停过。屡屡失败的沮丧感达到顶点,但就此放弃又心有不甘。后来经人推荐,她们决定到美国去,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还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说明我们没有这个运气。”
在美国取卵前,林迪、章敏两人打的针。
在美国取卵六天后,由于卵巢衰退,林迪只培养出两个囊胚,下一步还要做PGS染色体筛查,这是她压力最大的时刻。所幸筛完后,她还剩一个,章敏有四个。
此行期间,她们在洛杉矶择日登记了结婚。那一天是2016年7月6日,她们穿着便服在市政厅的小教堂举行婚礼,林迪回忆,当时说完“Yes,I do”后,她不自觉流下了眼泪,签字的手也在颤抖。
2016年10月,章敏和林迪在美国先后接受胚胎移植。她们想要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按原计划,林迪先移植自己的男胚胎,章敏再移植自己的女胚胎。但到了移植周期,林迪的激素没有达标,为了不打乱已订好的行程,她们决定按时赴美,让章敏先移植自己的一个男胚胎,等林迪激素合格后,再移植自己的男胚胎和章敏的女胚胎。
如她们期望的那样,三个都怀上了。朋友为此惊叹,“你们怎么那么勇敢啊?”
不幸的是,在12周产检时发现,林迪肚子里的那个男胚胎已停育。她在B超床上痛哭,章敏一直安慰她。
林迪说,虽然最后的结果与设想不同,两个孩子都是章敏提供卵子,但她们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哪怕是现在我也不觉得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一路上的曲折和欢喜都像是在测试我们的一致心意。为了组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族,我们或许走了最弯的路。这已经无法用“成功”和“失败”或“幸运”和“不幸”来衡量我们的经历。那一刻,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帮助我们来完整我们人生体验的。而我们依然还有两个优秀的孩子。我们也是通关后升级版的我们。
故事发展到此,才只是我俩下一段人生的引子。
破碎的家
“我们曾经很好”,林迪反复强调这一点。两人在孕期相互陪伴,彼此照顾,章敏对她“呵护有加”,很多画面让她至今想起仍有温柔的感觉。
那时,章敏因怀孕变得爱吃水果,她们晚饭后会一起出门散步,手牵着手去买水果,有时会停下来静静站着,相互依偎着,看月亮。
2017年,章敏与林迪去美国加州待产,先后于5月底、6月底生下儿子和女儿。
儿子出生时哇哇大哭,一旁陪产的林迪也哭得不成样。章敏是剖腹产,有点大出血。确认孩子无恙后,林迪赶紧回到手术台上的章敏身边,帮她 *** 疼痛的肩颈。护士叫她跟着孩子去观察室,她说:“不,我要陪在我妻子身边,她更需要我。”
之后她到观察室去看儿子,观望了很久,才敢去抚摸他的小手,小心翼翼地唤他,他用小手握住了她的食指,她一下百感交集,又笑又哭。
28天后林迪生女儿,章敏也到医院陪产,把儿子托付给月子中心,全力照顾林迪。林迪是顺产,生了近十六个小时,过程非常难熬,还一度因为没在好时辰把孩子生出来,自责不已。章敏安慰她,这个出生时间也不错,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差的。
儿子的出生纸上登记的母亲是章敏,女儿的出生纸上登记的母亲则是林迪。后来她们一直告诉孩子,他们有两个母亲,章敏叫“妈妈”,林迪叫“妈咪”。
女儿的出生纸上登记的母亲为林迪
月子还没坐满,她们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国了,并决定独立带娃。林迪说,刚开始没有请阿姨,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人一起带,彼此能互相体谅。后来章敏想转行业,开始到外面学习、工作,建立新的社交圈,她继续在家全心育儿,也请了一个阿姨帮忙。
之后,由育儿引发的各种观念冲突和摩擦,慢慢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林迪介意章敏在哺乳时抽烟,希望她能多陪陪孩子;章敏则认为林迪不上进、乱花钱。到了某个阶段,林迪感到很难跟章敏沟通。
林迪说,章敏是性格比较强势的人,平时相处基本以她的意见为主,当两人出现问题时,这种不对等更加明显,有时会感觉不被对方尊重,而对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痛苦。
但林迪始终觉得,“家是不会散的”,哪怕有再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好好商量,共同解决。因此当章敏提出分手时,对她来说是很突然也很沉重的打击。
林迪记得很清楚,分手那天是2019年3月1日,是章敏把她从苏州父母家接回北京的第二天,之前她们在电话里发生过争吵。
那天下午,章敏把她带出去买菜,回来的路上,开口第一句是:“你有什么打算?”她感觉,这就像一个公司的HR要辞退员工的姿态,平静,理智,不留余地。
而她的情绪波动剧烈,时不时会被对方冒出的一句话刺痛。相比感情的失败,对她打击更大的是,这个曾经圆满的家要破碎了。
章敏说,你可以走,两个孩子留给我,我会把他们带好。但她不相信,她觉得眼下没有人能代替她,给孩子最好的照顾。她提出想继续留在孩子身边,直到他们上幼儿园。章敏同意了。
几天后,林迪跟章敏第一次讨论孩子的抚养问题。章敏想让林迪去美国把女儿出生纸的生母改为自己,两个孩子都跟着她生活。林迪对此不置可否,只提出希望以后可以共同育儿,她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两次。章敏口头上答应了,却拒绝就此签一个协议。
“那她可以随时反悔呀!我觉得她只是想哄着我把孩子的出生纸改掉,改完之后就不需要我了。”林迪想,多拖一日,她就可以多陪孩子一天。
接下来近8个月,她和孩子朝夕相处,依然像以前一样照顾他们,每天拍照、写日记,记录与他们的点点滴滴,但心情已截然不同。她变得特别珍惜,更在意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不像以前累了会想歇一歇或抱怨一下,“那时候觉得你们虐我,我也欣然接受”。
她开始带孩子出去旅行,带他们第一次下海、第一次坐船、第一次爬山、第一次参加婚礼……她想跟孩子创造更多回忆,也许有一天他们不会记得,但对她来说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刻都珍贵,“像是偷来的”。
期间,她给孩子们讲过一个缓解分离焦虑的绘本《看不见的线》,儿子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她会把里面小朋友的名字换成他们的名字。“知道吗宝贝,不管你们在哪儿,妈咪都和你们在一起。”她抓着他们的小手说,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会有一根隐形线,虽然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它会牵住彼此,“妈咪很爱你,你一定要记得。”
生育孩子后,林迪曾计划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并学习了相关课程,这本儿童诗集就是她上课时做的一个作业
2019年5月12日,林迪与孩子们一起完成的画,作为母亲节礼物。
那段时间,林迪处于一种悲喜交集的分裂状态。一边,孩子们每天带来很多笑容和快乐;一边时刻吊着一颗心,想到早晚要跟孩子分开就很痛苦,偶尔缓不过来,只能趁孩子午睡时或躲进厕所哭一会儿。
她想过偷偷把女儿带走,也打听过外国籍小孩怎么报名上学,但又怕此举激怒对方,以后都见不到儿子了。
每次章敏一回来,她就觉得压力很大,言谈举止都小心翼翼,害怕眼神交流,又要察言观色,怕稍有不慎就“一脚踏空”,导致跟孩子分开。
离别终究还是来了。
2019年11月25日早上,章敏突然让林迪搬走,理由是林迪之前把她父母“赶出家门”。
林迪告诉澎湃新闻,11月初,章敏父母带着阿姨和两个孩子回舟山老家,她因故单独先回了上海,之后带着一位朋友和朋友的女儿去舟山玩,并提前发微信跟章母说,想让朋友母女在家住一晚,睡阿姨那间房,让阿姨睡沙发。但没想到,当天章敏父母去了外婆家,第二天才回来。
“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还停留在‘我们是一家人’(的状态)。”林迪说,之后她和章敏父母在舟山待了十天左右才回北京,没发生任何事情,“我一直很尊重她爸妈,即便生活中有些观念冲突或矛盾,我也不会跟他们呛。”
那天章敏拿这件事指责她时,她觉得“有点百口莫辩”。但她认为,这只是章敏找的一个借口,目的是让她离开这个家。
林迪回忆,当时章敏一开始想让她拿钱,条件是把手续办掉,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她不愿意。章敏又提出资助她再做一次试管,让她拥有自己的孩子。她还是不愿意。最后章敏说,你也可以把女儿带走,你现在立刻就把她带走。
林迪的第一反应是“我真的可以(带走)吗?”章敏又说,你如果真的把她带走的话,你会毁了她一辈子;你以后有什么怨恨,会发泄在孩子身上;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她是有亲哥亲妈的,她有一天会来找我们,我会告诉她当初是你要把她带走的,她就会恨你。
这些话一下击中林迪的软肋。她最怕的就是伤害到孩子。
“作为一个在家多年没有出去工作的人,我很怕环境变动导致孩子过很差的生活,我怕孩子受委屈。”林迪说,分手这件事几乎摧毁了她的自信心,使她时常陷入一种“我真的那么差吗”的自我怀疑。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能力把孩子照顾好。
章敏的那些话,犹如施了魔法的万钧之力,压在她本就茫然无措的心上,以至于不自觉地困在对方的逻辑中,失了方寸。
她决定先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再回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那天下午,她跟孩子们正常告别,随便收拾了两件衣服,带上女儿的出生纸和两张结婚证,离开了那个经营了七年的家。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被拒绝的探视
在回苏州的高铁上,林迪失控般地哭了一路。她感到无比后悔,恨不得立即掉头回去。母亲来火车站接她时也哭了,她拒绝了母亲的拥抱,像被痛苦灼伤到谁也碰不得。
离开原生家庭十几年,明明已经当妈妈了,突然一下被“打回原形”,以一个如此糟糕的状态,回到父母身边,重新变成了那个让他们担心的孩子,林迪觉得,她的人生太失败了。
十天后,在母亲的陪伴下,林迪鼓气勇气去北京找章敏沟通。“我非常清楚她不会让女儿跟我走,但我必须要开这个口。”她又紧张又害怕,压力很大。
林迪先把母亲安顿在宾馆,独自前往章家楼下的肯德基,与章敏见面。她回忆,章敏提出如果她要带走女儿,先把之前给她用的钱还回来。
那两年在国外受孕生子,花了一百多万,都是章敏父母出的钱,“我们帮她家里做事,我们也不拿工资,要花钱的时候,她妈就打一笔钱过来。”
林迪问,你要多少钱?章敏说一千万。两人谈崩了。林迪想看孩子,便提出要回家收拾东西,章敏说她来收拾,然后就上楼了。林迪回过神来,也跟着上楼了。
是阿姨开的门,女儿在边上站着,林迪还没来得及喊她,她就被拉进去了。章敏立刻出来,把门一关,开始骂人,因为她刚发现林迪把女儿的出生纸带走了。两人在楼道里争执起来,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林迪再回去,发现屋里完全没有动静,孩子已不在里面了。后来她得知孩子被带离了北京。她去问阿姨,阿姨很为难,表示不便再和她联系。
章敏说等过两天她有空了,可以继续谈。“你这样我们还聊什么呢,孩子都不在北京了。”林迪和母亲当天就回来了。
回到上海后,她开始找律师。她觉得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要回孩子,她很难面对那个“很强”“很有谈判技巧”且深知自己弱点的人。很多时候她看着手机,想跟对方说她想见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圣诞节前好不容易开口了,又遭到对方拒绝。
对她来说,光是面对章敏,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她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助她,替她挡在前面。
律师高明月回忆,去年12月下旬林迪第一次找到他时,整个人很消极,情绪非常低落,对自己和案子都没什么信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她,这是我们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他劝她振作起来,“你要让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给你。”
刚和孩子分开那段时间,林迪的状态不太好
后来有一天,林迪的手机收到了孩子们的体重信息,那是北京家里一个智能体重秤发送的,说明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
当时已重新工作的她,趁着元旦放假,连夜坐了火车,于31日上午到了昔日的家门口。
家里有两道门,第一道是指纹锁防盗门,第二道是钢门。林迪说,她到的时候,第二道门没关,能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声音,章母也在家。她敲门说;“外婆,让我看一下孩子。”章母很惊讶,马上打电话让章敏回家,始终没有开门。
45分钟后,章敏赶回来了,劈头一句“孩子是我的”,她反驳说“孩子是我的”,于是两人在楼道里又开始了“幼稚”且无意义的争吵,言语激烈。“她有点气急,扯我头发,抓我手臂,想让我离开。”
高明月的北京同事袁富连赶到现场时,先是听到林迪在哭,然后看到个子较高的章敏拽着林迪右边的胳膊,往电梯方向拉扯,看到她来了,才停止动作。
袁富连说,章敏始终很冷静,后面警察来了,她也一直强调林迪是 *** 的,要来抢她的孩子,还跟她要钱。
那天林迪报了三次警。第一次她和章敏同时报警。林迪回忆,警察来了之后,双方各说各的,一个拿出了出生纸,一个说有亲子鉴定,警察感到很困惑,她把整件事情解释了一遍,警察差不多听明白了,就说这种事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建议她去法院解决。
警察以扰民为由,把她们带到楼下谈,没有谈好。章敏表示跟林迪彻底划清界限,然后转身离开了小区。后来,她把林迪拉黑了。
之后林迪再次上楼敲门,求章母开门让她看看孩子。因为后来一直没听到孩子的声音,她很担心,就又报了一次警,求警察让她看一眼孩子,确认下孩子的安全。警察与章敏取得联系,但后者始终没有出现,并强调孩子不在家里。警察让章敏发一段孩子的视频过来,证明孩子是安全的,然后把林迪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下午4点做完笔录后,林迪独自返回章家,发现孩子又被转移走了,且这一次完全无从得知他们去了哪里。林迪被绝望击溃了。她千里迢迢来看孩子,确认孩子就在里面,离她只有一门之隔,却一眼都没见到。
深夜,她第三次报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倾诉。警察还是来了,规劝无果,又走了。她坐在门口的猫砂上,继续无望地等待,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那天北京零下6℃,她一天没吃东西,没上过厕所,又冷又饿,身心俱疲,蜷缩在昏暗狭窄的楼道里,就这样跨了年。
2019年12月31日,林迪蹲在北京昔日的家门口度过了跨年夜
凌晨一点多,她到楼下的麦当劳吃东西。这家店她带孩子们来过,回忆让她无法久留,凌晨3点她打了辆黑车,逃也似的直奔火车站,却不知道火车站也会关门。
她受着冻,心慌了。刚好另一辆车停下,下车的女孩也发现来早了,赶紧又回到车上。林迪请求带上她,司机和女孩都同意了。司机本想把她们带到附近的餐饮店避寒,但开了几公里都没找到一家营业的店,他干脆停在路边,说等到5点再把她们送进车站。
车里开着暖空调,三个陌生人聊了一个小时,林迪也讲了自己的故事。最后司机没收她钱,还开导她说,只要是你的孩子,你们总归有一天会见面的。
她被这份善意所鼓舞,心里重燃起一丝希望。2020年的第一天早晨,她坐上第一班火车离开了北京。
林迪第二次去北京见孩子未果后,所发的朋友圈
漫长的等待
回到上海后,林迪正式委托高明月。1月14日,他们给章敏寄了律师函,希望对方接函后三日内与高明月联系,并协商沟通以下事宜:解除双方法律关系、两个孩子的抚养和探望、双方财产分割争议。但未收到任何回复。
林迪决定起诉。家人劝她不要打官司,说打了官司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现在有什么啊?我连孩子都看不到。”
由于两个孩子是美国国籍,林迪一开始考虑在美国起诉,但咨询了当地律师,发现需在当地居住满六个月才可以起诉。他们又想办法在北京起诉,但无法取得章敏常住北京的相关证明,对方在北京没办过居住证。
于是只能到章敏的户籍地舟山起诉,但考虑到章家有亲戚在司法系统,林迪一直有些犹豫,她甚至还试过在苏州起诉,因之前在父母家为了给孩子打预防针,两人曾在当地办过居住证,法院核实发现章敏并没有在当地实际居住。
后来又遇上疫情,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3月中旬,她才正式在舟山定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4月1日受理立案。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于4月1日受理该案
起诉书的诉求是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法官觉得很奇怪,特来向林迪求证,问她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孩子(指儿子)。她向法官解释,她对这两个孩子的感情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她都不想放弃,“哪怕我没有权利我也不想放弃。”林迪说,也许有一天,等孩子长大了,他们就会知道,妈咪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律师建议林迪找媒体报道下这个全国首例的案子,或许可以带来一些正面影响。也有朋友提醒,如果不愿意,可以拒绝采访。但她一次都没有拒绝,一遍一遍地重复诉说,她希望抓住一切机会,穷尽一切办法。
“全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孩子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分手就分手吧,没有关系。”林迪哽咽道。
第一篇报道出来后,她很害怕,担心章敏会打电话来骂她。结果并没有。后来上了热搜,又把她“吓死了”。朋友安慰她,“你知道吗,你在创造历史。”
作为一个从2005年就开始做女同公益组织的人,林迪深知这个案子对性少数群体的意义,站出来发声对她而言无可推辞,前提是她要保护好孩子和章敏的隐私,“我也要尊重她,不能把她推到人前去。”
林迪说,虽然不认同章敏的做法,但不曾有过怨恨,因为她知道,对方也是在用她的方式去爱孩子。“分手了,她可能希望彻底一点,孩子以后不用问那么多问题,不会有那么多困惑。”
近一个月,澎湃新闻曾多次约访章敏及其代理律师,均未获回复。
第一次去北京谈判失败后,林迪的状态一直很糟糕,尤其过年期间无所事事,她整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好几次都想放弃自己。但后来又想,还没有努力到最后一分,凭什么放弃?
她开始主动屏蔽悲伤,专心工作,每天健身,看书,学滑板,做甜点,甚至开始追星。什么事能让她轻松一点她就做什么,尽量让自己保持平和的状态。
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林迪除了定期到健身房锻炼,还经常在晚上出来滑板,她说“每天一滑防抑郁”
通常在夜里失眠时或梦醒后,会把她拉入情绪的深渊。
有一次梦到她带两个孩子去吃早餐,孩子被人抱走了,她疯了一样满世界找,章敏责怪她,你为什么把孩子弄丢了?醒来后,她崩溃大哭。
还有一次,她梦到去参加章敏和新女友的婚礼,新女友和孩子们相处融洽,像是已经取代了她这个妈咪。即便是梦,也有种难以排遣的嫉妒。她担心梦会成为现实,时常患得患失。
她猜测孩子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跟她有关的信息。阿姨曾告诉她,刚分开那段时间,孩子们会问妈咪在哪里,但没有人回应他们。现在已经半年没有见面了,他们还会想起妈咪吗?不知道。
林迪时不时会梦到孩子们,有些是伤心的梦,有些则稍微能缓解下她的思念
每过去一天,遗忘就多一分,她与孩子的距离又拉远了一点。时间是她的敌人。
4月中旬,章敏向舟山定海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称其近年来一直在北京生活,已在北京丰台区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本案应移送至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4月下旬,高明月向定海法院提交关于本案管辖权的书面意见,认为被告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且提交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北京丰台区为其经常居住地,应予驳回。
5月26日,林迪收到定海法院通知,案子确定移送北京。高明月判断,可能又要再等4个月才能开庭。
4月底,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那天,林迪健完身回家洗澡,突然悲从中来,大哭一场。“我已经做了15个采访了,就觉得好累啊,一直在重复,但真的有在改变吗?我还在等,一个开庭日期都没等到,一点进展都没有。”想到这些,她罕见地在白天崩溃了。
采访末尾,她说她会坚持到底,直到和孩子团聚的那一天。“他们没有回来,就永远努力,就永远努力,不要放弃。”像是给自己打气般,她重复了好几遍。
每次看到同龄的小朋友或者相关的事物,林迪都会想起远在天边的两个孩子
林迪给孩子们买的衣物
(林迪、章敏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