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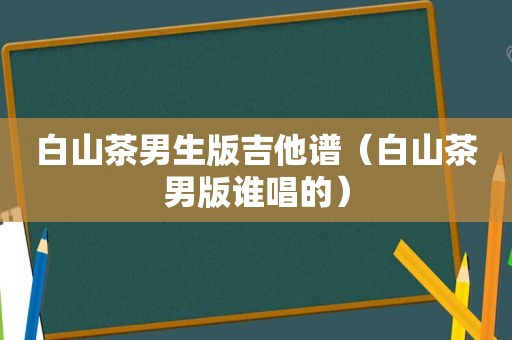
又是修路。他抱怨着。在乐室楼下买了瓶常喝的果酒,从另一条路回家。
幽暗的巷子里,一束又一束灯光路过他的身旁。
“先生,进来坐坐吗?”一道娇艳而羞涩的声音从某个小院中传来,叫住了他。
秋夜里,她只单穿了一条酒红色的长吊带,倚着门框,手指轻弹着烟。
她格格不入,白山茶丛中。但她那傲人的姿态又像是这花为她而开,这灯为她而明。
他定住脚步,从未想过这里有这样的“生意人”,转过头,一个身影在脑海浮现,但转瞬即逝。
他向她的方向迈了一步,却没继续向前,攥着小提琴包的手紧了紧。
她看清他的脸,神色闪过一丝诧异。
“我……见过你,”她轻笑道,“我听过你拉琴。”
我的听众?他疑惑,但没问出来,而是推开小院的门,同她进了屋。
事后,他无意瞥见了她腿上隐蔽的一片片青。
他把那瓶酒落在了她的梳妆台上,第二天晚上他又买了一瓶。回家之前他本想走另一条路,但真到了晚上,他还是走了那条路。
为什么呢?不知道, *** 上瘾吧。他想。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一抹酒红。
事后。(休想让我写过程)
“你的酒很好喝,”她笑嘻嘻的,像个小孩,“你又买了对吧?”
他也笑着承认,看到一旁的橱柜上有纸杯,抽了两个出来,手上倒着酒,眼睛却不时瞄着身着白色吊带,正卸着妆的她。
酒抖出来了。
转身放下酒瓶,想着找纸擦一擦。他注意到一个台历,这月的最后一天被红笔圈上了。一张身份证被压在下面,他鬼使神差的拿起。
2002-……
他的瞳孔骤缩,甚至整张身份证只能看清这一个年份了。他想象不到自己竟然这么 *** 。此刻,他想逃离,但他僵住了。
“你多大了?”他缓过神问,一边把那烫手的身份证放回原处。
“你猜呢?”
他沉默不语,与转过头的她对了个视,露出了一个勉强的笑。
她抿抿嘴,移开了视线,离开梳妆台,在他对面坐下。男人突然想起昨晚的那句话,想问点什么,却不知怎么开口,只好作罢。
“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见过你啊?”他抬头,眸中映着让他移不开眼的笑颜。
他轻轻“嗯”了一声,便再也不敢与她对视,望向窗外试图掩盖自己心中微小的慌乱,那盛放的白山茶当真敌不过对面这娇艳的人儿。
她不解为何他不再看自己,便自顾自地说道:“十几年前,我还在广场周围捡破烂,有天夜里,广场中央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用小提琴演奏,背对着我,前几天我没理会,后来有一天他开始反复练同一首曲子,我想走近去听,可……”她大概感觉有趣,不自觉笑了两声,“易拉罐声太大了,被他发现了,不过他冲我笑了一下就没再理我了,当我不存在继续练习了。”
那是一张,让她久久不能忘怀的、让她奉为神明的、清秀的、俊美的脸庞。
他想起来了。那时他还是个顽固的富家公子,大学勉勉强强毕业后,他拒绝出国镀金,拎着提琴,偷偷转移了父母给的零花钱,孤身一人来到这座小城市。
窄小的公寓当然比不上敞亮的别墅,什么时候都不是练琴的好地点,他只能在半夜前往无人的广场。
最开始他以为,月光是他唯一的听众。
后来,他迎来人生中第一次大型独奏,却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要演奏的曲子总是有一小节无法顺利进行。他疲惫地站在平台上,静静地望向护栏外的河面,有些丧失信心了。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吓到了他,他猛地转头--是白天那个捡垃圾的小孩。她头发乱糟糟的,身上每一处都破破烂烂的,一张漂亮的脸蛋就这么遭在这糟糕得显而易见的人生里。
他尴尬地冲她笑了笑,似乎出于面子,他又开始了练习。而令他惊讶的是,有那么一次两次熬过了那一小节,坐在花坛上的她会高兴地拍手,摇着双腿。
似乎她生来就是为了成为他这首《白山茶》的听众。
不知道是不是他想的那样,不过他还是第一次尝到他人真心为自己高兴的滋味。那是他生来作为富家子弟不曾拥有过的,是他曾以为他不配拥有的。
他在流下眼泪前转过了身子,开始了下一次练习。
“对了,你还记得那张票吗?”她眼里闪着困倦带来的泪水,喝了几杯后,面色潮红,摇摇晃晃地起身,从首饰盒最底层抽出一张平整的门票,不过因为是浅色底,已经泛黄了,可还是看得出主人在很用心地收藏。
演出前的那一个月内,即使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她便是昏暗的路灯下,他唯一的白山茶。不知是否有些唐突,演出前的倒数第二个晚上,他买了一张票送给了她,希望女孩能去看他演出。
第二天傍晚,他悄悄拨开红幕,扫视一圈也没见到女孩的身影。也是,正常人不会轻易来的吧,更何况还是个小姑娘。他失落。
那天傍晚,他一战成名。
而他的白山茶,不知是不再盛开,还是已经凋零,只是很多人都知道,在听众面前,那首曲子他仅仅拉过一次。
她趴在桌子上,一只手下压着那张票,另一只手握着纸杯,轻轻喘着气。
“你……”男人看到没有撕掉的副券,仍然会想起当年不可诉说的情愫,“当年为什么没去?”
她一愣,随后眼里只剩释怀。她用胳膊撑起身子,叹了口气,笑着说道:“那天啊,我妈让我爸打死了,因为我妈不想给他钱了。我们家也没有亲戚,于是……过了几年我就接我妈的班了”
这几句话,比他吃过的任何牌子的醒酒药都好使,甚至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还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久,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遍。
“那首曲子你可以再拉一遍吗?”她的声音似乎又将把他灌醉,他微笑着点头,各种复杂的情绪都化作了他对那首曲子的记忆,他感觉如今的旋律似乎比当年多了一种悲伤,可她却觉得他仍是当年那个人。
那个亲手在她心里种下一丛又一丛白山茶的人。
他隔三差五地去探望她,每次去都会给她带几件首饰,尽管他存款不少,平时花钱也不大手大脚,然而在这件事上他是一点都没犹豫。
(作者:不懂就问,这就是爱吗?)
“我跟工作室商量了一下,申请了一场演出,我想把那年你错过的演出,补回来。”他挽起她鬓边的碎发,给她戴上新买的耳坠。“到时候戴着它,好吗?”
“什么时候?”她惊喜地看向镜子里的他,指甲抚摸着耳坠上的珍珠雕刻的白山茶
“31号?”
她先是诧异,又低下了眼,似是在犹豫什么。他看出了她的为难,安慰道:“没关系,时间没定下来呢,听你的就……”
“不!”她拽过他的手,“31!就31号!”她转过身,眼里多了一丝恳求。
他来不及想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反应,只是声音变得更加轻缓,抚着她瘦瘦的后背。
“全听你的。”
演出的日子到了,她穿着他给她买的白色长裙
第一排观众席的中央,只有她一人,没人知道她是谁--明明第一排的票不售出。
演出结束时,观众席上的所有人都小声地抽泣,除了她,这次的听众都是被他这首只演奏了一次的《白山茶》圈粉的,时隔十二年,有人心中那首完美《白山茶》再次被唤醒,有人心中含苞待放已久的白山茶,终于盛放。
他站在台上注视着她,而她依然像十二年前那样仰望神明般看着他。她甚至双手合十。
他再也无法克制,丢下琴和琴弓,跳入观众席,一手紧紧揽住她的腰,一手扶住她的脑袋不可自拔地吻了下去。观众席先是瞬间鸦雀无声,而后爆发出优雅的音乐大堂中不该出现的欢呼声。
送她回家的路上,她一直紧握着他的手。到了地方,他离开前,她塞给他一个盒子。
“回家再看。”她叮嘱。
走到距离她家门口有三四百米,他听见了哀嚎声。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心脏疯狂跳动,他非常希望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他一边匆匆往回赶,一边打开了盒子中相机里的录像。
他庆幸很快就回到了她家门口,他实在不忍看下去了。
他无法理智,踹开了门,心爱的人正蜷缩在地上,马上就要昏厥,拿皮鞭抽打着她的男人正是那录像里她禽兽的父亲。
他反手拿起桌上的酒瓶, *** 地砸中那个男人的头,又冲着他的脸揍了几拳,可一不注意就被那个男人拽倒,桌子也被掀翻,肚子上挨了好几下,那个男人明显是喝醉了,估计得下死手,他伸手够到了掉出果盘的水果刀,直接刺进了男人的颈动脉,没一会儿那个男人就没了动静。
他的脸溅上了血,眼眶通红,眼球布满血丝,艰难地伏着身子爬向她,把她揽在怀里,“我……”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药,药在哪里,我给你上点……”
“没事,你缓缓,我早习惯了……”她失去血色的嘴唇颤抖着,“倒是你,真不听话,不是都说了,让你回家看吗……”
她抬手擦拭着他混着鲜血的泪水。
“为什么,你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告诉我?”
她笑而不语,他悲哀,他愤怒,他把头埋进她的颈窝里,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
在这一遍遍的质问中,他忽然明白,她怎么会没想过要直接告诉他呢?在他之前,这将近十年苦海般的日子里,又有多少个人成为天真的她的希望呢?她又被辜负了多少次呢?
--红笔圈划的31号
--小腿上大片的淤青
--2002年
--“于是我接班了……”
后来,那间有着种满白山茶的小院的房子一朵白山茶都没有了,倒是郊区正方地形四栋小别墅被买下,那对小夫妻也真是奇怪,四栋别墅都推了之后在正中间建了一栋,别人家都是种种菜,这家可倒好……
只有白山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