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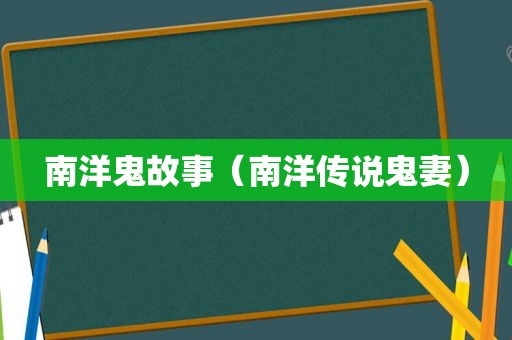
我想我通过一种秘密的途径,见证了一个南洋老人一生的爱情。诡秘、凄迷,而又震撼人心:
早年,我还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又对流浪充满着浪漫憧憬,在晨昏交替之间风尘仆仆的挥霍着我的青春。每天回家的路上,我都会路过一间小士多店。店主是个小姑娘,年轻、淳朴而又漂亮,或许是为了多看她一眼,借故和多她呆一会儿,每次我都会在那里买点东西。
这天傍晚,我又路过那间士多店,小姑娘笑嫣嫣地接待了我,我指着一个切开的大芒果问她:这个多少钱?她说你想要就送给你。我以为她开玩笑,结果她真的把那半个芒果放到我手里,然后无奈地告诉我这几天天热,芒果都蔫了,再这样下去可能都得扔掉。
她那种与年龄极不匹配的生意人的无奈和豁达对我来说,有种致命的吸引力。我顺手捏了捏芒果,软软的,看来真的是蔫了。出于某种补偿心理,我又和她买了一些零食和干果,然后回去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听到她嫁人的消息。她嫁给了一个整天喝酒赌钱的醉鬼,那个粗壮的男人一次次地醉醺醺地回家要钱、打人,记忆在这里发生了分歧,印象中那个男人也许不是他丈夫,而是她的父亲。但结果都一样,最后一次那男人实在太过分了,把她的左手腕打坏了,留下了残疾。
我愤怒了,虽然这件事和我毫无关系,虽然这在男权至上的马来地区再平常不过。但我还是带着地保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冲进店里,把躲在柜橱里的男人揪了出来——短短几分钟,那个男的在一堆棍棒中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人群散后,我帮那女孩子将尸体抬进了冰柜,以后做腊肉用。
我问女孩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女孩子抱着残疾的左臂,凭栏望着外边无际的棕榈树,一直没说话。
我说我要去远方做产品,你要不要跟着我去。开店有啥好的,做营销才好哇,营销你不懂?销售发展到当今这个时代单靠叫卖是不行的,于是就发展成好多拆分细节的手段和套路,对了,你可以到我那里去做话务或者促销。
女孩最后有没有答应,我忘了。
然后就是在某地漫长的流浪之旅。
我在做活动,整天忙得累死累活但坐下来却又想不起来忙了些什么。一天傍晚,我、王动和一个半是招聘半是帮忙性质的男孩,以及一个蒙着头的陌生人在一个小巷里聊天。
我和两半男孩以及陌生人挨着坐在水泥台阶上,王动站在我们对面。在印象中,我对那个男孩是充满了感激的。因为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帮忙,而且似乎又不要工资。但男孩对我的态度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淡然和尊敬。
我对男孩感激的一个原因是,他还叫了他的朋友来帮忙——就是他身边这个神秘的蒙头男。和对我的态度不同,男孩对蒙头男人很是热情,说话也大声了很多。我在一丝尴尬中凑上去一看,这才大吃一惊:这个蒙头男不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杨挺松吗?
哎呀,原来是你呀,你弄得神神秘秘的吓了我一跳。对面的王动也笑了,我们高中一起的。我用夸张的热情来掩盖内心里复杂的自卑,我始终认为,我的表现远不如王动憨厚的笑容来得淡定。
我询问了杨挺松来这里的时间、近几年的状况和将来的打算等等寒暄的俗套,最后问道:你现在住在哪里?
杨顾左右而无言,我就明白了,很豪爽地拍了拍挺松的肩膀:那晚上就住我那里吧。又问打工男孩:“你住哪里?”“我朋友那里。”我说就都住我那里吧,我住的是三房一厅的,都能住得下。
于是我们就往回走,路上我掏出一支烟递给杨挺松,杨接过来抽了一口像被蝎子蛰了一样立马扔了。我诧异地抽出一支点上,结果发现烟盒子温度越来越高,最后竟然哧哧地着火了,烫手地扔在地上,烟盒子越烧越快, “砰”地一声炸了。我惊恐地将嘴里的烟赶紧扔掉了。
不得不服挺松啊,还是像当年一样机警敏捷。我问挺松是怎么发现烟不对劲的,挺松皱着眉头说一抽就知道了,我再问咋就一抽就知道了。就像过去无数次的愚蠢提问一样,聪明人或内行用看半吊子傻叉的眼神看你半天,让你无地自容。
于是我马上装明白:这明显是竞品的阴谋啊,就像当年山海关被放炸药一样,是要搞坏这个牌子的。
我带着他们三人从一家小卖铺的拐角楼梯直接上了我的公寓。很老式的那种筒子楼,经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水泥装修,发霉的味道里永远流淌着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一进楼道,我就发现了鬼魅的踪影。在水房那边,我看到一个没有脚的穿白衣的女人,带着一个同样装束的无脚小女孩飘了过去。
我强忍着不去看和不去想这些东西,面色僵硬地笑着对伙伴们说:诺,这就是我的房子。地方够大吧,这是客厅,那个敞着门的最大的那间是我的卧室。我看了看我的卧室有4张床,欣慰地想:这样大家就算都睡我的房间,也都能挤得下,还正好旺一旺人气。
打工男孩欢快地抱着一摞被褥进了我的卧室。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身穿锦衣马褂戴员外帽的小男孩,脸涂得死白死白像是祭奠死人的金童一样,向我走了过来,笑嘻嘻的引逗着我,进了旁边的侧房。我凭空抓起一条柳枝,用力的向那个男孩抽过去,所谓柳枝打鬼,打一下矮一寸。果不其然,等那小男孩进了那间侧房的时候,就已经只有巴掌大小了。
进了这间房,我环目四顾,才发现这里空落落大得吓人。除了墙上挂着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永远看不清楚的人像照片,房间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不对,房间里充满了鬼。
那小鬼一家子都跑了出来。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他的保姆阿姨……等等,于是我凝念轮番念咒——六字大明咒、金刚般若真言、道家九字真言、阿弥陀佛咒,我发现第二个比较好使,鬼在听到“般若波罗密”时明显恐惧地往后退,而听到“麻里麻里吽”却反应不大,其实在梦中我也醒悟到我念错了,不是“麻里麻里吽”,而是“唵嘛呢叭咪吽”。
后来我在疲惫和恐惧中终于完成了驱邪,躺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结果那家子鬼魂根本不打算和我善罢甘休,在梦中他们将我的魂魄拘役到放魂海,将我一步步推向海域深渊。
在海边,我闭着眼睛不断念着金刚般若密咒和群鬼对抗,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的耳边恢复了清净。睁开眼,要么沉溺在汪洋血海的恐惧里不能自拔,要么是暖和的被窝。
挣扎再三,我睁开了眼,身在海滩,旁边是几棵被海水浸唰海藻缠绕的脏兮兮的枯树枝。
我站在海滩上,知道这只是个梦中之梦。
我得回去了,床头还有亲人记挂呢。于是我再次睁开眼,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正一脸深情和沧桑地看着我,旁边的那个女仆也不比老太太年轻多少。
我惊慌的摸了摸自己的脸,发现皱纹也多了好多。
我在床上到底躺了多长时间?
40年啊,老爷。
老太太用手擦了擦眼窝,我看到了她残疾的左手。那一霎那,我才记起来,当初从南洋回来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去做营销的时候,她是答应了和我走的。
可是为什么你变得这么苍老啊?阿银。你不是那个笑眯眯淡定的小姑娘吗?
我满目满心的悲伤和愤怒,走下床来,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为什么这么苍老?”阿银早哭倒了,女仆也哭着反复念叨:“阿爷,侬不晓得哇。”“阿爷,侬不晓得哇。”
我看到过道的墙上挂着7枚饺子,用红线缝成七星的阵势,由于时间太久,饺子变成了干黄色。我用金钱剑指着这7饺阵,吼道:“是不是这7饺阵让你变得这么苍老,我这就毁了它!”
“不可以啊!”阿银拼命地拦着,哀哀地从墙上滑倒,坐在地上。女仆也一边扶着阿银一边哭着劝阻。
“为什么?”我茫然地问。
女仆急忙说:“是小少爷。您要毁了饺子,小少爷就再也回不来了。”
大概哭得没力气了,阿银告诉我:40年前有几个男子冲进我们房子强行入住,其中有个会咒术的男人用柳枝把我们7岁的儿子活活打死了。为了给孩子聚魂转生,阿银耗尽青春做了这个7饺阵。
那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头昏脑胀地问。
你在床上躺着。她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