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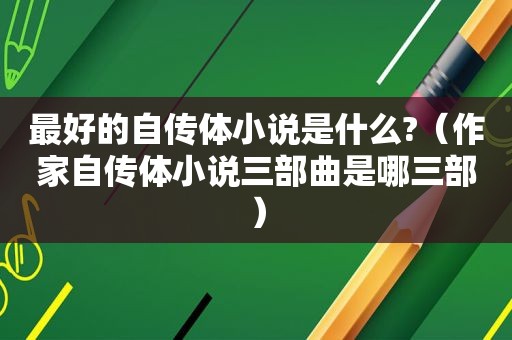
第五章 沉重的翅膀
4 赶 鸭 子 上 架
1981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月朗星稀,大地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热闹了一天的校园顿时清静下来,教师办公室没有了灯光,只有会议室灯火辉煌。说是会议室,其实是“多功能”教室,但不是现在的“多功能教室”。原来是一间教室,后来改为教师办公室兼寝室,一敞三间,大一点的会议就在这儿开,故而又是会议室。室内有四五张办公桌,还有两张床。屋子中央一根粗大的木梁横跨其间,上面是十几根弯弯的椽子和灰白色的房瓦,没有天花板,透过玻璃亮瓦就能看到湛蓝的夜空。这里陈设虽然简陋,却是工余饭后教师们光顾频率最高的地方。一下课,从教室走出来的人不管这里是不是他的办公室,都喜欢带着一身粉笔灰往这儿一坐,有的干脆往床上一躺,稍事休息。饭后更是成了教师 *** 的场所,看报的、聊天的、下棋的,办公的都有,国家大事在这里“发布”,社会热点在这里议论,教学经验在这里交流,奇闻异事在这里谈论,疑难杂题在这里钻研。社会的、学校的、班级的、甚至家庭的好事喜事在这里分享,烦恼事在这里倾诉,没有顾虑,没有隐私,就像一家人一样,成为真正意义的教师之家,是最民主、最自由、最活泼的一方乐土。
今天这里一反常态,气氛有点严肃,因为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中心校领导和大队管校的副书记,他们分别坐着一张办公桌的两边,算是主席台,参加会议的是全校教师、职工,包括两个教学点的老师。年纪大的正儿八经坐着另外一张办公桌边,年轻的爱热闹挤在一起,坐在两张床的床沿上,床不堪重负,压得几几昂昂的,要不是床沿用几块青砖衬着,早已腰折骨断。会议的主题是民主选校长,主题有点凝重,两位主持人各自说了一通,然后分发选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票数最多的当选校长,其次是主任。结果出来了,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宣布后一阵掌声,我坠入五里雾中。
没有就职演说,也没有类似今天的获奖感言,一切就这么简单。我从稀里糊涂中清醒过来,只是把它当作领导和同事对我工作的认可和一种褒扬,并没有去想当什么校长,因为此时的校长由中心校副校长兼任。学校工作都在正常进行,我还是带我的课,也没有出席过什么校委会之类的会议,我充其量把这个头衔当成民办教师的代表而已。
这一年暑假结束,学校原来的领导调走了,我在同事们的催促下,到中心校所在地古松庵中学请派校长,恰好教育组书记也在。他说再不往你们那儿派校长,你就是校长!我顿时涨红了脸,不知所措,连忙推辞:“那不行, *** 不了,我们那里原来是中心校,去年才撤并,还有两个初中班,七八个公办教师,您还是派一个公办校长吧!”我想:我一个“民办”怎么去领导“公办”呢?此行没有结果,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学校。怎么办?马上要开学,总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耽误开学吧。于是又在同事们的催促下,开始张罗开学的事。没有上级书面任命,也没有上级领导来学校宣布,就这样赶着鸭子上架,稀里糊涂当起了村校校长,慢慢进入角色,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但总是有一种被哄上楼突然撤掉梯子的感觉,心里空空的。
我这个人做事总不顺,喝口凉水也塞牙缝。1987年任中心校长,不到一个月民利乡 *** 撤销,民利乡变成了民利管理区,民利失去政治中心而被边缘化;1998年调桐柏中学,刚刚一年镇 *** 撤销,又一次被边缘化;2002年我主持桐柏中学工作,“一费制”成了现实,学校陷入困境。这一次刚刚当这个校长, *** 没有坐热就来了麻烦事——要精简民办教师。工作者和村干部就精简人员问题没有向我征求过意见,被精简的人也不相信我刚上台能有多大的建议权而迁怒于我,让我避过一劫。但麻烦还在,原来的炊事员减了,学校食堂没有人烧火,“民办”的可以回家吃饭,那公办教师呢?就像一部机器少了一个螺丝就不能运转。我一方面找村干部要人,另一方面除了要求教师按课表上课,还要临时安排人做饭。每天看哪个老师上午或下午没有第三节课,还要看哪位会烧火,一餐一顿的安排,一直持续了两多月。哎!真够婆婆妈妈的,说来惭愧。
我当校长凡事商量着办。不飞扬跋扈,不独断专行,不搞“一言堂”。这种工作作风有时有点麻烦,但对工作有利,便于把工作搞顺畅些,现在时新叫“和谐”,不把关系搞得剑拔弩张。每学期排课,要知人善用,统筹安排,对于个人而言相当于生产队派工,那是一天天地派,这一定是一个学年。关系到负担轻重,搭档“好坏”,学生成绩和品行优劣。无论学校的类型、规模怎样不同,但每学年分课都是开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挑肥拣瘦的,有避重就轻的,有选择搭档的,有选择班级的,将就了张三又不合李四的口味,反之亦然。用行政手段也不是不行,可能因为不公平的原因或教师的片面看法导致一部分教师有意见,不服气:轻,则在分课会上公开反对,导致会议“炸把”,重新分矛盾更多,将就某人吧,其他人会说你怕“狠人”,不将就又会形成僵局,整个一锅“夹生饭”。重,则教师带情绪上课,少数觉悟不高的甚至误人子弟。生产队安排工,有人觉得不好有磨洋工的,那只是一天,如果教书磨洋工就耽误一年,耽误了几十个学生,浪费的是学生一年的青春。我的办法是:一是细,尽量把工作想细、想全面,综合教师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包括性格、爱好,制定一套或几套比较合理的方案,宗旨是扬长避短,人尽其用,充分调动积极性,同时考虑教师个人困难、特殊情况,包括身体、家庭等方面,设身处地为教师着想;二 是先,思想工作做在先,逐人逐人征求意见,解释、协调,估计工作难做的先做,对于少数“叫鸡公”拿出几套方案供其选择,说难听叫“逼其就范”;三是严,一旦形成决定必须坚决执行,一鼓作气“把饭煮熟”。由于我把工作做在前头,工作做通了,做顺畅了,宣布只是一个程序,一个仪式,不会出现“炸把”的情况。把它比大点,就像外交文件,事先已经逐条敲定,签字只是一个仪式。我在小学是这样,在中学也是这样,把校长放在与教师同等的高度而不是居高临下。这种工作作风有时比较麻烦,我认为是处理好干群关系的好办法,有少数领导要面子或想耍威风,结果适得其反,要威风没威风,要面子没面子。
村办小学经费总是紧张,总是没有钱,如果说教育是清水衙门,那村小就是穷光蛋。按规定收取的学费除了教学日常开支,所剩无几。每个月公办教师发工资,教研组七扣八磨,学校除了一摞白纸条几乎没有现钱,怎么给他们发工资呢?几乎每个月都这样,学校会计拿着一摞条子哭丧着脸找我说,又扣了多少,应该拿出多少才能发工资。我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商量解决。根据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年轻的负担小,就多压点,承诺什么时候补上;家庭困难的就酌情少压点或全部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也不容易,一家人靠这点工资过日子。把工作做在前面,即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又避免了矛盾,,免得发工资会计与老师发生争吵,当然这时候发工资与我们“民办”无关,我完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就这样借新债,还旧债,债债相连,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商量办事是单位的滑润剂,加在旧机器上,也能使之满负荷运转 。
我当校长凡事带头做,不敢学高为师,但求身正为范。按时到校,坚守岗位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但在分田到户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有的公办教师搞“假三天”,星期六下午离校,到星期一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到校;“民办”则是见空插针,抽空忙生产,上节课还在上课,一转眼就不见了,他会马上出现在责任田里。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是小事,星期天我也在种责任田,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早早放工,没有办法顾及田间地里还有多少事——也许坚持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饭后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到学校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当远道而来的外地老师陆续到校时,迎接他们的是我办公室窗口的灯光。
如果星期六上午第三节课没有课,我也可以提前回家,我不能那样做。既使没有紧急事,看看书,挨也有挨到放学的时候,和同志们共进午餐后,再与他们道别,明明知道田地里有多少事等着我,即使下午不休息,干到天黑也不能早退一节课。有一天下午,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滚滚,远处不时传来隐约的雷声,天,要下雨了。我正在上第三节课,短短几十分钟就有几位老师在门口小声叫我,说家里带信稻场晒的小麦冇收,叫赶快回家。我心急如焚,晒干的麦子见雨就全完了,恨不得立即飞到稻场;但理智告诉我,我不能走,教室学生几十双眼睛看着我,全校教师十几双眼睛看着我。教师的战场在教室,教师的职责在学生,前方打仗的战士,如果听到家里有事的消息,不顾对面敌人的疯狂,扔下身边的战友,撒腿就往回跑,那还叫战士吗?我们离家近,可以回去,那离家几十里的老师家里也晒了麦子,他回得去吗?我坚持上完课,放学回家看到一堆湿漉漉的麦子,哭笑不得。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没有少挨父母的训斥,没有少挨妻子的埋怨,然而我耽误的农活,没有耽误工作。
分田到户两年后,我家又是老、又是小,唯一的男劳力心思又不在田地上,体弱多病的妻子已经整得够呛,向我提出在学校旁边开一个小卖部,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少种点田,可以做到收入不减而体力劳动强度大减,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是这样,从八十年代开始一边教书,一边经商——何况那个时候个体做生意的少,钱也好赚,一直到后来,也许手中少有积蓄,不像现在清风两袖,两袖清风。事实证明为数不少的人是走这条路的,有教师,有干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一提议,表面的理由是精力顾不上来:又要教书、又要种责任田,还要抽空自学——转正的念头时刻在折磨我,如果再搞经销,时间上算不过来。而骨子里的想法觉得又教书育人又赚钱,而赚钱的对象是我的学生,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心里不踏实,别扭。你在课堂上道貌岸然地对学生进行理想、前途、道德品质的教育,大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盛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民族精神,下课后马上面带微笑地招徕顾客——刚下课的你的学生们,不是来个正负抵消、酸碱中和吗?你在大会小会上煞有介事地大讲教师的道德修养、专业素质亟待提高,还在念叨大教育家的名言“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会后慌慌忙忙骑着单车,汗流浃背地进货、卖货而拼命赚取差价,你的说教还有几分力量?在人们心目中恐怕不是“苍白无力”那样简单,纯碎是一个伪君子!也许我的观念老化,当时年纪不大但过于迂腐,也许经济社会应该是这样:周一到周五学生的偶像、他们的老师到了周六和周日就成了培训班老师,收取几倍于过去一年的学费而拼命捞取外快;要求学生购买各种资料,在课堂上大肆宣传他的巨大作用而拼命捞取回扣;有的把座位作为资源,拼命接受家长的“馈赠”。推而广之,经济社会也许是:相当一级的官员,在主席台上作报告,大讲反腐倡廉,讲得慷慨激昂,对 *** 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比杀父之仇还要恨,信誓旦旦地表达反腐的“坚强决心”;回到家中面对红包一并笑纳,脸不红,心不跳。时至今日,我对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就是对不起我的家人,当然也对不起很容易到手的钞票,但我没有让铜臭影响我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上级要求全面开科,特别是加强体音美教学,我这个五音不全的数学教师也 *** 教起了音乐。在办公室请同事手把手教,有空就练习,一个星期后我给学生教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先教简谱,再教歌词。偶尔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说,你教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我们还会唱呢,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要求教师用普通话教学,今天的教师不在话下,那时候就不同,大部分是“土克西”。语文老师教拼音还可以,如果要一节课都用普通话就困难了,至于说其他学科的教师说普通话那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像。怎么办?我先上!用普通话给全校老师上了一节数学课,尽管发音不准,声调错位,不时还夹杂红安土话,但毕竟开了个头。以后普通话就在这小小的校园开展起来。
教师是知识分子,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看到领导身体力行,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怎么做,就比较容易了。
我当校长力求办学正规,哪怕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学校。偏远的农村小学,正规不正规,完全取决于该校校长,因为上级不可能天天派人监督或检查。有一次我到邻村学校监考,规定八点半开考,九点老师还未到,学生还陆陆续续不紧不慢的走在上学路上;有的学校没有时间表,有时一上午上两节,有时上一节,几乎没有第几节的概念,就像生产队休不休息、休息多长时间全凭队长一句话;有的两个教师一个班,搞“半日制”。有一次看到一个教学点的大门上赫然写着“明天天晴就放假,天变就上学”的字样……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种放任式、游击式的教学模式在我管辖的学校是不存在的。我的理解是,学校就要像学校,不能是生产队,不能是畜牧场。
我所在的也是小学校,有时间表、课程表、任课一揽表……并能按表运作。钟声就是命令,它相当于部队的军号,尽管没有真正意义的大钟——用一截钻井队废弃的钻头代替;包括钟声信号都有严格的规定,上课钟声敲几下、 *** 钟怎样打,不是乱敲一通。虽然大部分人离家近,有的只有几百米,还是要求全体教工在校住宿起伙。学生组织齐全,有少先队、学生会,有学生干部值日,有教师轮流值日;学生路队有专人护送,并规定必须达到的地点。……
值日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职责是司钟,而司钟离不开钟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位教师有手表,掌握时间只有唯一的一个座钟,它“血统”比较高贵,是解放初上海生产的“555”牌座钟,只可惜它老了,腿脚不太方便,时走时停,如果它 *** 学校就乱套了。老师们分析来、实验去停摆的原因是放置不平,于是就有了每天对这个宝贝疙瘩的摆弄。今天放学了,值日人把它交给继任者——明天的值日官,双方交接时小心翼翼,生怕惹怒了这位尊者。明天值日老师把它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纸折的小条儿,把它垫在座钟底部的前后左右,调整着水平,差一点用水平仪了。一边调一边等,等到它发出均匀的“滴答滴答”声时,上好发条,估计明天可以工作一天。
学校规模小,教师少,有的学校实行“包班制”——一个教师包揽了全部课程,这样做的好处是教师对学生有更详细的了解,因为接触学生的机会更多,当然不用排课;不好的是上课随意性大,一节课上什么完全取决教师的随机选择。我们学校这种情况也不包班,采用交叉带课。有一年我们学校只有六个老师,还是五个班,虽然一节课只有一个人空堂,还是按课表上课,一天下来都很累,但秩序仍然井井有条。
勤工俭学也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上级要求,也是学校的需要,可以增加收入,聊补教学经费的不足。我们因地制宜,同时考虑学生的安全和体力的因素,主要是捡花生和摘茶叶,既培养学生劳动观点、端正劳动态度又力所能及。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勤工俭学意义再大、作用再明显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原则是不能影响教学。我们三里岗有一个比较大的茶场,摘茶是农忙季节,人不好请,因此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学校身上,一两个星期不上课他们也欢迎;作为学校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给老师发福利,何乐而不为?我没有那样做,规定摘茶季节一周最多两次,一次半天,各班轮换,不搞倾巢而出,宁可把摘茶的活介绍给兄弟学校,相当于把订单让给同行,也不利用学生的廉价劳力为学校创收,为个人谋利。
绵绵秋雨,一连下了几天。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小雨还在断断续续地下,淅淅沥沥的;阵阵北风挟裹着温柔的雨丝,飘到刚刚被秋风染红的枫叶上,飘到路边小松树碧绿的针叶上,飘到路人的身上,送去丝丝凉意。天完全黑下来,泥泞的小路上走来三个人,他们没有受这习习秋风的感染,依然洋溢着夏天火一般的热情,一路说笑着走来。他们打着雨伞,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大踏步向细屋杨家走来。路上到处是小水坑,一个连着一个,他们踮起脚,步伐矫健地跨过一个水坑又跳过一个水坑,快速地跑着、跳着,像猴子跳圈一样。忽然,前面的靴子刚刚抬起,后面的球鞋重重地落在水坑里,溅起的泥水刚好落在前面的靴子里,“靴子”一边脱鞋一边佯怒道:“怎么搞的!”“哈哈,精确计算的。”“球鞋”调侃着说。前面的路更加泥泞,全是黄泥巴,手提靴子的“靴子”此时反而轻松,“球鞋”在后面一步一扯,步履艰难,忽然一只鞋陷在泥巴里拔不出来,“靴子”报复性地顺势将她一扯,两只鞋都陷在泥里,两只脚孤零零地站在泥中。“这也是精确计算的!”又是一阵笑声。“别闹了,快到了”三人中年龄大的一位发话了。此时塆里传来阵阵狗叫声,像是迎接这些雨夜来访的客人。他们是大屋杨家学校的老师,今晚兵分几路,夜访未上学的及龄儿童,这三位是动员细屋杨家塆的一户人家的两个女孩上学。这一家是“钉子户”,情况也特殊。他们家一连生了四个丫头,为了生一个男孩,分别叫望娣、盼娣、招娣和后娣。年年上门做工作,家长年年油盐不进,一直到老大老二超龄——已过了十二岁,现在老三老四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还在家里放牛,动员这姊妹俩已经是第三次了。
另外的三位,此时已经坐在细屋宋家塆的一个女娃的家里。这一家情况更特殊,男主人两年前不幸去世,留下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大孩子是个姑娘,刚满十岁读三年级,这个学期读了不到一个月就辍学了,妈妈要她在家照看小弟弟。小女孩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好,老师都喜欢她,学校不收她的学费,班主任给她找几本旧书,数学教师是女老师,自己掏钱给她买笔,买发卡,都鼓励她克服困难坚持读下去。她也很听话,也表示要努力学习,报答老师,下决心把小学读完。就是她妈不乐意,三天两头把女儿骂一顿,逼她驮书包回家。班主任邀科任老师上门做工作,孩子上几天学,过几天又不见她的人影;又走访,又来几天,已经反反复复好几次了。也不能责怪她妈妈,一个妇道人家,又种责任田,又要带一个三岁的小孩,有一次把小男孩带到地里摘花生,差点掉到地边的塘里。这个女人也怪可怜的,三十岁就像四十的人一样,又瘦、又憔悴。这一次女主人很感动,又是泡茶,又是炒花生。这么黑的天,又下雨,老师的衣服都湿了,还不是为我的女伢吗?并拍胸保证不再麻烦老师,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完小学。临走把老师送出大门,站在雨中千恩万谢,目送着老师远出。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这是老师们无数次家访动员适龄儿童入学的两幅极平常的画面。上级规定,适龄儿童入学率要达到95%,同时青壮年文盲不超过10%,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为了学校应尽的社会责任,为了教师职业的一份崇高与神圣,为了千百个孩子的未来,让他(她)们能接受起码的教育,我和我的同事们,自觉地、踏踏实实地做好这份工作,当时没有或很少有后来“普九”(当时是“普六”——要求学生受完小学教育)时期应付检查的花花肠子。
首先是搞好普查。全村十个村民小组,约四百户要入户调查,登记年龄在零至四十五岁公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汇总编成《文化户口册》;一个家庭一页,一个小组一分册;据册造表:一份“适龄儿童入学统计表”,一份“青壮年文化程度统计表”;做到人头、表、册三对号。
二是抓好关键时间,现在时新说法叫“时间节点“。1是开学前,特别是新学年开学前,先根据《文化户口册》摸清今年的新生应该有多少,各个小组分别有几个,然后调查新生中有没有不打算读的,老生中有没有打算辍学的,再分头做工作,重点是女童。如果开学前不走访,错过了开学的黄金时间,家长就有“理由”不让小孩上学,势必事倍功半。2是每天清查人数,发现未到校的及时走访,是病了,能体现对学生的关心;不是病了,就做家长的工作,也许能打消家长让学生辍学的念头;如果时间一长,学生掉课了,再上学成绩跟不上,学生的厌学与家长的想法相吻合,那工作就难做了。
三是持之以恒,把普及教育贯穿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去年达标,不等于今年就一定能达标,要巩固好学生,不是在于一朝一夕——在那经济不发达时期。不能抓普及的时候想到普及,验收一完就万事大吉。你班今天有一个调皮的学生,你不去耐心教育,而是简单粗暴甚至于打他,明天要查巩固率,你再去请他返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学生基础差,作业不交,考试不及格,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课后个别辅导他,而是大骂“蠢材”,甚至叫他“滚”,他厌学了,接着辍学了;到检查普及的时候,你还有何面目去请这位昔日你“深恶痛绝”的差生?为了孩子们,也为了你的脸面,你要用爱留着孩子,用爱留着他(她)们的心!不是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吗?就凭这句话,你就应该用父亲般的爱去关心、去呵护每一个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耕耘就有收获。从1982年起,我们学校连续五年适龄儿童普及率、在校学生巩固率,学习成绩合格率年年达标,受到前来检查的地县领导的好评和褒奖:“工作最扎实,表册最清楚,合格率最高”。
如果说普及教育是办学的软件,是用心去做,那么改善办学条件就是硬件,要用钱来说话。
我们学校历史并不悠久,1961年草创于大屋杨家祠堂,两个老师两个班;1969年迁往现址,地名叫茅屋岗,可能是名字不太雅观,就叫大屋杨家学校,后来恢复老地名,叫三里岗村校。校舍坐北朝南两排平房,坐东朝西还有三间,一共15间房子成横着的U 字形,它的开口处原来是一段围墙,是干打垒的土坯墙,天长日久、风吹日晒,已有部分倒塌,后来干脆推倒,成为一所纯碎的无围墙学校。
“村小”的全称是村办小学,根据国家分级办学的原则,它是村一级管理的学校,村里不仅有管辖权,还有办学权,有给学校提供资金的义务,包括民师的工资、校舍的维修和小型建设。然而我们村穷得叮当响,既没有赚钱的企业,也没有上级扶持,一个林场、一个茶场能养活他们自己就不错,连村干部的工资都是靠农户上交,根本没有财力顾及学校;倒是我们给村里档了不少门风:村里开个会、上级来检查什么的,又是茶、又是烟 ,有时还要管饭。几年来房子漏水自己修、小型设备自己置,经济上从来没有找过村里。有一年学校需要更换缘子,我们直接找各小组,没有现成的木料,他们叫我们直接到山上去砍。我们分成几个组,我带六个学生到龙王山砍了四棵松树,我一人扛一棵,一棵活树上百斤;重是小事,关键是松毛虫多。一棵树上几十上百个,锯一拉,松毛虫像下雨一样往下掉,掉在头上、掉在手上,有的直接掉进颈窝里。顾不得一阵阵肉麻,顾不得全身奇痒,顾不得去仔细端详那毛茸茸的狰狞模样,一心想快砍快回,赶快离开这恐怖的地方。结果我的手开始是星星点点的红包,后慢慢长大,最后连成一片,不一会手臂“胖”了一圈。
1984年秋开学后,上级又布置了新的任务:彻底消除校舍危房,确保师生生命安全,是全面改善办学条件的第一个举措。当时最严厉的提法:当政治任务完成——延续了“政治挂帅”的思维。不管怎样的提法,在中国只要党和 *** 重视,什么事情都好办。于是民利乡 *** 召开了各村财经主任和村校校长的专题会,乡长亲自主持,内容是消除学校危房,迎接地县两级的检查。会上传达了上级指示,提出了总体要求,最后各村汇报情况。前几位村小校长不知道他们村是真的积极办学,还是当着财经主任的面有意恭维,或者怕得罪村村干部以后办事更难,都在会上报喜不报忧,尽捡好的说,什么书记、村长、特别是财经主任如何积极改善办学条件云云 。我最后一个发言,都以为我和前面的发言一样顺着竿子上,不料我的发言令在坐的人大吃一惊,讲了一通大实话,历数村里不顾学校死活,至少近三年没有拿一分钱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好在我们村的主任上台不久,对过去的事不需要负责任,但脸还是红得像关公似的。中心校的领导和其他村校校长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担心我当着乡长泼了村干部的面子,以后为改造危房会更难。此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是实话实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知是我的发言起了作用,乡 *** 给我们村施加了压力,还是财经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想踏踏实实做点事,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我的大实话不是激将成了激将,歪打正着地发挥了作用,六个村只有我们村真正行动起来,其余的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干脆一滴也不下,导致两个月后地县两级检查组驱车前往我校时,中心校早就通知公路沿线的其他学校不要升国旗,以免检查组误入其中而漏了马脚。
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有村委会的行动,我的底气更足了。我向村委会汇报了改造项目:门窗要换,玻璃要安,椽子要添,房顶要修,水沟要砌,室内外要装修,门窗要油漆等。村委会要求学校负责施工,所有费用由村负担,这一回让村里扎扎实实放了一回血。一时,人伕轿马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校,石工、木工、油漆工来了,砂石、水泥、石灰来了,木料、玻璃、油漆来了;屋上是换瓦换椽子的,地下是砌墙砌水沟的,“叮叮邦邦”是木匠在做门做窗,“突突突突”是运送材料的手扶拖拉机……
一个月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屋面、外墙平平整整,教室墙壁雪白雪白;崭新的门窗漆成墨绿色,闪着耀眼的光泽;透过明亮的玻璃看到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房前屋后笔直的水沟把校园的空地、操场规范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她像一个憔悴的女人,描眉画眼、换上新衣后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危房改造后,上级又下达新任务,要求校校有标准的课桌凳,连同上一次一起叫“一无两有”:即“无危房,有课桌、课凳”。我校先改造屠凳桌,而凳子则是要求家长按图纸加工,自己制作成统一标准的课凳。做桌子的木板是原来的老枫树板加工的,桌子的腿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周旋来一批木料,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两有”的任务。
这批木料有上千棵,是一年前乡林业站从农户家中搜出来的,理由是乱砍滥伐,树木要没收并且要罚款;农户说是自留山上砍来做农具的,是政策允许。当时处于转型期,政策不衔接,双方各执一词,因此树木一直放在学校,谁都不敢乱动,上关政策,下关农民利益。如果按正常程序,找林业站、找村组两级,不知会拖到猴年马月才能解决。我和教导主任一起找我们塆的两个小组组长,通过他们与农户协商,树木给学校做桌子,不罚农户的款,他们满意;树木没有退给私人,是给学校做事,林业站也无异议。拖了一年之久的这起纠纷,一夜之间就化解了,皆大欢喜,想不到我也有天随人愿、心想事成的时候!
我这只鸭子被赶着上架:被上级逼着,被同事催着,被学生感动着,被良心驱使着。时至今日,如果昔日的同事回忆过,还健在的家长念叨过,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谈及过——某某人在大屋杨家学校的那些年还算正直,吃过苦,做了一些事,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一滴水流入大海,大海或许不在乎多这一滴;如果流入沙漠,就会显示出它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