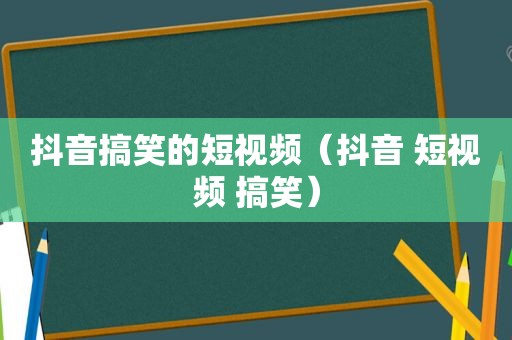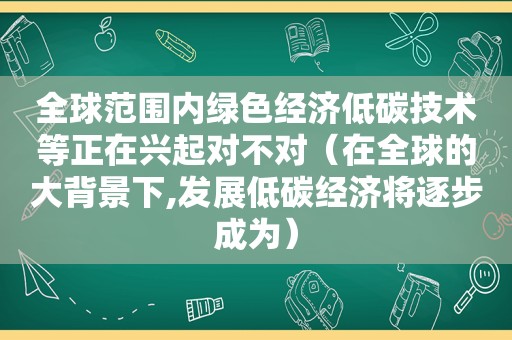本
文
摘
要

提起东北,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是那带着棒碴子味儿的东北话,还是“赵家班”的拿手二人转,抑或是盘靓条顺、性情豪爽的东北姑娘?
说到东北,我脑子里会浮现黑土地,白桦林,松花江,还有无边无际的北大荒。人是很难走出自己的童年的,我对东北的第一印象缘自儿时的一部热播剧《年轮》,这部电视剧是由著名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年轮》改编而成的。
《年轮》讲的是东北哈尔滨6个知青聚散离合的故事。剧情时间跨度很长,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贯穿主人公们的大半生,重头戏是他们作为“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奔赴北大荒挥洒青春和热血。
这部剧是90年代的“爆款剧”“现象级电视剧”,荣膺1995年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长篇连续剧之一。它在当代青年特别是知青群体中间引发强烈反响,不少知青成群结队前往原先下放的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追忆旧日时光。
人是很难彻底走出自己的童年的,《年轮》在我的心底植入“东北情结”。黑土地的厚重,山林的清新,人民的坚忍,好像在我的记忆深处生了根,无法抹掉。
于是,从小到大,有关东北的影视剧作品和文学作品,我都很关注。《年轮》开了个好头,以至于我的口味很刁钻,只喜欢原汁原味的、质量过硬的作品。梁晓声的小说《年轮》,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班宇的《冬泳》,张云的《白驯鹿的九叉犄角》,是我比较喜欢的东北题材小说。读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驯鹿的九叉犄角》,我走近了曾生活在浩瀚林海的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额尔古纳河右岸》主题宏大,是第一部描述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白驯鹿的九叉犄角》则从小处着手,以谋杀事件为线索,聚焦大兴安岭地区日益猖獗的盗猎活动,揭示离开山林之后使鹿人的混乱生活和深层精神危机。
自然之子: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鄂温克族的祖先尚无定论,有说是北室韦和鞠部,有说是靺鞨七部之一的安居骨部。在此不再赘述,留待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去考证。
鄂温克族人世代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部族沿着勒拿河分布,以放牧、狩猎、捕鱼、饲养驯鹿为生。300多年前,俄国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被迫迁徙,穿过森林,越过额尔古纳河,到达了河右岸,开始新的生活。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鄂温克族人口数为30875人。
他们没有固定的房屋住处,住在一种叫作“撮罗子”的简易房子里。撮罗子是用削去树皮和枝桠的木杆搭建而成的尖顶形木棚子。季节不同,制作材料不同,夏天用桦树皮和草帘子,冬天用兽皮。住在里面,夏天不避雨,冬天不防寒,但躺在这里面才能看到森林和星星。这种浪漫大约只有吃苦耐劳的鄂温克人才能懂。
说到吃喝,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天生天养,不愁吃喝。
“咱们大兴安是个好地方呀!那时交通还不便利,很多都是没有砍伐开发过的原始森林,有着数不清的沼泽、河流、草地,驯鹿有吃有喝,使鹿人也能猎取到野兽野禽,捕到大肥又大的鲜鱼,捡拾松子、蘑菇,活得有滋有味。他们住在撮罗子里,共同狩猎,平均分配,和大自然和谐共处,仅从森林中获得够生存的东西。”长年与世隔绝的鄂温克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最独特之处是驯鹿文化。在鄂温克人眼里,驯鹿是吉祥、幸福、进取的象征,也是追求美好和崇高理想的象征。他们把驯鹿看作吉祥物,无论男女老少都非常喜爱和保护驯鹿。
鄂温克族饲养驯鹿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证,可追溯到汉朝以前,而《梁书》中“养鹿如养牛”的记载就是和北方民族有关。漫长的岁月中,驯鹿曾是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被誉为“森林之舟”。他们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关于驯鹿的神话传说极其浪漫动人。
《白驯鹿的九叉犄角》提到,鄂温克族有个传说,人死后,会有一只长着九叉犄角的白驯鹿前来接迎,亡灵乘着白驯鹿,穿过无数的大河和森林,穿过无数的河流和土地,来到祖先的灵魂生活的大海(贝加尔湖),在那里,和祖先们在一起,欢乐唱歌。
鄂温克人认为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段旅途的开始,是人一生中最重要、最神圣的时刻。如果能看到长着九叉犄角的白驯鹿,那是最幸福的时刻!而撒谎的人、不尊敬老人的人、不勇敢的人、背叛祖先的人,灵魂将不被祖先接受,不被白驯鹿接受,永远在烈火和黑暗中沉沦。以前,鄂温克族多信萨满教,萨满多由酋长担任,地位尊崇,是神灵的代言人,肩负着和天地、自然、灵魂沟通的重任。萨满最重要的职责,是指引亡灵回归祖地。
我记得,我的祖先带来过九万头驯鹿
它们的犄角高高扬起,一边挂着太阳,一边挂着月亮
我的那些驯鹿呢,大兴安?
我记得,我的祖先支起九千顶撮罗子
它们矗立在激流河两岸,一边是日出,一边是日落
我的那些撮罗子呢,大兴安?
我记得,我的祖先划起九百个桦皮船
它们在天空中飞行,一边是黑夜,一边是白天
我的那些桦皮船呢,大兴安?
我记得,我的祖先背着九十杆猎枪
它们的硝烟飘荡在森林里,一边是乌云,一边是阳光
我的那些猎枪呢,大兴安?
我记得,我的祖先中有九位大萨满
他们敲响两面神鼓,一面呼唤死亡,一面带来新生
我的那些萨满呢,大兴安?
我记得,这里曾经有一个部落
他们叫自己使鹿人,他们用灵魂与自然交谈
人群里一半是父亲,一半是母亲
我的那些族人呢,大兴安?在《白驯鹿的九叉犄角》中,萨满穆鲁站在高处,对着月亮、山林还有空荡荡的家园高声歌唱这首使鹿人的歌谣,歌声中满是对驯鹿、对祖先、对家园、对森林的纯洁热诚的爱。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弥漫全球的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以打猎和驯鹿为生的鄂温克族,成了繁华世界的边缘人。渴望维护民族传统的萨满,则成为了最痛苦的人。
使鹿人的痛苦: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玛利亚 • 索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她带领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落,一个只有200多号人的微型族群,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玛利亚 • 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这在我们看来,是不是有些难以理解呢?
历史上,鄂温克族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得繁衍,在日俄侵略者的铁蹄和政治运动的阴云下求得生存,他们虽是弱小民族,但在命运面前殊死抗争,彰显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可以说,他们承受住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白驯鹿的九叉犄角》中穆鲁的初恋柳娃即是死于日军枪口之下。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 *** 组织鄂温克族搬迁到山下的定居点,希望他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这本来是好事。定居点有水有电,生活设施齐全,房舍结实暖和。但是,鄂温克人过惯了共同狩猎、平均分配的原始社会生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令他们感到很不适应。
他们习惯了养驯鹿,习惯了随身携带枪。枪对于他们来说,是仅次于驯鹿的存在,是灵魂的一部分。组织收枪的时候,有的人宁死不交,抱着枪跳下了悬崖。这一幕非常悲壮又令人无可奈何。
失去了森林和枪,以苔藓为食物的驯鹿也大批死亡,使鹿人无所事事,了无生气,很多人开始以酗酒打发日子,包括女人和孩子。
“你见过的那种塑料桶,一桶20斤白酒,喝酒跟喝白开水一样,头一年就喝死了七八个!喝醉了就干架,往死里干!”*** 组织禁酒收效甚微。使鹿人组团跑到几十公里外的镇上喝酒。大冬天喝醉了躺在雪地里,冻得硬邦邦。更可怕的是,盗猎活动日益猖獗。大兴安岭里什么都有,飞龙、狍子、灰鼠、熊瞎子,还有使鹿人的驯鹿,在盗猎分子眼里,哪一样不是白花花的现大洋?下夹子、使套子、弄吊杆或者干脆私造枪支,手段五花八门,歹毒凶狠,不光猎杀动物,连守护驯鹿的使鹿人也杀,还有无辜民众惨死在巨型兽夹之下。昔日安静祥和的大兴安岭遍布杀机。
大萨满穆鲁的三个儿子给力克、德布库、乌力吉相继因盗猎者而死,他唯一的孙子维克,也因目睹父亲被杀,受惊过度成了哑巴。
作为萨满和父亲,穆鲁用心给乌力吉和德布库跳了大神,但他根本就没听到神的回应。他痛苦不已,相信神明已经抛弃了使鹿人。 他感觉山川哭了,河流哭了,森林也哭了。
“时代变了,天地变了,山林也变了。使鹿人快完了,也不会再有人接过我的神鼓。”玛利亚 • 索也发出了同样的叹息:
“我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当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一半浅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经分不清天上人间了。”这不是无病 *** ,也不是吟风弄月,这是担心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萨满面对这个繁华又陌生的现代世界,从内心深处流露的忧惧。
在儿子们都死了之后,穆鲁将儿媳和孙子送下山,执拗地一个人住在撮罗子里。孤独的他对偶然认识的亡命徒麻子倾吐心声:
“麻子,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森林一片一片消失,那可是从天地诞生时就一直生长的森林呀!我想不通为什么使鹿人没了枪、没了放养的驯鹿,甚至连萨满都要没了,更别说和神灵、祖先、万物交谈了!我想不通为什么林子里到处是屠杀,那些鸟兽,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不通,我们使鹿人以前没有什么钱,也幸福得很……”人人都爱钱,人人也都知道钱是万恶之源。小说中盗猎团伙头目耿彪和亡命徒麻子杀人如麻,皆因利欲熏心。但是,穆鲁不能理解,他生于森林,长于森林,始终固守朴素自然的信仰观念,没有那么重的物欲和贪念。我们都说无欲则刚,但他的内心痛苦深重。他身为萨满,责任重大,是和天地、祖先沟通的使者。他害怕祖先不能原谅丧失信仰和灵魂的族人,决心自杀赎罪。
穆鲁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者,面对凶残的盗猎团伙,面对来路不明的亡命徒麻子,面对大兴安岭里不断出没的猛兽,他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他的一生,经历了妹妹、父母、妻子、儿子的死亡,这些我们常人眼里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都没有击垮这个鄂温克族汉子。
而和祖先失去联结,灵魂无处安放,这些我们眼里不可思议、玄之又玄的烦忧,却是穆鲁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轻而易举就击垮了他。
大兴安岭深处的枪声
有三拨人相继走入大兴安岭深处。
先是穆鲁和麻子。
穆鲁错拿了亡命徒麻子的皮包,被麻子盯上。至善无意中感动了至恶,麻子和他达成协议,一老一少一同上路,走向大兴安岭深处。麻子需要识路的穆鲁带他走出大兴安岭,他妄图偷渡到俄罗斯境内开餐厅。穆鲁想去祖先的圣地犴马自杀,必须借用麻子的手枪。不用枪自杀,祖先不会接纳他的灵魂。
然后是以耿彪为首的盗猎团伙。
三年前,耿彪暗杀了穆鲁的大儿子给力克,还打了穆鲁黑枪。他唯一的亲人,当成儿子养大的弟弟双响莫名其妙死去,他想当然地认为是穆鲁寻仇杀了双响。他威逼利诱,带着一群同伙摸进大兴安岭,一路尾随穆鲁,伺机下黑手。
最后是警察郝仁的队伍。恪尽职守的郝仁为三道河的民众操碎了心,他希望能阻止大森林深处的罪恶。
最终,一阵枪声,震碎了大兴安岭的宁静。一切都结束了,皑皑白雪染满了血。
小说最后,穆鲁的孙子维克蹬上爷爷的神靴,穿上爷爷的法袍,戴上爷爷的神冠,举起了爷爷的神鼓,缓缓起舞,唱起了使鹿人的歌谣:
我记得,我的祖先带来过九万头驯鹿 它们的犄角高高扬起,一边挂着太阳,一边挂着月亮 我的那些驯鹿呢,大兴安……《白驯鹿的九叉犄角》三次出现这首歌谣,第一次是德布库对着古老的森林吟诵,第二次是穆鲁夜半高歌,第三次是维克唱起爷爷和叔叔唱过的歌儿。这是不是隐喻着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
结语
我曾有幸到访过小兴安岭附近,那是片美丽广阔的土地。天空很蓝,蓝得像童话,树很绿,草很绿,绿意浓得几乎化成流水。比起小兴安岭,大兴安岭应该更美丽更迷人,也更传奇神秘。
读《白驯鹿的九叉犄角》,我感受到了鄂温克族奇特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世界,也仿佛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来了一次奇妙惊险的旅行。雪泡子、沼泽地、林地、针叶林、桦皮艇、撮罗子、山魈、驯鹿、熊瞎子、狼、棒鸡、列巴,加上那里的驯鹿人、盗猎人、苦守三道河的警察……罕见的地域环境、民风世情、饮食习惯,让这次阅读体验如同和穆鲁、麻子坐在火堆边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一样痛快酣畅。
有些人永远留在了大兴安,融入这里的山川林地。作者张云给了他们浪漫幸福的死亡。
《白驯鹿的九叉犄角》着重于使鹿人下山之后的故事, 不经意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边缘民族的某种悲哀。
面对鄂温克民族驯鹿和狩猎文化的逐渐消亡,年逾九旬的玛利亚 • 索向林外的人们悲怆倾诉:“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下一代使鹿人究竟何去何从,盗猎能否禁止,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知道老人简单的愿望很难实现,就像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游子,永远不可能回到梦中的故乡。
世无永恒之物,最终都要消逝。传统和文明的消逝,对于热爱它们的人来说,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而人到底需要什么,到底怎么活着才能快乐?答案可能因人而异。希望每个人都能直面内心的声音。
在《白驯鹿的九叉犄角》之前,我已经读完张云的《鲸背上的少年》《大象马戏团》。三部小说合在一起,构成“动物三部曲”。每一种动物,都见证了一段沉重纠结的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塑造了一个神秘而纯粹的世界。从鲸的纯净,鹿的聪敏,象的坚忍中,我感受到了万物有灵且美。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 张云. 白驯鹿的九叉犄角[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2]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3] 梁晓声. 年轮[M]. 文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