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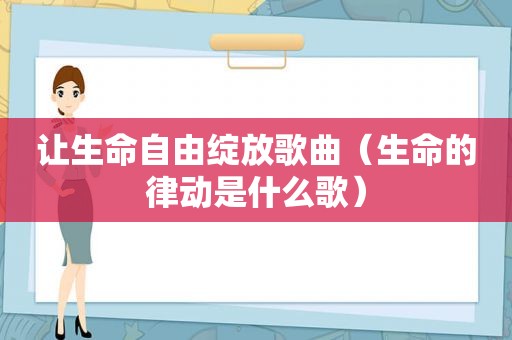
文 | 田青
今晨5时,著名古筝演奏家、画家、潮州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秀明病逝。噩耗传来,不胜悲痛!特选载田青先生大作《禅与乐》中有关杨秀明先生的章节,以寄哀思!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问过“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宗教”的郭沫若,虽然不是音乐史家,但却曾宏观地断定:在中国现存乐器中,但凡一个字的,如琴、筝、瑟、笙、锺、磬等等,都是中国固有的乐器;但凡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的,如琵琶、筚篥、唢呐等等,都是外来的,至少,先秦时尚未在中原流行。郭沫若的判断未必完全准确,但筝这件乐器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不折不扣的民族乐器,却向无疑义。因此,人们就像称琴为“古琴”一样称筝为“古筝”。
筝还有一个名字,叫“秦筝”,类似“楚瑟”,暗示着这乐器的“原籍”。筝还有一个名字,叫“哀筝”,李商隐有《哀筝》诗,其中就有“轻幰长无道,哀筝不出门”的句子。古之诗人咏筝,又常喜用“悲”、“怨”、“苦”等字,仅以唐诗为例:李峤有“莫听秦筝奏,筝筝有剩哀”;柳中庸有“抽弦促柱听秦筝,无限秦人悲怨声”;张祜有“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云寒一夜风”;李远有“座客满筵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岑参说得更明确:“汝不闻,秦筝声最苦……汝归秦兮弹秦筝,秦声悲兮聊送汝。”
但有一首筝曲,却超越了悲苦之情,以出世的高迈与洒脱充分表现了生命的鲜活、自由、灵动,这就是潮州筝乐大师杨秀明演奏的潮州筝曲《行云流水》。
杨秀明(1935— ),是中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我初识杨君,是1977年夏天。那年,我刚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留校任教,去广州番禺寻找冼星海早年的生活经历。在广州,住在文化局招待所。一天夜里,月白风清,我坐在阳台上乘凉,一边盘算次日的日程安排,一边悠闲地欣赏着远处一棵老榕树山峦般的树影。那树影像一掬巨掌,以同样的悠闲托着一轮朗月,任月华在掌心缓缓游走。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筝声。
筝声很清、很柔、很美,分不出声音的远近,但却分明包蕴着某种超越了音质、音色,超越了技巧和风格的东西。那时候,我刚刚结束四年音乐学院以西洋音乐为主的“正规”教育,把时间全花在分析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的和声、曲式上了,对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听过民间音乐大师的演奏。但那筝声,却依然唤起了深藏在我血液里的审美基因和对纯真音乐本能的向往。当我寻声而去找到弹筝人的时候,才发现这位因为怕吵到别人而躲在公共厕所兼冲凉房里练琴的中年男子。当时,他赤膊、短裤、拖鞋,双腿分开,十分专注地流汗与弹琴。这位在特殊环境里用特殊的姿势演奏特殊音乐的男人,就是杨秀明。
我后来知道了杨秀明坎坷的经历,也许是命运为了锤炼和栽培一位音乐大师吧,他在青年时便因错案而锒铛入狱,错失了少年得志的机会,却得到了一份超乎常人的韧性、耐力、精神,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与佛结缘的缘分。1981年,杨秀明因北京古筝研究会会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曹正的大力推荐,应邀至中国音乐学院执教,十年间,树桃培李,成绩斐然。出色的古筝演奏家邱大成、林玲、李淑萍、王勇、李萌、周望;琵琶演奏家李景侠;胡琴演奏家刘顺等,皆曾蒙其教诲。
我当年在为他的唱片所写的序中,曾这样评价他的音乐: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雅而不矜,丽而不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清朗恬淡、光明洞澈。如莲花不着水,如日月不住空。由于其艺术修养的广博,更因其对中国禅学的修养,使他的音乐能超脱一般世俗音乐的审美观,达到静心、开智、增慧的作用。
杨君音乐之外兼善丹青。其客寓京城之时,居中国音乐学院教工单身宿舍,乃恭王府墙内夹道里一陋室也。方不足八平方米,木床下,塞满或用过或未用过的宣纸。那时,我恰好随杨荫浏先生攻读研究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课室和学生宿舍,就在这个夹道旁边。因此,我读书写作之余,就常跑到他这里闲聊、喝茶。就是这样一间陋室,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充满 *** 与幻想的“理想主义”时代,曾将简陋、清贫与精神世界空前的丰富与自由融汇在一处,而杨秀明的琴艺与画艺,也在这“谈笑有鸿儒”的狭小空间里得到了提高、释放、尊重。赵朴老曾为其题词曰:“海潮往复高低呗,林鸟和鸣大小弦。早许音声为佛事,不期画笔落梵天。溪头池角鱼蛙乐,牛背山腰岁月闲。画到未生前面目,雄鸡一唱破重关。”
文如其人,乐亦如其人。《乐记》中说:“唯乐不可以为伪”,诚哉斯言!杨君隐逸一生,信佛茹素,尤具古人之风。我与杨君相交凡三十余年,可记者无数,仅举印象深刻之数琐事,以勾其轮廓:
其一,我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移居东直门外新源里音乐研究所宿舍,当时尚无私家电话,更无手机之便利,但杨君基本不用“共享电话”呼来唤去,时而起心动念,欲与我晤谈,则不打招呼,一人骑自行车“出城”来访我,倘若我不在,则掉头骑车回家,来也悠然,去也悠然。幼读古诗,见古人有“小扣柴扉久不开”句,知魏晋时王徽之雪夜乘船访戴逵“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典故,而时人有如此之行者,唯杨君一人耳!
其二,20世纪90年代某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跑到杨君的宿舍去看他。因为下午要去北海静心斋参加一个纪录片拍摄,我还穿了一身崭新的白色亚麻西装。没想到,前晚下了一夜大雨,他的宿舍被雨水浸泡,屋里跟屋外一样存着一尺左右的积水。泡在水里,蹲在椅上,我俩谈性不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他拿出两个大馒头,我俩一人一个,权作午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那天我俩像在船上一样蹲踞椅上一边神侃一边啃馒头的情景,当然,我更希望有缘看到那集讲述佛教音乐的纪录片的观众,不要太在意那位“专家”穿着的那件皱巴巴、沾着泥点的白色西装。
其三,1989年春天,我去潮州开元寺为赵朴老担任顾问、我担任主编的《中国音像大百科·佛教音乐卷》录制《潮州佛乐》。录音结束后,杨君与我同游觉山。当我站在山顶,迎着猎猎海风远眺大海的时候,那苍茫海面上的点点渔帆,不知为什么竟让我胸中一热,一刹那间百感交集,自觉男儿一生,当有所担当。后来才知道,那一天,开始了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
1992年9月8日,由汕头市文化局、中央乐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北京音乐厅八单位联合主办的“杨秀明古筝独奏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应杨君之邀,我亲自担任主持和解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天他弹的什么曲目、我说的什么话,都已经模糊,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两个场景:一是他初登舞台、落座筝前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演奏,而是默然 *** 片刻,像是入定,又像是为众生祈祷。待他双手触弦的一瞬间,银瓶乍破,乐泉汩汩流出,沁人心脾……其二,是他演奏的最后一首乐曲《行云流水》。这首乐曲,是杨君自创,以即兴为主,似曲水流觞,又信马由缰,让真性情随着音符释放,让音符随着真性情流淌。这首乐曲,可长可短,每次演奏都有所不同,每次演奏,都会赋予音乐以新的乐思、新的乐句、新的结构、新的意境。那天的演奏,杨君似乎用情过深,以致忘却了时间、忘却了空间,任那充满禅意的音乐如行云流水般奔泻了大约20多分钟,其长度超过了任何乐器独奏曲应该有的长度。我在侧幕暗暗为他着急,怕他一直弹到天明!奇怪的是,音乐厅里的全体听众,居然像着了魔似地被他的音乐引领着,随波逐流,任意平生,直到他戛然而止。
1992年第4期《佛教文化》有一篇文章《离声之响——记“杨秀明古筝音乐会”》,这位署名“妙音智”的作者用一大段真诚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在现场聆听杨秀明音乐的感受,仅录其文,以飨读者:
杨秀明先生欲将其几十年的生命与艺术体验,凝聚于他自做的《行云流水》中。他曾说,这几十年的生活感受(顺逆、悲欣?),使他悟出了许多道理,而欲以“行云流水”这一洒脱的意境来比拟。是的,云、水的千姿百态,历来是古今中外文人笔下(琴下)所钟情之物。又因云能无形无有、水能随器而居,更为善用比喻的佛教常引为解说“性空缘起”、“真如妙用”的境界。佛法又向以慈悲济世为主题,僧人出家后,云游四方,参访名师,入道后,随缘化度。因此,寺院称接纳外来游方僧人的去处为“云水堂”,以示“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律中明确比丘(意为乞食者)维持三衣、一钵、一杖,或行头陀,坐于露地,依于裸石,夜卧荒冢之间,精进向道;或结庵而居,受众供养,讲经说法,弘化一方。这在表面上看去,确有些超然之味,想来应是远离人间了。然而这首《行云流水》却从第一个音开始,就打破了你的妄想。
在我们眼前仿佛展开了这样一个场面:(镜头向极远处望去),有一行人在路上缓慢地走着,(随着镜头推进),我们看清了这是一队去举行放生仪式的行列,其前为主法的僧人,后面跟着的是男女老少的居士,当中还有一些尚未懂事的孩子,他们正走向一条河边。间或我们听到几声木鱼和引磬之响,耳边有一阵由远而近的笛声,似乎在暗示着什么,而又未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他们来到湖边时,本来是阴沉的天空,这这时更加晦暗,河水也变得浑浊起来。僧众在老法师的引领下开始做法,木鱼、引磬合着祈祷的经声。浓云密布,下雨了,豆大的雨点抽打着水面,淋湿了人们的面孔和衣衫——音乐转到一段长时间的不和谐与扭曲之中——我们看到,满满几大桶的活鱼、活鳝、泥鳅等,在极少的水里痛苦的扭动着,吐着泡沫,挤在几只笼子中的禽鸟也相互冲撞拥挤、躁动不安(它们本来是以送到集市,即将被人活活宰杀食用的)。(一个特写)老法师紧缩的眉头、消瘦的面颊与几乎是嗫聂蠕动的嘴唇。他心中在想,罪孽深重的有情,实难度脱,唯仗皈依三宝之力,方能免离恶趣之苦。而旁边的人却不禁暗想:佛力真的是无边的吗?这些鱼鸟真的能得救吗?纵今放还,不是仍难免再遭网捕,即使得免,难道又能逃离彼此残杀之苦吗?突然木鱼紧敲几声。随后,慈悲的主题骤然而起。在深思了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皆曾为我父母,众生亦本来平等,相互维系,而却于此无知,自他相害,同类之间你争我斗、异类之间弱肉强食等等现实之后,一种追求息灭众苦,给予安乐之心油然而生。“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在慈悲之旋律中乐曲转换为欢快、明朗、和谐的调子——诵经已毕,人们把一桶桶活鱼轻轻倾入水中,又打开了拴紧的牢笼……这时,雨住了、天也晴了,天空现起彩虹和祥云,河水变得清澈见底。得到了解放和祝福的鱼儿们欢畅的向河心深处游去,鸟儿们纷纷展翅高飞,鱼跃于水、鸟翔于空,自由的世界,自由的心灵,大地万物在雨后的阳光中更加欣欣向荣。善良战胜了邪恶,人间净土恍然降临,孩子们拍手而歌,成人们则泪流满面……就在这盎然的旋律中,演奏者俯身连续在古筝上往复拨弹,十几下、几十下、上百下、直如行云流水、流水行云,全场听众都为其忘我的演奏和娴熟的技巧所激动,不自觉地鼓起了阵阵掌声……
杨秀明的潮州筝曲,得潮州音乐真传,无论其继承古曲,还是随兴而奏的“新”曲,都禅意浓郁、韵味深长。除了杨君本人的修养外,潮州音乐本身的特色与妙处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潮州音乐与泉州南音一样,被视为“华夏正声”,是我国汉族传统音乐中最古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音乐品种。中国古代先民的创造,至今在潮州音乐的宫调、音阶、乐谱中魂魄俱存、仿佛唐宋。潮州流传的“禅和板佛曲”与“香花板佛曲”,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好的佛教音乐,清幽淡雅,古趣盎然;潮州大锣鼓,是遍及中国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锣鼓乐中的奇葩,其气势之雄伟,可撼天动地。被称为“弦诗”的潮州古典弦索乐,细腻委婉、柔媚动人。潮州音乐至今仍在使用的“二四谱”是十分古老的谱式,以潮州方言“二、三、四、五、六、七、八”为唱名,在其独特的律制中,“si”、“fa”二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潮州音乐独特的韵味,同时构成潮州音乐“轻三六”、“重三六”、“活五”、“反线”等多种调式,其中“重三六”的弦诗多出现“si”、“fa”。活五多出现“si”、“fa”和“re”。“re”的高低变化是“活五”的要点和精华,在筝人的指压下,这个音可以升高半度左右或至一度音;弓弦乐器演奏时, “re”字要活按,指要捞上抹下,所以称为“活五”。“轻三六”多出现“la”、“mi”。“反线”多出现“la”、“do”、“re”、“fa”,其中“fa”是骨干音。“轻三重六”类似“轻三六”,多用“la”,而又用“fa”,且以“fa”为关键音。潮州音乐在演奏上强调充分发挥“作韵”和即兴加花的技法,保留着中国传统音乐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我们所说的禅意——突出生命的鲜活、自由、灵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