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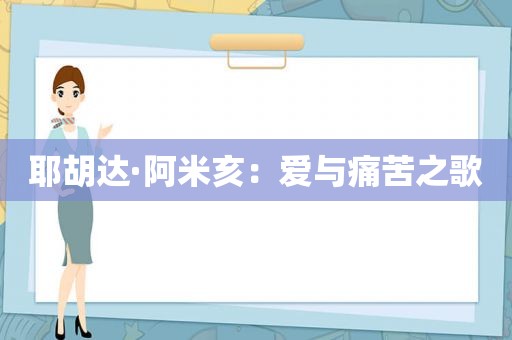
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诗人之一。生于德国的乌尔兹堡,十二岁时随家迁居以色列,二战期间在盟军犹太军队中服役,目击了以色列独立战争和西奈战役,战后他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师,先后出版了《诗:1948-1962》《现在风暴之中,诗:1963-1968》《时间》等十余部诗集。诗作被译成数十种文字。
阿米亥曾获得众多的国内、国际文学奖项。1982年,因为“在诗歌语言上的革命性变化”,阿米亥获得了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奖”。在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当年的获奖者之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朗读了阿米亥的诗作《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阿米亥的诗透明、睿智、幽默,富有人性的思想和力量,善于使用圣经和犹太历史作为诗歌意象,把日常与神圣、爱情与战争、个人与民族等因素糅合起来,因此他的诗多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普遍命运,想象力极其丰富,具有深远的哲学意味和语言渗透力。
本专题通过比较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选出阿米亥脍炙人口的经典诗作,同时也是翻译佳作的集成。
摄影:[美国] 拉夫·吉布森
诗歌:[以色列] 阿米亥 翻译:傅浩等
选编:徐淳刚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没有足够的空间
去容纳每一个欲望。
《传道书》的说法是错误的。
人不得不在恨的同时也在爱,
用同一双眼睛欢笑并且哭泣
用同一双手抛掷石块
并且堆聚石块,
在战争中制造爱并且在爱中制造战争。
憎恨并且宽恕,追忆并且遗忘
规整并且搅混,吞食并且消化——
那历史用漫长年代
造就的一切。
人的一生没有足够的时间。
当他失去了他就去寻找
当他找到了他就遗忘
当他遗忘了他就去爱
当他爱了他就开始遗忘。
他的灵魂是博学的
并且非常专业,
但他的身体始终是业余的,
不断在尝试和摸索。
他不曾学会,总是陷入迷惑,
沉醉与迷失在悲喜里。
人将在秋日死去,犹如一颗无花果,
萎缩,甘甜,充满自身。
树叶在地面干枯,
光秃秃的枝干直指某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万物才各有其时。
凌丽君 杨志 译
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不太怜悯课桌前的孩子。
对大人,他毫无怜悯。
让他们自生自灭。
某个时候,他们不得不四肢着地
在燃烧的沙地上
爬向急救站
全身流血。
或许他会怜悯那些真心去爱的人
庇护他们
就像树给睡在公园长椅上的人
遮荫一样。
或许我们也应该送给他们
我们最珍贵的、充满慈爱的硬币
那母亲遗留给我们的硬币,
这样他们的幸福就会保佑我们
在此刻,在此后的日子里。
凌丽君 杨志 译
忘记某人
忘记某人就像
忘记关掉后院的灯
而任它整天亮着:
但正是那光
使你记起。
傅浩 译
苹果内部
你到苹果内部拜访我。
我们一起听到刀子
削皮,绕啊、绕着我们,小心谨慎,
以免皮被削断。
你跟我说话。我信赖你的声音
因为里面有锐疼的肿块
像蜂蜜一般
在蜂巢内凝成蜡块。
我以手指触摸你的唇:
那也是一个预言的姿态。
你双唇红润,烧荒的田地般
成了黑色。
它们全都真实不虚。
你到苹果内部拜访我。
在苹果内部,你和我一直待到
刀子完成它的工作。
刘国鹏 译
今天,我的儿子
今天,我儿子在伦敦
一家咖啡馆里卖玫瑰花儿。
他走进前来,
我和快活的朋友们正坐在桌前。
他的头发灰白。他比我年迈。
但他是我的儿子。
他说也许
我认识他。
他曾是我的父亲。
我的心在他的胸中碎裂。
傅浩 译
爱与痛苦之歌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像一把有用的剪刀
分手后我们重又
变成两把利刃
插入世界的肉里
各在各的位置
傅浩 译
一颗行星一旦嫁给了一颗恒星
一颗行星一旦嫁给了一颗恒星,
在内部,有声音谈论未来的战争。
我只知道从前在课堂上学到的概念:
两点之间只能经过一条直线。
对于许多痛苦你轻声地啜泣已足够,
就像火车头能把长串的车厢拖走。
何时我们才能走入镜子里面?
两点之间只能经过一条直线。
有时“我”站得远远,有时它与“你”
押韵,有时“我们”是单数,有时
是复数,有时我不知道是什么。老天,
两点之间只能经过一条直线。
我们欢乐的生活变成了流泪的生活,
我们永恒的生活变成了计岁的生活。
我们黄金般的生活变成了黄铜一般。
两点之间只能经过一条直线。
傅浩 译
情歌
人人使用别人
来治疗他们的伤痛。每个人都把对方
放在自己生存的伤口上,
放在眼睛、 *** 、 *** 、嘴巴和张开的手上。
他们彼此攫紧,不许对方离去。
杨志 译
同样的刺绣,同样的花样
我看见一个男人戴着一顶小圆帽,绣着
很久以前
我爱过的一个女人的
*** 的花样。
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看他,
他走过去以后我为什么回头,
他耸耸肩,走掉了。
我咕咕哝哝自言自语:同样的
颜色,同样的刺绣,同样的花样,
同样的刺绣,同样的花样。
傅浩 译
战场上的雨
雨落在我的友人的脸上,
在我活着的友人的脸上,
那些用毯子遮头的人。
雨也落在我死去的友人的脸上,
那些身上不遮一物的人。
董继平 译
宁静的欢乐
站在一处恋爱过的地方。
下着雨。这雨就是我的故乡。
我怀念着那片遥远的风景
渴望握住它。
我记得你曾挥动着手
似乎在拭去窗上的薄雾。
记得你的脸,
模糊不清,仿佛一幅放大的旧照片。
曾经,我对别人和自己
犯下了巨大的错误。
但是,这世界被创造得如此美丽
乃是为了好好休憩,就像公园里的一条长椅。
太晚了,
此刻我才发现一种宁静的快乐
就像一场沉重的疾病,发现时已经太迟:
如今只剩下一点时间,享受这宁静的快乐。
傅浩 译
纽约大学
在大学门对面宽阔的人行道上,
一位老妇人坐在轮椅上
她是遵医嘱坐在这里的
好让年轻的人流每一天
都漫过她,就像做水疗一样。
傅浩 译
统计学
每一个陷入狂怒的人,总是有
两三个拍拍肩膀使他安静下来的人,
每一个哭泣者,总是有更多替他擦去眼泪的人,
每一个幸福的人,总是有满含悲伤的人
在其幸福时刻试图温暖他们自己。
每天夜里至少有一个人
找不到回家的路
或许他的家已搬到别的住处
他沿街奔波
成为一个多余的人。
一次我和我的小儿子在车站等车
一辆空巴士驶过,儿子说:
“看,巴士里挤满了空荡荡的人。”
刘国鹏 译
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
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我在想
人们是怎样精确地在医院里向大夫描述他们的疼痛。
即便那些还没有学会读写的人也懂得精确:
这种是一跳一跳的痛,这种是
扭伤的痛,这种是咬痛,这种是灼痛还有
这种是刀割似的痛而这个
是一种隐痛。在这儿。精确地说就在这儿,对,对。
欢乐却把一切弄得模糊。我曾听人说过
在爱情和狂欢的夜晚之后:真是太棒了,
我都飞上七重云霄了。但即便是太空人漂浮
在外层空间,拴在飞船上,他却只能说,真棒,
真奇妙,我无法形容。
欢乐的模糊性和疼痛的精确性——
我要用那种剧痛的精确性来描述
幸福以及模糊的欢乐。我学会在各种疼痛中说话。
罗池 译
歌
当一个男人被爱
所遗弃,一个空洞的圆形空间
在他体内慢慢扩展,就像
一个山洞,生长着奇异的石笋。
就像历史中的一个空洞的
空间,打开着,
面向意义、目的和泪水。
胡桑 译
最后的词语是船长
在我停止生长之后,
我的大脑就没有再长,而记忆
就在身体里搁浅了
我不得不设想它们现在在我的腹部、
我的大腿和小腿上。一部活动档案、
有序的无序,一个压沉超载船只的
货舱。
有时我向往躺在一条公园的长椅上:
那会改变我现在的状况
从丢失的内部到
丢失的外部。
词语已开始离弃我
就像老鼠离弃一艘沉船。
最后的词语是船长。
刘国鹏 译
好时机
与新欢幽会的好
时机同样是
安放炸弹的好时机。
在季节与季节的
结合部,
在蓝色的心不在焉中
卫兵换岗的一丝混乱
在接缝处。
傅浩 译
真遗憾,我们曾是那么好的一种发明
他们把你的大腿
从我的臀部切除。
对我而言
他们都是外科医生。他们所有人。
他们把我们
从彼此身上拆开。
对我而言
他们都是工程师。他们所有人。
真遗憾。我们曾是那么好的,
并且爱着的,一种发明。
一个男人和他妻子组成的飞机,
翅膀和其他一切。
我们曾稍稍离开地面。
我们甚至还飞了一会儿。
卢墨 译
秋日将至及对父母的思念
不久秋天就要来临。最后的果实业已成熟
人们走在往日不曾走过的路上。
老房子开始宽恕那些住在里面的人。
树木随年龄而变得黯淡,人却日渐白了头
不久雨水就要降临。铁锈的气息会焕发出新意
使内心变得愉悦
像春天花朵绽然的香味。
在北国他们提到,大部分叶子
仍在树上。但这里我们却说
大部分的话还窝在心里。
我们季节的衰落使别的事物也凋零了。
不久秋天就要来临。时间到了
思念父母的时间。
我思念他们就像思念那些儿时的简单玩具,
原地兜着小圈子,
轻声嗡嘤,举腿
挥臂,晃动脑袋
慢慢地从一边到另一边,以持续不变的旋律,
发条在它们的肚子里而机关却在背上
而后陡然一个停顿并
在最后的位置上保持永恒。
这就是我思念父母的方式
也是我思念
他们话语的方式。
刘国鹏 译
爱之歌
它是这样开始的:猛然间它
在里面变得松弛、轻盈和愉快,
正如你感到你的鞋带有点松了
你就会弯下腰去。
而后别的日子来了。
如今我倒像一匹特洛伊木马
里面藏满可怕的爱人。
每天夜里他们都会杀将出来疯狂不已
等到黎明他们又回到
我漆黑的腹内。
刘国鹏 译
仿佛在出席葬礼
我作完的事排队向前走去
仿佛在出席葬礼:多年前还是孩子的我,
初恋的我,当兵的我,
一小时前头发花白的我,
以及那些我曾是或我忘记的,其他的我,陌生人,
也许包括一个女人。
所有人的嘴唇都在歙动、追忆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闪亮、流泪
所有人都在哀悼与宽慰
所有人都将重返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时间,
仿佛在出席葬礼。
其中一个对他的朋友说:“现代社会的
主要任务就是
创造更强大而又更渺小的物质。”
他说完哭了,然后继续他的路,
仿佛在出席葬礼。
杨志 译
从前一场伟大的爱
从前一场伟大的爱把我的生命切成两段。
前一段在某个别的地方
继续扭动,就像一条被砍成两段的蛇。
岁月的流逝使我平静下来,
给我的心带来痊愈,给我的眼带来休憩。
我就像有人站在
犹地阿沙漠里,看着一块标志牌:
“海平面。”
他看不见海,但他知道。
就像这样,我处处记起你的脸
在你的“脸平面”之前。
傅浩 译
在我们正确的地方
在我们正确的地方
花朵永远不会
在春天生长。
我们正确的地方
被踩踏得坚实
像运动场。
但是怀疑和爱
挖掘这世界,
像鼹鼠,犁铧。
在毁圮的房屋曾经站立的
地方将会听到
一声低语。
傅浩 译
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诗人之一。生于德国的乌尔兹堡,十二岁时随家迁居以色列,二战期间在盟军犹太军队中服役,目击了以色列独立战争和西奈战役,战后他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师,先后出版了《诗:1948-1962》《现在风暴之中,诗:1963-1968》《时间》等十余部诗集。诗作被译成数十种文字。
阿米亥曾获得众多的国内、国际文学奖项。1982年,因为“在诗歌语言上的革命性变化”,阿米亥获得了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奖”。在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当年的获奖者之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朗读了阿米亥的诗作《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阿米亥的诗透明、睿智、幽默,富有人性的思想和力量,善于使用圣经和犹太历史作为诗歌意象,把日常与神圣、爱情与战争、个人与民族等因素糅合起来,因此他的诗多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普遍命运,想象力极其丰富,具有深远的哲学意味和语言渗透力。
本专题通过比较多种不同的翻译版本,选出阿米亥脍炙人口的经典诗作,同时也是翻译佳作的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