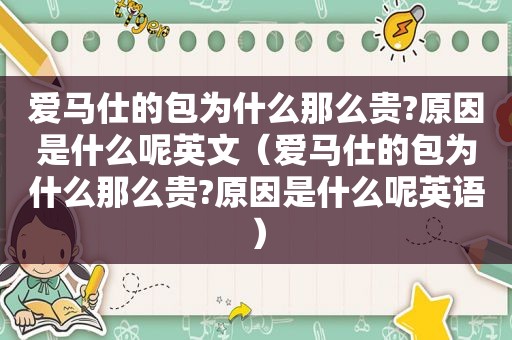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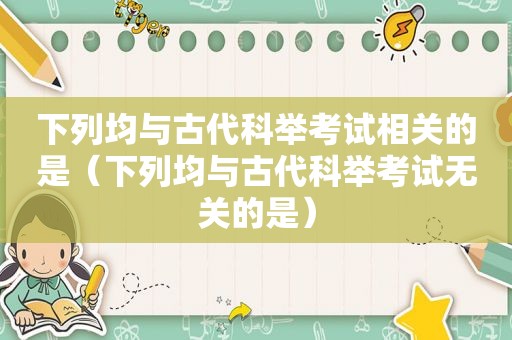
700年科举官方正统标准答案——朱熹理学
朱熹:天生一个孔子命
文\刘立夫(中南大学教授)
2021/05/13 08:23
朱熹被认为是儒家里面仅次于孔子的人物。中国儒家的代表,前1000多年是孔子,后700多年是朱熹。先秦儒家以孔孟为正宗,宋代儒家以程朱为正宗,程朱加陆王,构成宋明理学的四大家。
儒家的人物那么多,论资排辈就很讲究。朱熹到底排在什么位置呢?他被排在“孔门十二哲”中的第11位。这个排位与清朝的康熙皇帝有关。
传说康熙皇帝私下里改名换姓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中了个探花,第二名,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就有这个情节。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康熙皇帝对儒学很推崇倒是真的。他在看过《朱子大全》以后,下诏将朱熹列入孔庙的“四配”之后。大家知道,孔庙里面的四配,是孔子学问最重要的四个继承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也就是孔门“四圣”,都带一个“圣”字头衔。再往后,还有十个很重要的人,称为“十哲”,子路、子贡、子夏,等等,都是当年孔子的嫡系弟子。如果按照康熙皇帝的意见,朱熹列在四配之后,那孔子的十大弟子就不好摆了。大臣李光地建议说:“朱熹尽管造诣极深,足以比肩四配,但时间相隔一千多年了,一旦把他放在孔庙的四配之后,恐怕朱熹也心有不安。”于是,康熙皇帝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将朱熹置于十哲之后,凑成了十一哲。但十一是单数,不好摆,后来乾隆皇帝干脆增补一个孔子的学生有若,变成“孔门十二哲”。朱熹算是孔门十二哲里面惟一非孔子嫡传的儒者。
我们现在给朱熹的定位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要理解他的思想,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我今天重点谈谈他的身世、阅历和主要贡献。
一、“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
古人云:“穷学文,富学武。”意思是说读书的成本相对较低。现代人也相信:“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但是,出身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的人,肯定比白手起家的读书人起点要高。
前面讲到的几个宋代理学家,都有较好的家庭背景,朱熹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叫做朱松,做过建州政和县的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晚年还做过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朱松曾经请人算命,算命先生对他说:
“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
朱熹出生在福建,祖籍江西婺源,今天的上饶。他生下来右眼睛边上长了7颗痣,如北斗七星,与众不同。不管怎么说,朱熹后来的影响力,确实对孔子的儒学有再造之功。
朱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他的几个好朋友照看。他们很给力,其中,刘子羽给朱熹建了一栋小别墅,刘勉之则把女儿嫁给他。一个给他起房子,一个给他找老婆,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啊。还有,这几个人虽然都是儒者身份,却对佛教情有独钟。朱熹从小接触佛教,就与他们有关,他早年认识一个叫道谦的和尚,是宋朝著名僧人大慧宗杲的徒弟。据说,朱熹当年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时,他的行李箱里空空如也,只放了一本禅宗和尚的语录,叫《大慧语录》。朱熹后来回忆说,因为禅宗的和尚说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话不说死,两头都照顾,他就学着和尚的口气,竟然得了高分。
朱熹19岁就考上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叫“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地方的州试,第二级是朝廷的省试,第三级是皇帝的殿试。殿试本来也有通不过的,但宋朝有个特殊情况。当年宋太宗在殿试的时候,以貌取人,把两个长相不好的人给淘汰了,结果那两个人投敌叛国,去了西夏国,给西夏出谋划策,北宋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宋朝以后便吸取教训,殿试环节就不淘汰了,但排名有高低。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朱熹就属于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虽然名次靠后,但19岁考上进士,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宋朝319年,总共才录取了二万多进士,一次就录取几十个,最多不超过几百人。有人调侃说,殿试相当于985,省试相当于211,州试相当于普通本科,其实,这没有可比性,过去是精英教育,与今天的全民普及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二、拜李侗为师
大家看到“程朱理学”这个名词,就会想到朱熹与二程有关。确实是这样,朱熹是二程的学术传人。问题是,朱熹生活在南宋,二程生活在北宋,相隔一百来年,怎么接得上呢?
其实,朱熹一开始学得很杂。千万不要以为朱熹从小立志做圣贤,就只会天天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真正要做圣贤哪有那么简单。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这就叫“泛滥百家,出入佛老”,宋明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这个经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太小,你就是想做圣贤也没有资格啊。我们现在分科太早,文科、理科、工科在高中阶段就想定下来,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行切割,那绝对是做学问、搞科研的大忌,格局太小,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才。
朱熹大约在24岁的时候,学问才有一个根本的转向。因为这一年,他拜见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李侗。李侗是谁?杨时的第二代弟子。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人。列成一个道统传承就是这样:
“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
这样算来,朱熹成了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有意思的是,先秦的孟子也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合称“孔孟”。朱熹与二程也是隔4代,合称“程朱”。有点巧合。
你可能会纳闷:朱熹原来就有私塾老师,加上前面提到的三位刘先生,都有学问,凭什么要拜李侗为师?主要原因是朱熹前面学得太杂,没有主心骨。特别是他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太深,前面那三位刘先生就经常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儒佛道三教不分家。朱熹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大问题。他年轻时候研究过道教的神仙术,有诗为证:
“不学飞仙术,日日成丑老。空瞻王子乔,吹笙碧天杪。”
意思是,不学神仙之术,会很快变老变丑。只能羡慕王子乔那样的仙人在蓝天白云间飞过,吹着芦笙飘向远方。他也写学佛的诗: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
大意是说,闲来无事翻翻佛经,暂时远离尘世的烦恼。在空山新雨后的竹林深处,大自然的幽静更能让人体会佛教“无为法”的奇妙,身心安详而宁静。
从这些游仙诗、禅趣诗可以看出,朱熹年轻时候对佛老二教还是很向往的。这跟他后来强烈批评佛老形成鲜明对照。
朱熹24岁时,做泉州同安县的主薄,心中的疑虑增多,于是“徒步数百里”,没有坐车,走了几百里路,专程来到李侗的住所,向他请教。朱熹回忆说,他在李侗面前说个不停,学富五车的样子,还说自己学过佛教。但李先生只回应道:你说那么多悬空的道理看起来高大上,一旦用到实处,就会自见分晓。大家一定要明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名师关键时候几句话点拨你,胜读十年书。
李侗提醒朱熹的,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真理。这非常重要。李侗明确告诉朱熹儒佛道三教的区别,朱熹经过反复思考,大约在28岁的时候,最终和佛老决裂,回归到儒学,成为与二程一样的儒家道统人物。朱熹有句名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对孔子的推崇类似于西方人对待上帝。我们不妨也来看他的一首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选入了中学课文。如果不了解朱熹的思想转变,一般人只能根据文字,理解成这样:在春天的一个良辰吉日,我来到泗水之滨,只觉得无边的美景是那么清新亮丽。谁都知道这是可爱的春风,才让大地变得万紫千红。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朱熹生活在南宋,泗水是孔子的家乡,远在北方的山东,那是敌占区,跑到泗水河边去春游,那不是找死吗?所以,这首诗的“泗水寻芳”只能是象征,象征儒学的春风吹遍了朱熹的世界,他在儒学的熏陶下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感到一切都是春光融融。当然,这只是文学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却很残酷。
三、一个有道学性格的政治人物
朱熹19岁考上进士,就有了从政的资格。他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秘书长;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军有三个县,相当于知州,这个职务周敦颐也做过。还做过漳州知府、潭州知府。潭州在湖南长沙。《宋史》朱熹传用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从政阅历: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仕”就是做官,“九考”就是九次考核。古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三年一考核,那相当于他做了27年的地方官。其余时间都是做有职无权的闲职。“立朝才四十日”,是说他在朝廷任职约40天。
南宋时代的政局很复杂,那个时代的官员要想有一番作为非常困难。朱熹为官多年,为民办事,政绩当然有,但让他名留青史的还是他的讲原则、重气节,“六劾贪官唐仲友”就是一段佳话。
宋孝宗醇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朱熹52岁,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之职。盐茶是两浙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常平盐茶公事算是一个肥差。他的这个职务本来是当朝宰相王淮推荐的,而唐仲友的亲家却王淮。这一年,朱熹到台州视察灾情。没想到,一连接到各种反映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的举报。面对正义和私情,朱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了正义,决定对唐仲友的丑闻进行调查,并总结成8条违纪行为上报中央。一开始唐仲友仗着宰相王淮的撑腰,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被提拔为江西提刑,相当于江西省司法厅长。但是,朱熹一身正气,誓不罢休,前后六次向朝廷递交弹劾报告,惊动了宋孝宗。宰相王淮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皇帝奏请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之职,让他提前退休,安全着陆。朱熹当然很气愤,毅然辞职,回到了福建武夷山。
朱熹65岁的时候,还给宋宁宗皇帝当过老师,当时叫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让我们想起北宋的程颐给小皇帝当老师的情形。程颐担任那个崇政殿说书才1年多,而朱熹做这个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不过40多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理学家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本来,做帝师是人生莫大的荣光,但理学家想的是如何“格君心之非”。皇帝有错误,也要帮他纠正。朱熹奉诏入都,当时就有人提醒他,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了皇帝切忌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
“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不顾皇帝的面子,用他那套“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标准,给皇帝上政治课。批评皇帝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想而知,宋宁宗哪里受得了一位道学家如此铁面无私的训导。他的这个帝师自然是做不成了。朱熹这种道学性格为他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过了两年,韩侂(tuo)胄做宰相,权倾朝野。朱熹看不下去,上疏直言,惹怒了韩宰相。这一次终于引发“庆元党禁”。要知道宋宁宗就是韩侂胄等人扶上台的,皇帝也要听他的。朱熹遭到清算,他的学问作为“伪学”被查禁,他的许多弟子遭到流放或坐牢。还有人趁机给朱熹挖出十条罪状,称他“不忠于国”、“不敬于君”,还说他“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等。后来有人根据后面这两条罪状,演绎朱熹把两位尼姑收为小妾的绯闻,还编造他与自己的儿媳妇 *** 的情节,搞道德绑架。世界上喜欢听绯闻的大有人在,像朱熹“外传”、“别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只是后人的附会,谁也没法考证。
四、“四书”因朱熹而升格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文化人,文化人往往是 *** 官员,像庄子那样完全拒绝做官的道家人物实属例外。学问好而从政,那是“学而优则仕”,现在称为“学者型领导”;从政之余做学问,那是“仕而优则学”,现在称为“领导型学者”。像朱熹那样的人,二者兼而有之,但他一生最大的兴趣还是做学问。他为后人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著述,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朱熹的文集称为《朱文公文集》,一般人不会去翻,但有一本著作不得不提,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是朱熹最重要的著作,耗费的精力最多,他晚年虽然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而且一只眼睛瞎了,还在写这本书,据说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琢磨《大学》的章句。“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合称。它为什么很重要?这与儒家的“道统”有关。前面提到,唐朝的韩愈第一个提出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他认为《大学》的“修齐治平”就是对抗佛教的有力武器。李翱抬出《中庸》,认为《中庸》的心性境界足以抗衡佛老。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普遍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当然,《周易》也很受重视。经过朱熹的注释,四书的地位超过了汉唐时代的“五经”。
我们现在很多人想看四书,但不知道先看哪本。朱熹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先读《大学》,奠定人生格局,好比建房子先定个框架。接下来读《论语》,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然后读《孟子》,可以激发人的“浩然之气”。最后读《中庸》,它是孔门传授的“心法”,精深而微妙。当然,这是朱熹的意见。我们今天也可以先读《论语》和《孟子》的部分章节,因为它们比较平易近人,容易理解,《大学》、《中庸》抽象一些,不妨放在后面。
朱熹去世后,他的冤案得以 *** 昭雪。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为法定的教科书。元仁宗于1313年诏令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教材,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就是说,朱熹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四书集注》统治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约700年的时间。
五、朱熹哲学三题
朱熹是理学的一个集大成者。我们今天总觉得他的思想很难懂,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人的两种心理障碍。认为朱熹说的都是对的,其实他也有说错的地方。第二,朱熹用的一些概念太模糊、晦涩,我们今天应该用现代语言转换过来。朱熹的哲学思想丰富,我给大家讲三点比较重要的。
1、“理先气后”
理是什么?我们现在说“天理不容”、“岂有此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理,主要是生活中要遵守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伦理。虽然理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但理学家的重点是伦理,而非物理。“气”是什么?气就是物质,引申为万事万物。
我们前面说过,张载重气,二程重理,朱熹吸收了两家的思想,但他倾向二程,更看重理,认为理在气先,或理在事先。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为什么说理在气先?按照朱熹的意思,一个事物不存在了,它的理还在,原则、规则还在。比如你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一开始感情好得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熄火了,你认为爱情的“理”还在吗?朱熹会说,爱情之理还在,因为“情理”与你们之间是否恋爱无关。又比如某个人的父母去世了,他不能像父母生前那样去尽孝,但“孝道”还在,你不孝,别人会孝。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中国造了一款先进的五代战机歼20,按照朱熹的说法,中国即使造不出歼20,这款飞机的原理还在。
那么,朱熹到底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你要是跟一个女孩分手了,绝对不会承认爱情之理还在,因为爱情已是过去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朱熹说“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认为即使天地都坏了,人世间的伦理道德的原则还在。实际上是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跟人类具体的生活实践割裂了。但是,自然界中的物理定律就不一样,你造不出歼20,并不意味着自然界不存在“飞行原理”,关键你能否发现这个飞行原理并用这个原理来造出各种飞机。所以说,朱熹的理在气先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有点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唯心主义”去否定它的某些合理性。
2、“存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在二程那里就提出来了,但朱熹说得更明白,过去认为这是提倡宗教禁欲主义,遭到非议。朱熹的原话是: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如果单独从字面上看,谁都感到有点毛骨悚然,觉得这不是人说的话。因为只要是人,都会有欲望,要是把欲望都浇灭了,那人活着还有啥意思?看来“灭人欲”这个灭字用得太绝对了。但是,如果你结合儒家文化的背景去理解,就不会误解朱熹。
什么叫“天理”?什么叫“人欲”?《礼记·乐记》上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意思说,一个人在外部环境的诱惑下,如果不能自我节制,就会丧失本来的道德良知,穷奢极欲。这本是人之常情。过去说“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两朝”,人在富贵的环境中最容易忘乎所以,骄纵横蛮。孔子的学生子贡做生意赚了钱,他问孔子:“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傲,如何?”孔子回答说:“当然不错。但不如贫穷而快乐,富贵而以礼待人。”孔子说这样的话,确实很高明。
《尚书》里面记载上古时候的圣人舜曾经告诫禹,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坚守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十六个字放在今天还是座右铭,很多书法家喜欢把它送给有身份的人,以示策励。
现在再来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道心,人欲就是人心,更确切一点,天理就是人类崇高的道德原则,人欲就是失去控制的私心杂念。古今中外,节制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人性的光辉所在,任何一位道德学家都不会鼓励人去满足私欲。为什么?欲壑难填。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正常的穿衣吃饭是天理,老想着山珍海味就是人欲。找老婆是天理,嫌三妻四妾还不够是人欲。这是朱熹的原话。
有人说,中国人口味重,除了凳子以外,四只脚的都吃;除了飞机以外,两条翅膀的都吃。这叫“暴殄天物”。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据说就是人类吃蝙蝠的报应。其实,蝙蝠已经长得不像个食材,可是某些人还是要满足口腹之欲,这就是典型的灭天理,穷人欲。
3、“半日 *** ,半日读书”
朱熹曾经提倡“半日 *** ,半日读书”,这个读书方法后来被人讽刺为:
“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
批评他的这个人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他有感于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认为自宋朝以来,由于受到朱熹的影响,儒家培养的都是文弱书生:“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还说,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像妇女一样,缺少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娘炮”。我们今天看的有关明朝的一些电视剧,里面都是些“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组织,一个个凶巴巴的样子,跟颜元说的情况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到底电视剧真实,还是颜元说的真实,这里就不讨论了。不过,颜元说朱熹提倡“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确实揭示了它与佛教的关系。
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佛教和尚会打坐,朱熹也提倡打坐,难道这两种打坐是一样的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其实,打坐与 *** 是一个意思,来源于佛教的禅定,英文叫meditation。朱熹早年热衷于佛教,他认识大慧宗杲的徒弟道谦禅师,还写过关于坐禅的诗,后来他拜李侗为师,回归儒家。此后就把佛教骂得一无是处,刻意将他的“ *** ”与佛教的“禅定”区别开来。
“ *** 并非要人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
朱熹说,儒家的 *** ,也就是把心收敛,以便专心读书或做事,与佛教的老僧入定绝然不同。不过,我这里要告诉大家,朱熹说坐禅入定是“断绝思虑”,这是不对的。你要是去庙里体验一下,或者问问一位法师,打坐是“断绝思虑”吗?回答肯定不是。佛教有各种禅定的方法,基本要求就是“静虑”,目的是消除烦恼,朱熹学过禅,应该明白,要么就是他故意说错。比如,他曾举了一个“主人翁惺惺着”例子:
有一个禅师,天天都唠叨同一句话:“主人翁惺惺着。”意思是,心灵的主人啊,你务必要清醒,千万别犯糊涂啊。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看住自己的主人翁,什么事都不管。有一天,这个和尚的父亲被他人欺负了,有人告诉他这个坏消息,让他赶紧想办法去救。可是,这个和尚无动于衷,一心念着他的“主人翁惺惺着”。
朱熹讲完这个故事,然后告诉他的学生,佛教的坐禅入定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管”,放弃了人世间的一切道德责任。但是,儒家就不同,必须时刻关注道义的要求,承担社会责任。
从朱熹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半日 *** ,半日读书”,跟颜元批评的“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还是不同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禅宗的和尚毕竟是出家人,他们尽管提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但还是不能看到“事君事父,无非妙道”。宋明理学就是接过禅宗说的,把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统一起来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朱熹还没有完全做到把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一起来,因为他把佛教骂得一无是处,坚持要与佛教彻底决裂。本来, *** 就是用来放松心灵的,佛教的禅定是一种很典型的心灵放松技术,是值得儒家学习的。但朱熹不敢承认他的 *** 方法与佛教有关,刻意撇开,他的言论显得有点矫情。
顺便提一个细节。朱熹晚年身体不好,还研究道教的《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写了一部《周易参同契考异》,因为害怕别人笑话他,就用了一个化名,叫做“空同道人邹䜣”。实际上,道教的某些法术也是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对于养生长寿是有帮助的,但朱熹私下里做了,却又不敢公开。这也说明像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一方面在“道统”上有纠结,另一方面心胸确实还不够开阔。不过,这并不影响朱熹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也说明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高不可攀、只能仰望的圣人。
好了。朱熹就说这些。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他们两个人思想差距很大,曾经有过轰动一时的江西“鹅湖之辩”。我们下次就讲陆九渊。
(责任编辑:邴丽娜 PFO023)
^v^v^v^v^v^v^v^v^v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四章》
-------------------------------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1033~1108)开创的学派,由朱熹(1130~1200)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1032~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年)继续,王守仁(1473~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匆忘,匆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颢、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戟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区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同上)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同上)。它“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颖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宇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俟。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v^v^v^v^v^v^v^v^v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五章》
------------------------------
新儒家:理学*
程颐死后只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00年)就生于今福建省。这二十年中,政局变化是严重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一1279)。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仍然如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 *** ,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在第二十三章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写了几部经典的“新义”,宋神宗于1075年以命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 *** ,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作了《周易本义》、《诗集传》。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 *** 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作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理
前一章已经考察了程颐关于“理”的学说。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同上)又有一段说:“问:枯稿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同上)笔之理即此笔之性。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于这个原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朱熹在《答刘叔文》的信中写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因此,所谓发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质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语类》卷一)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极”字本义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新儒家用“极”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极”。如朱熹所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
他又说:“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周敦颐——引者注)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语类》卷九十四)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善”的理念,亚力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
可是。朱熹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相拉图的“善”的理念,比亚力士多德的“上帝”,更为神秘。这一点就是,照朱熹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
但是,如果万物各有一太极;那不是太极分裂了吗?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要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解释一与多的关系,就发生困难。朱熹也有这个困难,他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这个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于事物的某个种类之理,与这个种类内各个事物,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假使提出来了,我想朱熹还是会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
气
如果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
他又说:“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语类》卷一)我们在这里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原故。
关于理相对地先于气的问题,是朱熹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有一次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语类》卷九十五)一个理,先于它的实例,朱熹这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于一般的气呢?朱熹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语类》卷一)
另一个地方有这样一段:“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朱熹心中要说的,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同上)没有元气的时候。由于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说成是有始的,就是谬误的。因此,若问先有理,还是先有气,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意义。然而,说气有始,不过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始,则是逻辑的谬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气之间有先有后,并不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问题是:理与气之中,哪一个是柏拉图与亚力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动者,因为“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但是理虽不动,在它的“净洁空阔的世界”中,却有动之理,静之理。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但是气一“禀受”了动之理,它便动;气一“禀受”了静之理,它便静。气之动者谓之阳,气之静者谓之阴。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中国的宇宙发生论所讲的宇宙两种根本成分,就产生出来了。他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语类》卷九十四)这样,太极就像亚力士多德哲学中的上帝,是不动的,却同时是一切的推动者。
阴阳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产生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宇宙。朱熹在他的宇宙发生论学说中,极为赞同周敦颐、邵雍的学说。
心、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朱熹赞同程颐的“性即理也”的说法,并屡作解释。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是个人禀受的理。这样,就可以解释程颐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 程颐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理。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语类》卷四)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禀受于理者,还有禀受于气者,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质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想。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圆。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个人气禀中发现的实际禀受之性。一经发现,如柏拉图所说,它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可是,固有的普遍形式的理,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以资区别。张载早已作出这种区别,程颐、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问题。
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朱子语录有云:“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语类》)卷五)又云:“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成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
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什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的,便是性。”(《语类》卷四)
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孟子主张,在人性中有四种不变的德性,它们表现为“四端”。上面引的朱熹这段话,给予孟子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照朱熹的说法,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的活动。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我们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陆王学派主张心即性。这是程朱与陆王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政治哲学
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定而繁荣;它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陷人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友人陈亮(1143~1194)有过激烈的争论。陈亮持不同的观点。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答陈同甫书》,《文集》卷三十六)还写道:“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同上)
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以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就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朱熹写道:“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同上)
为了说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举建筑房屋为例子。建一栋房子,必然依照建筑原理。这些原理永恒地存在,即使物质世界中实际上一栋房子也没有建过,它们也存在。大建筑师就是精通这些原理,并使他的设计符合这些原理的人。比方说,他建的房子必须坚固,耐久。可是,不光是大建筑师,凡是想建筑房子的人,都一定依照同一个原理,如果他们的房子到底建成了的话。当然,这些非职业的建筑师依照这些原理时,可能只是出于直觉或实践经验,并不了解它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其结果,就是他们所建的房子并不完全符合建筑原理,所以不可能是最好的房子。圣王的治国,与所谓英雄的治国,也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讲过,孟子认为有两种治道;王,霸。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是王霸之辩的继续。朱熹和其他新儒家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因为它们的统治者,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因此,这里又是朱熹继承孟子、但是像前面一样,朱熹给予孟子的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政治的。
精神修养的方法
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有这种柏拉图式的思想,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相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将要做王的哲学家应受的教育。朱熹在上面所引的《答陈同甫书》中,也说“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但是做这种功夫的方法是什么?朱熹早已告诉我们,人人,其实是物物,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太极就是万物之理的全体,所以这些理也就在我们内部,只是由于我们的气禀所累,这些理未能明白地显示出来。太极在我们内部,就像珍珠在浊水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使珍珠重现光彩。做的方法,朱熹的和程颐的一样,分两方面:一是“致知”,一是“用敬”。
这个方法的基础在《大学》一书中,新儒家以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第十六章中讲过,《大学》所讲的修养方法,开始于“致知”和“格物”。照程朱的看法,“格物”的目的。是“致”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
为什么这个方法不从“穷理”开始,而从“格物”开始?朱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书》卷四十六)换言之,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我们本性中的理。理,我们知道的越多,则为气禀所蔽的性,我们也就看得越清楚。
朱熹还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
这本身似乎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辅之以“用敬”呢?回答是:若不用敬,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一智能练习,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在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是为了擦净珍珠,重放光彩。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一朝大悟。这就是用敬的功用。
朱熹的修养方法,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他的人性中有万物之理的学说,很像柏拉图的宿慧说,照相拉图所说,“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关于一切本质的知识”(《裴德若》篇)。因为有这种宿慧,所以“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各个美的事物”的人,能够“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的本质”(《会饮》篇)这也是顿悟的一种形式。
注:* 英文本作 The school of Platonic ideas(“柏拉图式理念”学派)。—译者注
(5、宋明理学——复古思想,秦汉与隋唐思想的重演
(1)分裂。韩愈复古运动的继续。“洛\阳\反\革\命\集\团”:司马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苏轼、欧阳修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心怀不满的知识集团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墨家与孔家的冲突,是儒家内部的冲突。争论导致了返回正统和主流的极端主义,向玄学求助,“内转”为理学,就是必然结果。
(2)合禅为理。寻根,“万理归于一理”,理为中国人的终极关切。“终极关切”赋予了知识分子真理上的优越感,这是一种“文化禅教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不过理学内部有冲突,可从中“朱陆之辩”(鹅湖之会,理学与心学)看12世纪中国精神的某种不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朱熹的新儒学重建“道统”(四书五经),并使儒学理想进入政\治\中\心和百姓生活:宗族主义。理学的失败:伦理生活的混乱,迷信横行。
(3)明代理学。元朝完成了宋儒的制度化建构,宋代理学和蒙古政权相结合(许衡)。这是一场理学世俗化运动,精神直逼秦汉王道之学。儒学为君\主\专\制\主\义辩护,在明代同样受到重视,并更加强调其实用性。在这种背景下,陆学复兴是可想而知的。王学(王阳明)就在陆学的未尽事业中站起来的,但更多得益于程朱思想的“欲理”(人心与道心)之辩。王学首先是对“官学”的 *** ,然后是朱学的修正,“心即理也”。外在规则就这样被消解了。从神学的角度说,人无法靠行为成义,这是儒学的千年难题,不断将“义”主观化,则是中国心灵不断的自我解放或自我解嘲。这无疑又是一场禅宗的补救行动。与此同时,朱熹的“格物致知”(知识就是良心)的“成圣”之路,被替换为“致良知”、“求之于心”。王阳明的“死穴”在于孟子的性善论,“良知无不在”实为谎言。《中国思想极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