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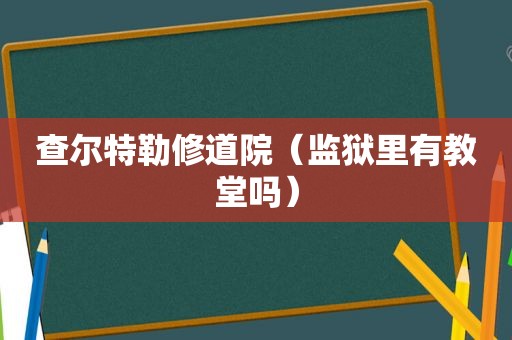
原创: Zoom Vith
“充斥着李帕蒂式的自我压抑的布列松电影里,艺术家所共通的那些被镇压在黑白键盘上、涂抹在声画机关里的极简色彩反复延宕着。而在属于艺术本身的刺破时刻,那些情绪都如灵魂决堤一般破茧而出,凭空缔造出了坚硬的人格上的悲欢。”
描述性的文字是无法外化我对布列松电影的全部观感的。
在认识到这一让人沮丧的事实之后,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在文首表述的那一段对布列松艺术内核尝试性的总结曾产生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妙挫败感。
不过对于我与布列松来说,认知的旅途永远在是路上的。于是,在重看了他的《乡村牧师日记》和《圣女贞德的审判》后,布列松在电影中所制造出的巨大宗教困惑,彻底地把我从电影语言的桎梏中拽出了。我被带进了个人真理的另一道门,一道真正让我开始理解布列松的电影内核的大门:
巴赞所无法涵盖的布列松电影的那一部分,能否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达?
从作为布列松登堂入室的电影《乡村牧师日记》起,其最熟悉的面目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而非巴赞式的。
当一个年轻而虔诚的神父的一生被以绝对私人化的视角呈现在面前时,我觉得布列松是从一开始就已然预设好他的悲剧结局了。这是我在无数次地看到牧师吃着沾着酒的面包干强忍病痛写日记时忽然感知到的。因为在那种自我与深层信仰最隐秘的交流时刻,牧师的脸上却永远呈现出一种垂死的谦卑表情,从影片的一开始就是如此。于是,仿佛影片伊始,自我就已然选择了那条最去世俗化的路途,一种舍弃肉体的灵魂酷刑,拷问的正是自我与上帝二者无阻碍的开诚布公。布列松也借此向每一个观众宣布:
这电影是教徒与信仰最诚实的交往纪录,看看你们能在其中找到何种自我,是愚民,还是圣徒。
大部分人很显然都是愚民。
这在我们很明确是严苛的讽刺,可布列松却说:这是最诚实的记录,因为这一切都是人间的常态。
在充满着光与暗的田间,关于信仰最刺目的画卷铺陈展开。年轻的牧师忍痛步道,却被无知的教区愚民以仇恨的眼光对待,狭窄的人心终使虔诚变成滚烫的自我拷问。
电影里,牧师问:“为什么你们要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呢?”
人们回答:“上帝对我们丝毫不公平,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我的儿子被病魔夺去,如果我信仰他,他应该降下神迹。”
这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述的审判官对耶稣的拷问:“你许诺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在永远不学好、永远不感恩的孱弱人种眼里,那种面包怎能和地上的相比?你可知晓,就是为了地上的这点面包,地上的精灵(撒旦)将要起来反抗你,和你斗,打败你,那时所有的人将跟着他跑,并且高喊:‘谁能与这野兽(指撒旦)相比?你从天上给我们取来了火!”
于是卑劣的人们烧毁基督的教堂,在那片废墟上,看似理性的巴比伦塔拔地而起。
布列松的电影完美地包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性。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态在他的每一个电影主角身上清晰可见,丝毫不愤怒,可是却带着善良的绝望。俨然陀思妥耶夫斯基《 *** 》里的梅思金公爵,信仰被践踏的年代,耶稣还没有死,但已失去神力。
尼采说:“最后一个基督徒,已死在十字架上。”
尼采的哀嚎就像《圣女贞德的审判》所带来的直接观感。贞德为了法国被捕,却被法国人卖给了英格兰,在可笑的时代,除了重复了6遍“基督”然后在火中湮灭的贞德,似乎电影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嘲笑信仰而存在的。就像布列松说:“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坏。”于是在电影里,再没有其他正面人物了。
在一个全是反面人物,正面人物逐一死去的电影里,作为观众的我如何获得救赎呢?
“没有救赎。”布列松说,“因为事实就是事实,而电影只是记录和仿拟事实的工具。”
布列松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好像丢失了情绪的灵魂。
横向对比布列松那些并不涉及基督的所有改编电影,这样的绝望一直都在。没有救赎,一概死去。
不论是对《扒手》中最终被捕的米歇尔,还是《金钱》中被假钞毁灭的年轻人,甚至是《穆谢特》中最终滚落山坡的少女穆谢特,布列松都是说到做到。人世间的苦难无处不在,不论是修道院还是监狱。又或者,人世间本身就是修道院和监狱,信仰与人的卑劣本性的拷问每天都在上演,无止无休。
他缄默了,永远地缄默了,在他确定过这世间的每一间修道院与监狱毫无差异之后,直至去世,他都缄默着描绘那些幽暗小路,每一条路都通往绝望。
可布列松的绝望并不是人类的绝望。
布列松的文学思想源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审判官”说:“人类是绵羊,绵羊是无法忍受个性荒漠的极端痛苦的,只有集体化的宗教组织的钳制,才能给予人们存活的可能。”
这在某种程度上才是真正将一种对与错并列召唤进存在本身的自问:
对于每一个愚民而言,个体自由所带来的痛苦荒漠,真的是我们可以承受之物吗?
如若不是,那么我们大肆鼓吹所谓的天上的面包,本身又有何现实性可言?
布列松的宗教崇高性在此刻被清醒地搁置一旁。
现实性的漩涡终于开始吸附虚无的空洞。
看似绝望的布列松式基督崇拜也许对人而言不可或缺,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终究让人对它的现实性认识更加清醒起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凯撒之剑会战胜基督,也终将杀死上帝。
我终于想起马修•阿诺德曾在《文化与无 *** 状态》中告诫过的话:“或许阻挠我们追求圆满性的,正是某种罪。”
这罪让基督的门徒蒙羞,但这罪也让布列松之所以成为布列松,既孤独,又缄默。
今日,布列松的道路也许与我们既不相同也不相关。可终有一日,当人们的原罪如深渊般吞噬存在的初始,当理性面对非存在的虚无撒旦束手无措时。我相信,人们终会记起,曾有一个在烈火中反复呼唤“耶稣”名字的修女叫贞德,曾有一个因绝望而平静教徒,叫布列松。
Vith往期优质文章推荐
END
Vith微信公众平台长期接受征稿,并推出最新系列类征稿,直接进入聊天界面点击菜单栏[写戏]即可获取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