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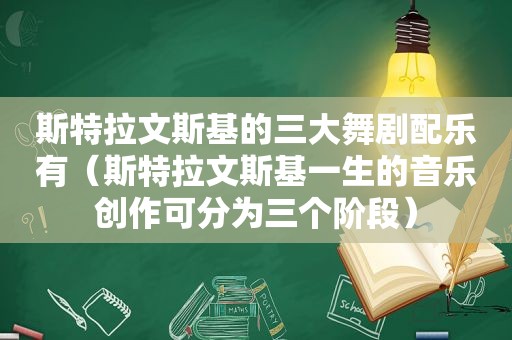
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史上的角色与地位,恰如毕加索之于绘画史,卡夫卡之于文学史,这位现代乐派的旗手与领袖,在20世纪波谲云诡的艰难而复杂的境遇中——先后遭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纳粹的崛起与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经历着整个世界以及整个音乐历史的双重流浪,在巨大的声望所带来的无数镁光灯的暗影处,一个踽踽独行的寂寞身影在颠沛而辉煌的漫长人生中一直找寻着自己的原乡——那个超越了民族和地理意义之上的故乡,最终安身于跨越千年的音乐历史中。
整个世界的流浪者
如果20世纪的未来历史家从该世纪所发生的事件这个长远眼光来决定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和形势时,他们就会发现1913年5月29日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现代音乐领域中,这一天就如14个月后震撼了世界的那场政治、军事危机一样是至关重要的。那天晚上,谢尔盖·佳吉列夫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把一部新的芭蕾舞剧《春之祭》搬上了舞台。舞蹈动作的设计者是尼金斯基,佳吉列夫的著名舞蹈演员成功地表演了这些动作,尼古拉斯·罗里奇为这部作品设计了布景和服装,斯特拉文斯基则为其谱写了乐曲。
出席首场演出的 *** 可能并不像半个世纪以前出席瓦格纳的《汤豪舍》首场演出的那些人一样怀着一种制造骚乱的意图,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做的事恰恰达到了这一效果。他们很快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或是大喊大叫,发出嘘声,或是用力跺地,这一切都因为其中的音乐:这是引起极不和谐的骚乱和充满 *** 的愤怒的音乐。它的忠实信徒竭尽全力鼓动人们的热情,而守旧派则施展出古老的天赋能力:集体退场。对前者来说,《春之祭》就像一部现代版的《英雄交响曲》,他们认为它会猛然打开通向全新的音乐时代的大门;对后者而言,这部作品代表了“对音乐艺术的亵渎与毁灭”。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部作品为31岁的斯特拉文斯基在现代音乐中奠定了稳固的地位,使他在近20年的时间内成为最有影响、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伟大的巴托克称《春之祭》为“俄罗斯乡村音乐的升华”,塔鲁什金则将之称为民族之声与现代之声的“伟大融合”。随后,斯特拉文斯基领导的这场运动横扫了欧洲和美国的各大音乐厅,甚至一度要把浪漫主义本身的最后残迹都一扫而光。如今看来,1913年可以视为斯氏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也正是这一年,他与时尚女王可可·香奈儿宿命般地相遇,这段短暂而热烈的恋情据说直接催生了著名的香奈儿五号),或许是一生的好运都在一年之中全部花完(让人想起陈奕迅《明年今日》的歌词: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随后等待着斯特拉文斯基的是漫长而颠沛的流浪生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肯定没有意识到,终其一生的漫长流浪已正式拉开了序幕。同年,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迁居到中立国瑞士避难,一住就是五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斯特拉文斯基所有的私人财产(包括土地)全部被没收,这彻底割断了他与故乡仅有的联系,从此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
瑞士避难期间,斯特拉文斯基有过两次重要的旅行,分别是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可以说,这两次旅行对斯特拉文斯基逐渐走出“俄罗斯风格”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与俄国民族既相似、又相左的西班牙民风”表现在他1917年创作的四手联弹《小品五首》中,而在意大利的旅行中,不仅那不勒斯的风格影响到了未来对于《普尔钦奈拉》(1919)的创作,与另一位艺术大师的会面仿佛让他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影子,他就是毕加索。这位以风格多变著称的艺术大师对斯氏美学风格的形成和探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后来,斯特拉文斯基被公认为“音乐界的毕加索”),而他的音乐杰作又对20世纪的舞蹈、绘画甚至是诗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诗人埃兹拉·庞德曾说:“斯特拉文斯基是世上唯一一个音乐家,让我可以与之取长补短的。”
一战后,斯特拉文斯基举家移居法国。在这个世界艺术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艺术家们开始对世界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并通过各自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新古典主义是其中一股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浪潮,不论是毕加索的绘画、纪德的小说还是瓦雷里的诗歌,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有着新古典主义的痕迹。斯特拉文斯基也开启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走向新古典主义。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将在我的新作品中回归巴赫。这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我没有将自己朝巴赫的方向,而是朝单纯对位的那种充满光明的观念发展,这种观念在巴赫以前很久业已存在,而他被视为其代表人物。……我不再寻求扩大音乐表现手段的范围,我寻求的是音乐的本质。”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特拉文斯基在法国生活了近20年后,再次被迫流亡。流亡似乎构成了他一生的宿命,从俄国到瑞士,从法国到美国,一生的颠沛流离与他在千年音乐历史中的游荡形成了某种命运般的呼应,他的最后一部歌剧《浪子的历程》(1951)中那种苦涩的身世之感成为了其一生的隐喻。从五十年代开始,斯特拉文斯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但其“音乐生命却依然旺盛”,他发现在青年作曲家中广泛流传的十二音作曲法后,又重新燃起了对于“序列主义”的兴趣,于是以古稀之年的高龄再次投入到新的音乐理想中,并为之一直创作到生命的尽头。
他明白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瑞士,还是法国,抑或美国——都无法代替他的祖国,于是他便在音乐的国度中找到了安放自身的原乡。是的,他唯一的祖国,唯一的安身之处,就是音乐,就是一切音乐家的全部音乐,就是音乐的历史。于是,他成了一个流浪在整个音乐历史中的游荡者,他决定在其中安置自己,正如另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流亡者苏轼的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在那里,斯特拉文斯基最终找到了他仅有的同胞,他仅有的亲人,从佩罗坦到勋伯格,从马肖到韦伯恩,正是和他们,在千年音乐历史的河畔,他开始了至死方休的漫漫无期的长谈。
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妙见,延续一千多年的欧洲音乐历史分别经历了两个半时。上半时的象征顶峰是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下半时的开端则以最初的古典主义音乐家的作品为标志。显而易见,两个半时存在着巨大的美学鸿沟。然而,一个基本而普遍的经验是: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下半时美学的熏陶。音乐历史的下半时不仅将上半时遮挡的黯然失色,而且将其压抑住。巴赫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遗忘的历史境况揭示了这一点。蒙特威尔第和巴赫构成了千年音乐历史的种种倾向的第一个交叉点:它是两种相对立的音乐美学的遭遇之处,前者建立在精巧的复调音乐的基础上,后者则建立在标题性主调音乐的基础上,并强调音乐的表现力。这预示了音乐由上半时向下半时的过渡。
在巴赫身后的两百年,种种历史倾向的又一个交叉点出现了,它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音乐的千年往昔从整个19世纪中从遗忘的迷雾中缓慢地显现出来,在这唯一的时刻,克利俄女神(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女神之一,司掌历史)的神秘容颜一下子全部展现出来,它的全部的美都变得触手可及。正是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中,这一总结性的时刻找到了属于它的纪念碑。由此,斯特拉文斯基所领导的现代派音乐就像日暮时分天际的晚霞(千年的欧洲音乐历史即将沉入无尽的暗夜之中),以其短暂却令人心醉之美开创了音乐历史的第三时。斯特拉文斯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俯身在千年音乐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灵感,他的这一有目的、有意识的、规模巨大且独一无二的“折衷主义”(将由格林卡所开启的俄国音乐所特有的“折衷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构成了他整个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
于是,为了能让自己感到是在家中,斯特拉文斯基做出了一切的尝试。他在这个房子的每一个房间里停下来,仔细欣赏、抚摸着不同年代的家具。他徜徉于千年音乐历史的长河之中,从古老的民间音乐到佩格莱西,后者给他带来了《普尔钦奈拉》(1919);他拜访其他的巴洛克大师,尤其是法国歌剧创始人吕利,没有他,《众神领袖 *** 》(1928)便是不可想象的;他从音乐前辈和同胞柴可夫斯基那里改编了旋律,用于他的《仙女之吻》(1928);巴赫成了他的《钢琴及管乐协奏曲》(1924)和《小提琴协奏曲》(1931)的教父,他还重写了这位教父的《基督升天圣诗变奏曲》(1956);在《雷格泰姆十一重奏》(1918)、《钢琴雷格泰姆音乐》(1919)、《爵士乐团前奏曲》(1937)、《乌木协奏曲》(1945)中,他将爵士乐发扬光大;他反复借鉴莫扎特多部歌剧的动机、主题和音色,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歌剧《浪子的历程》(1951);佩罗坦和其他复调音乐家启发了他的《圣诗交响曲》(1930),尤其还有他令人惊叹的《弥撒曲》(1948);在1957年,他专门研究了蒙特威尔第;1959年,他改编了杰苏阿尔多的牧歌;对胡戈·沃尔夫,他有两首改编歌曲(1968);对十二音体系音乐,他先是有所保留,后来在他一生的对手勋伯格于1951年逝世后,他也终于把它当作了自己家中的一个房间。
1962年9月21日,阔别故乡48年之久的老作曲家在受到苏联 *** 的邀请后重返故土,在莫斯科指挥了两场音乐会。然而,他所目睹的这个国家与他所熟悉的祖国已截然不同,他心中的那个唯一的故乡早已不复存在。在短暂的逗留后,他旋即回到美国。事实上,自从1928年写了《仙女之吻》这一对柴可夫斯基的纪念作品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主题上来。1971年4月6日,斯特拉文斯基以90岁的高龄于纽约辞世。他的夫人薇拉遵照他的遗愿,拒绝了苏联 *** 提出的将他的遗体运回俄罗斯安葬的建议,把他移葬在他心爱的 *** -圣米切尔公墓岛上,离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安息之地不远。
余响:“缺乏情感”的音乐家?
毋庸讳言,后世对于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个普遍而激烈的批评是:缺乏情感。杰出的音乐家、指挥家,同时也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最初演奏者之一恩斯特·安塞美(斯特拉文斯基在《我的生活纪事》中说:他是我最忠实最虔诚的朋友之一),后来却成了斯氏无情的批判者。对此,安塞美的异议是根本性的,它涉及到“音乐的存在理由”。在安塞美看来,“人心之中潜在的情感活动,一直以来是音乐的源泉”,在斯特拉文斯基这样一个“拒绝让自身介入到音乐表现行为中去”的人身上,音乐“不再是人类伦理学的一种美学表现”。
其实,这背后涉及到围绕音乐本质的一桩争论上百年的著名公案,一方是自律美学观,另一方则是他律美学观。音乐自律论的代表是19世纪著名美学家、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立克,他在《论音乐之美》一书中言之凿凿地宣称:“音乐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只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情感的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音乐也不是必须以情感为对象,音乐不描写任何情感。……音乐的原始要素是和谐的声音,它的本质是节奏。”显然,斯特拉文斯基自觉继承了自律美学派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在《我的生活纪事》中如是写道:“音乐无力表现任何东西:一种感情,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心理状态”。斯氏明确表示:音乐的存在理由,并不寓于它表达感情的能力。
颇为吊诡的是,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和柴可夫斯基似乎构成了音乐美学的两个极端,前者将所有的感情(尤其是浪漫主义情感)全部排除在音乐之外,以歌剧清唱剧《俄狄浦斯王》为典范;后者则达到了人类情感表现力的某种极致(甚至被人诟病为情感泛滥),以《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为代表。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斯特拉文斯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仅毫不排斥,而且欣赏有加,他认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虽然“主题和创作冲动基本上可以说是浪漫的,但他在体现主题和创作冲动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创作态度却一点也不浪漫”,柴氏的乐句段落和结构安排得十分完美。
由于音乐历史下半时的影响过于强大,也由于音乐必须天然表现人类情感的他律美学观过于强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奇特景观:广大观众一方面对他的早期作品的广泛流行而授予他最高的骑士爵位奖,另一方面却对他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保持相当冷漠的态度。其实,普罗大众有责任记住:今天已经不是亨德尔的时代,大量的情感内容对伟大艺术而言并不是一种必要的东西。如果说毕加索可以在绘画领域开拓出令人眩晕的“立体主义”(它似乎完全排除了绘画中的感官之美),卡夫卡可以在小说领域以谜一般的不确定性彻底颠覆传统小说的叙事范式(它没有起始,没有结尾,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方向,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没有,完全排除了小说中的叙事之美),那么斯特拉文斯基为什么不能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以新古典主义的绝对严谨、均衡和控制而将情感表现排除在外呢?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中挖苦斯氏只受音乐的启迪,是“依据音乐产生的音乐”,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评判。
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而言,或者更广泛的说,对于过去一百年间的所有作曲家而言,我们应该对他们试图摆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所带来的长久阴影的震怒心情表示同情。当然,真正的震怒心情乃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救世心理(这既是对即将沉入漫漫暗夜的千年音乐历史的拯救,也是对作为一个宿命般的流亡者的自我救赎),因为这促使他穷极一生不断找寻着新的表达方式,而瓦格纳的盲目崇拜者还在软弱无能地进行着各种拙劣的模仿。
根据一种民间说法,在人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垂死之人会看到他度过的一生一幕幕地从眼前浮现。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欧洲音乐回忆起了它跨越千年的生命,这是它走向一场永恒的无梦的长眠之前的最后一梦。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常被比作音乐界的毕加索(1881-1973)。这个类比有恰当的一面:两位都是20世纪艺术发展中各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大师巨匠;作为同龄人,两人是多年好友,有过深度艺术合作,如1920年首演的芭蕾舞剧《普尔钦奈拉》即由斯氏作曲,毕加索出任舞台和服装设计;而在创作此剧期间,毕加索给这位作曲家留下的画像是捕捉斯氏外貌特征与精神气质最传神的难得佳作。尤其是这两位同样长寿的艺术创造者均经历了崎岖不平的多次风格转折,从中映射出20世纪美术与音乐中一些最典型的风格走向与美学旨趣——正如毕加索的“蓝色”“玫瑰”“原始主义”“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个风格时期反映出20世纪复杂的美术潮流和风尚变动,斯氏音乐创作中公认的风格时段划分——“新民族主义”“新古典主义”“序列主义”三个时期——也大致代表着20世纪中最重要的几个音乐风格取向。
但两人的彼此相似或映照也不能推得过远。毕竟两人身处音乐和美术两个全然不同的艺术领域,面对的艺术传统和面临的创作问题也迥然相异。毕加索来自西班牙这个具有深厚美术传统的国度,而斯特拉文斯基出道时,刚好搭上俄罗斯这个音乐“新晋”强手的顺风船。20世纪初,俄罗斯音乐经过19世纪中后叶的迅速攀爬和追赶,已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正开始进入世界音乐市场的常备曲目库;如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俄罗斯钢琴名家也已打入欧美音乐主流——1910年1月16日,拉氏以作曲家和独奏家的双重身份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上演自己“新鲜出炉”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由当时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古斯塔夫· *** 执棒,纽约爱乐协奏,而日后它将光荣位列世上最著名、最优秀、演奏难度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林。
正值此时,斯特拉文斯基(1901年斯特拉文斯基入圣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1903年师承当时的俄罗斯音乐泰斗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驶入快车道,将俄罗斯音乐推至世界音乐艺术的最前沿,令人惊诧不已,并由此“暴得大名”。借助俄罗斯当时最有商业嗅觉和艺术敏感的经纪人大亨谢尔盖·佳吉列夫(1872-1929)的慧眼识才和巧妙运作,斯氏的“三大舞剧”——《火鸟》(1910)、《彼得鲁什卡》(1911)和《春之祭》(1913)——在巴黎炮炮打响,而且越打越响!尤其是《春之祭》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当夜(1913年5月29日),由于编舞(出自芭蕾舞天才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之手)和音乐在艺术特质上的超前和“先锋”,引发了史上一次极为著名的剧院骚乱——而这恰恰为此剧(尤其是它的音乐)成为现代艺术名垂青史的经典预设了前提。
《春之祭》作为20世纪音乐——乃至整个音乐史中——最重要的界标和里程碑之一,其地位和声望早已得到公认。但这部现代音乐杰作之于俄罗斯音乐尚有另外一层特殊的意义,似还需要强调。19世纪初以前,俄罗斯仅是世界艺术音乐的“消费者”(引入意大利歌剧等“高文化”艺术音乐品种供皇宫和贵族消费,但尚未产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作品)。自19世纪初以降,随着俄罗斯民族意识高涨和国力增强,俄罗斯在音乐上的身份发生重要改变——从“消费者”变为“生产者”:以格林卡、“强力集团”和柴可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音乐创作让世人刮目相看。随后至20世纪初,俄罗斯猛然发力冲刺,从“生产者”再次升格,一跃成为音乐艺术的“领跑者”——而这一飞跃最醒目的标志正是《春之祭》。
这里的所谓“领跑”,指的是艺术观念和技术实现均处于探索最前沿和创新最前端,并对整体音乐艺术文化产生持久后续影响。《春之祭》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意义的总谱大作——为了表达俄罗斯远古时代“以人祭天”的原始 *** ,作曲家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构想和精密构思,将庞大而复杂的现代交响乐队转化为一个遍布荆棘、充满野性感的巨型打击乐组合。听者耳边响起前所未闻的奇异声响和刺耳和声,无规律的节奏悸动和突如其来的重音敲击栩栩如生地捕捉到原始人类的生命本能与狂放血性。以打破传统技法和表现常规为突出特征的“现代音乐”美学在这里得到一次集中、 *** 并带有爆炸性的展现。
俄罗斯音乐自此在世界音乐的总体图景中“抢得先机”——它不仅是已有规则和价值的承继者和执行者,而且成为新规则和新价值的创立者和引领者。斯克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以及稍后的普罗科菲耶夫等,一同见证并参与到这个抢得先机的行动中。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俄罗斯音乐的角色转变恰也暗合了音乐艺术的一次重大风格分水岭的划分:从(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长19世纪”迈向“短20世纪”。传统音乐的堡垒阵地——功能和声-调性体系——在德彪西、 *** 、理查·施特劳斯和勋伯格等人的扩展、扭曲或直接攻击下摇摇欲坠(事实上,勋伯格已在1908年正式抛弃调性而进入“自由无调性”写作)。从现在的视角回看,《春之祭》正是宣告旧时期终结、新时代来临最强烈的音乐信号之一。
斯特拉文斯基自己也不负众望,自《春之祭》后一直以执音乐之牛耳的姿态站立在时代潮头,并将这种地位保持至去世:他是“新古典主义”这一20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重要风格倾向的首席代表,而在晚年又以独特角度吸收十二音序列主义的创作思路,从而将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创作思维集于一身。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认为,《春之祭》有时显得过于外露、张扬,刻意求工(见沃尔科夫记录整理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但此书的真伪存有争议,姑且信之),而《彼得鲁什卡》通过描写木偶彼得鲁什卡遭受侮辱和损害的故事,写出了俄罗斯普通人的悲剧、悲情和悲悯——一句话,有穆索尔斯基的遗韵,而穆氏是肖斯塔科维奇最推崇的俄罗斯作曲家前辈。《彼得鲁什卡》恰好位于偏向传统“民族乐派”的《火鸟》和已经跨入现代主义大门的《春之祭》之间,它既有好听而地道的俄罗斯民间音乐元素(以第一场和第四场的集市音响描画为代表),也有极为尖锐而鲜明的现代音响特征(以著名的“彼得鲁什卡”双调性 *** 为代表)。相比之下,《春之祭》总给人一种不祥的凶兆感——运用高度发达的交响乐(及芭蕾)手段,最终的目的却是刻画重回“蛮荒”的想象图景。这其中似有某种二律背反式的文化暗示:工业化的高级文明,结局导向却是原始的野蛮。考虑到《春之祭》的诞生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之前,这部作品就好似针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某种悖论式的隐喻,听起来令人心悸,观看时让人不安。它体现出某种“狰狞”的美——而这正是20世纪之前的音乐所不知道的新发现。
北京音乐节舞台
谭盾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携三位演奏家为观众们献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罕见上演的早期作品《焰火》和经典的《火鸟》组曲,与谭盾的《古筝与琵琶双重协奏曲》及二胡协奏曲《火祭》对话。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于1908年的《焰火》,据说这是斯特拉文斯基给他老师女儿的结婚礼物,带有印象主义色彩。
有着“音乐界毕加索”之称的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是谭盾自学生时代起就景仰的“英雄”,本场演出与其说是两者的对话,不如说是谭盾在自己年少时心目中的英雄逝世50周年之际,用音乐献上自己的纪念与致敬。北京国际音乐节曾在第十五届时委约谭盾创作了混搭摇滚、京剧与无调性音乐的《青春》,充分彰显音乐节和作曲家彼此对无所畏惧的不羁想象的肯定。本次闭幕音乐会上,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谭盾创作的二胡协奏曲《火祭》首演,作曲家将中国传统的祭祀音乐与宫廷音乐相结合,以五种情绪构筑一出当代音乐的舞台祭祀,想象人与自然的对话,表达对战争的反思,祈愿人类和平。在这部作品中,谭盾首次将二胡与交响乐并置,效果强烈而丰富,意韵深刻、悠长。谭盾将几年前为民族管弦乐乐队创作的一部作品做了改编,将原先作品中的高胡、中胡和二胡改成了奚琴和二胡,把民乐队变成了交响乐队,令这首作品变成了可以全世界演出的作品,并定名为二胡协奏曲。作品中用到了一个特别的乐器奚琴,它是二胡的前身,二胡演奏家陆轶文表示:“奚琴是三根弦,这种古老的乐器是从敦煌壁画中走出来的,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改用奚琴这门乐器,还有一个小插曲。谭盾透露,自己曾在敦煌看壁画的时候发现了奚琴,这个壁画上的乐器。“从这个壁画我们就开始琢磨着如何把中国最古老的音乐壁画变成声音,于是这个奚琴就成了我们其中的一部分。”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22821347361456676/?channel=&source=search_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