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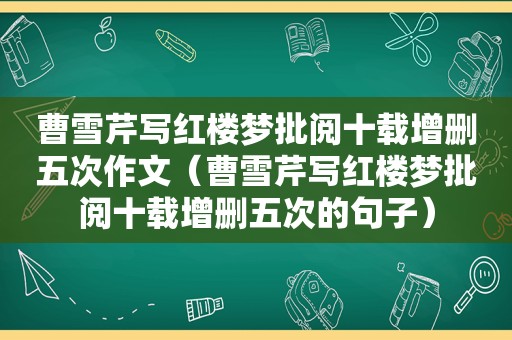
雪芹的家遣离南京后,心情十分黯然。但返抵北京,有一个时期家境还不算黯淡。
家是败了,但离了南京祖居之地,进的是北京祖居之地。曹家在北京原有住房二所,住有族人,还有空房一所。这些房屋,其中一座是高祖辈随正白旗旗王多尔衮入关进京后分得的颇具园林之胜。曹家被抄,北京房产,也就充公了,到曹家北归后,是住进祖屋的,不过不会是那所祖上遗下的大宅子,他们是罪人家属,生活自然也根本不能与南京时相比。叔父曹遗依然被拘禁,一年多以后才从监狱内放出来。
曹遗被抄家,但他没有株连九族。雪芹叔祖曹宜依然是内务府官员;祖姑父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兵都右侍郎傅鼐;姑父平郡王讷尔苏获罪被流放,圈禁,但另有罪名,与曹遗被抄无关。祖父的门生故旧,有的还做着大官。设法在有限的程度上照应曹家的人,也是还有可能的。
曹家过着带罪人家的日子,过了几年后有所缓和。主要是大环境即雍正朝局已趋稳定。到了雍正九年,流放的傅鼐已得起复并重新受到朝廷重用,纳尔苏之子福彭(雪芹表兄)也袭了平郡王爵位,还加了官,进入朝政中枢。叔祖曹宜也加官晋爵,任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雍正当政十三年上病死,乾隆皇帝即位,普施恩惠,曹家也因此沾光。先是以曹宜功劳追封其祖父曹振彦为资政大夫,然后下旨“历年亏空之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大多数前朝侵吞挪用款项的罪官宽免追赔,曹遗等骚扰驿站案应赔银两也获宽免,曹遗也重新起用为内务府员外部。曹家不再是罪臣,又上并到小康局面了。这就是《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提到的:“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但是好景不长,乾隆三年,傅鼐因“种种营私”革职病死。有研究者推测,转年曹家也因为什么事情而彻底破落。到乾隆十三年,福彭死去,曹家的几家重要亲戚就也都衰落了。在乾隆初年曹家稍稍振起的时节,家里曾送雪芹人内务府主办的官学读过几年书,目的是要他参加科举。但雪芹仍然无意功名。二十多岁的雪芹就闲在家中,家中只好求有权有势的亲戚帮忙,为雪芹取得贡生的资格,这就是雪芹的一世“功名”,对此雪芹也没有决然拒绝,因为他觉得不能剥夺长辈们想取得的这点安慰基于同样的原因,后来他在右翼宗学时结识的友人敦诚科场不利,他也曾劝慰过,这是敦诚诗中记得的:“三年下第曾怜我”。
从雍正六年自南京到北京,到乾隆四五年,曹家经过几年罪臣生活几年小康生活,最后又从小康生活跌落下来。生活境况急骤变化,居所也在皇城内外播迁。确切的记载没有,估计他们住祖居的时间不长,也可能是穷而变卖,他们又从祖居搬出,传说他们住过什刹后海南岸,住过西城旧刑部侍,住过外城广渠门内卧佛寺,或个安门内千佛寺,或西城卧佛寺,甚至还有传说住过某王府的马厩……传说并不都可靠,但雪芹因穷途末路,居无宦所,时好时“坏”,成租凭,或向亲戚朋友求告借居,添居,总之为觅栖身之地而在京城四处流迁,是极可能的。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竭蹶中,雪芹早早结束了少年,度过青年。迈向中年。过了而立之年的雪芹,经人介绍,找到了一份谋生的差事,到朝廷为皇族宗室子弟开设的官学去当职员,做文书之类的工作。
八旗宗室按左右两翼分设宗学,雪芹任职的右翼宗学。右翼宗学地址那时在西城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是一所古老的大宅。学中子弟六十人,有总管、清书教习和汉书教习若干,职员和杂役若干。雪芹在这里当差的年份,在乾隆九年到十九年之间的某一段。
他在这里结识了两个交往颇深的友人,都是宗学的学生,一个叫敦敏,一个叫敦诚,是两兄弟。他们年纪比雪芹小二十岁左右,雪片与他们是忘年交。后来雪芹离开右翼宗学,迁居西郊,他们仍城里城外往来。雪芹病故,是敦氏兄弟帮助料理后事的。多亏了这两个人,由于他们的诗文中记载着与雪芹的交往,才使我们对雪芹的生活与为人,对他中年时代以至亡故有了一些尽管是片断却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敦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英亲五阿济格五世孙。阿济格因夺位之谋,被顺治皇帝逮捕,削爵,幽禁,抄家,最后赐自尽。他的妻小家人,籍没为奴。雍正朝后裔得以从“庶人”恢复宗室地位,但接着受党祸牵累,所以到了敦敏敦诚这一辈,就完全是破落的飘零弟子,名为宗室,实同平民。二敦与雪芹同有家世之痛,同时牢骚不平。同处于潦落抑塞之中,共同感受着“世味薄于纱,境遇泛如电”的人生况味;两兄弟的个人爱好和性格,也和雪芹相近,耽迷于诗,负磊落怀抱,而且二人都特别敬佩雪芹的才华与为人。因此,尽管他们一个是包衣身份,两个是闲散宗室,一个是宗学职员,两个是宗学学生,年龄相差又那么大,却以气味相投而交情甚笃。
宗学学生是要在校住宿的,宗学职员日间不说,有时夜间也要轮值在校照料。所以他们相聚畅谈的机会很多。多数时候是二敦与雪芹,他们的同学有时也加进来谈话。大家也都愿意与雪芹聚谈,因为雪芹是个谈锋甚健,热情豪放,气度爽朗,博闻多识,极有吸引力的人,有他在座,总是满室生春。
若干年后,敦诚在《寄怀曹雪芹》诗中,回忆当日情景:“当时虎门数畏夕,西窗剪烛风雨昏。口接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所谓“虎门”指的就是宗学。取得是《周官》“立学于虎门外以教周子弟”之义。“西宿剪烛”典出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说的是友人间接谈竟夜风雨绵绵,友情更密,谈兴更浓,蜡烛不知换过多少支,剪过多少次了。“接罱”指头帅,晋代名士山简与友人出游;酒醉而归,半扒半骑在马上,白接罱歪戴着,路人与儿童见了,又好笑又敬爱。“虱手扪”也是晋人故事,五猛去见大将军恒温,一边谈话,一边揭起衣服捉虱,表现着一种率真,放旷的风度。敦诚这样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与雪芹交往的友情,另一方面对我们更重要的是,勾画了雪芹高谈雄辩,睥睨世人的气概。
敦敏也有诗记雪芹在人群中洒脱不羁情景,这诗有个长题目,本自就是记事:《匠圃曹君露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洒话旧事,感成长句》。诗中有名“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急倍殷。雅织看渐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明琳也是雪芹的一个友人,是和敦敏敦诚一样的宗富子弟。雪芹在明琳处作客,高声大噪,意兴风发,隔着一个院子就让人听到了。那才气横溢的高谈宏论,使他就像一只卓拔绝尘的野鹤站在鸡群中。敦敏也为自己未见其人仅凭其声就够辨认出久别的老朋友雪芹原来在这而惊喜和得意,觉得自己也有点像晋朝的褚太傅,不认识孟嘉,却凭其不同的气度,一下就把他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一样。孟嘉是恒温的参军,在当时士大夫中以谈吐脱俗潇洒逸群著称。
这就是敦氏兄弟用诗的语言为雪芹绘的一幅传神的肖像。在场的养石轩主人明珠,虽然没有直接在诗文中为雪芹 *** ,却把自己的印象传给了外甥裕瑞。后来裕瑞在《枣斋闲笔》中,根据舅父明珠他们的印象,写下了一则文字记载:“雪芹……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令人终日不倦……”。
雪芹与友人们谈什么呢?具体内容没有资料留下来。但敦诚写进一篇《闲慵子传》,说:“成良友以酒食歌唱相招,不为月日,亦不说鬼。”敦诚又在《鹪鹩庵杂志》中说:“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又在奇谐雄辩,逸趣横生,词文书史,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语旧,击钵分笺,兴致亦豪,雅言泪出 -一是谓谈之中乘;议论不尽知之政乏,藏否无足数之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羡没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
敦诚交友虽然不只雪芹,但豪谈者恐怕没有超过雪芹的。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雪芹在宗学中、宗学外,与敦敏敦诚等人的交游中,不议论“岩廊”即朝政得失,不评价权贵显宦是非,不计较个人一时荣辱--对于二敦,雪芹这样的破落宗室与世家子弟来说,“莫谈国事”是可以理解的,这既是为了避祸,也表现着他们的脱俗。他们所谈的,主要是词文书史、旧识新知,互相诵读自己的诗文新作并讲评彼此唱和之作。他们的谈话,奇僻诙谐,析理辩玄,挥洒豪雄,逸趣雅言流溢于满座之间。
在这种畅怀剧谈的场合,倾杯倒盏之际,雪芹也应朋友们之请,讲他为《红楼梦》所写的章节,他开玩笑地对友人们说:“若有人欲快睹看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鹅享我,我即为之作书。”
艰难的时世,坎坷的身世,潦倒半生的际遇,没有挫折雪芹的心志,没有毁堕雪芹的精神。他行走在皇城根下,像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也像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雪芹与友人倾谈不评论朝政,不藏否权贵,不计较荣辱,并非他不知不识,乃是由于现实环境所阻。他把抑塞情怀留给自己,只以傲态狂形示人。
清代嘉靖、道光年间行世的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有一条批语,“曹雪芹为楝亭曹寅之子,世家,通文墨,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开庵所为者。”周汝昌在所著《红楼梦新征》和《曹雪芹小传》中都用了这个材料,并加以解释,看来这条批语虽是传闻,却也不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我们知道,贾宝玉与世家子弟下海演戏的柳湘莲,与名旦角蒋玉涵,与贾府戏班中的女伶如芳官、龄官等,都有密切接触并且尊重他们,这是《红楼梦》写明的。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把“奇伏名倡”与历代逸士高人、诗画名家,乃至帝王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列为同类,这也是红楼梦开卷即载明的。如果说雪芹幼年时“杂优伶中”是一种爱好,一种对伶人的理解和尊重的话,那么,他在青年,中年时代的“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就不只是单纯的爱好,也不只是对伶人的尊重,而还是一种傲世态度,一种抗世行为了。
清人杨懋建的《余尘杂录》中提到几个怀才不遇的士人,放浪形骸躬为优戏的故事。一个明代的才子杨升庵,他被贬到云南时候,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满头,让他的门生,以及他招致的 *** ,把他抬起来游街,招摇过市。明代苏州才子唐寅,大夏中游虎丘,模仿乞丐唱莲花落。清代乾隆间才子黄仲则居京师,落落寡言,不登树贵的门,却愿意混到世人们中间去吃他们的饭。他又和艺人一起抢装演戏、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谄笑傲、旁若无人。这是“才子失意,遂至逾闲荡检”的事例。
“傲世也因同气味”,雪芹“杂优伶中”演戏为生的行为,与杨升庵、唐寅、黄仲则们有相似处,都表现着一种支离傲骨,是一种带社会性的个人行为;而雪芹行为中的社会内涵,却比他们更深广。
雪芹还是个酒徒。一个深秋的早晨,风雨淋漓、朝寒直透衣襟,敦诚到哥哥敦敏的槐园去,在那里遇见了雪芹。时候太早,主人敦敏还未出来,而雪芹“酒渴如狂”忍也忍不住。敦诚就和雪芹到附近一个酒店沽酒,因为敦诚也没有带钱,就把佩刀解下来交给买酒老板,权当酒钱质典在那里。雪芹饮得很尽兴,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都想起醉人仙之一唐诗人贺知章不惜掷所佩金龟来换酒,晋人阮孚摘下所佩貂沽酒狂饮的故事。敦诚说,我和你都是和战国齐人能饮一石酒的淳于髡一样的酒徒,今日秋寒相逢,得各饮一石才可以暖暖肚肠呢?我这佩刀,既没有人好赠,也用不着卖它买牛来耕田,我又不为拿它出征边疆杀敌,还不如换酒一斗喝个够,让肝肺烧得像生出棱角长出针芝一样呢!雪芹听后大笑,连称痛快痛快!
友人们都知道雪芹能饮酒,恐怕这是丛小养成的。《红楼梦》中有影子,黛玉就深知宝玉“是好吃酒看戏的”。有次宝玉在薛姨妈处吃酒,心酣意洽,宝玉是这样,雪芹一定也是这样。成年后,饱经忧患,雪芹豪伙就未为都心酣意洽了。有时是慷慨悲歌,有时是愁绪满怀。没有钱,则“卖画钱来付酒钱”。饭都吃不上了,却要赊酒,“举家食粥酒常赊”,他的伙酒也是有性格的。“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肯向人斜”。“步兵”即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诗人阮籍,酣饮以避世,他听说步兵厨役善于酣酒,贮存的酒有三百斛之多,就请求做步兵校尉,以便鲸吸海饮,所以时人称他“阮步兵”。他对守俗礼的人总是对以白眼,对旷达之士才对以青眼,因此礼法之士都很恨他。雪芹之伙,也是有魏晋名士之风,有“抗世违世情”意味的。
更可注意的是,雪芹杯中常映出往昔岁月,每当他“呼酒话旧事”,说到“秦淮旧梦人犹在”。他就容易不胜酒力,就容易白眼向人,正所谓“燕市悲歌酒易醺”。这“燕市悲歌”或“燕市哭歌”典出《史记·荆轲传》。战国时卫国的饮士荆轲,流亡于燕国,抑郁不得志,他嗜饮每日与高渐离饮于燕市,他们痛饮一番之后,高渐离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荆轲和着节拍而歌于市中。两人一时相对大笑,一时相对而泣,旁若无人。司马迁说:“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就是说荆轲虽然耽于酒,但也是很清醒的,他的耽于酒不是他的肤浅,正是他的深沉。敦敏的诗写雪芹“燕市悲歌”既是用典,也是纪实,杯中有岁月的梦,酒里有醒着的精神。雪芹“燕市哭歌酒易醺”因为在他的旷达后面,有着难以排遣的抑郁。一方面,他“杨州梦久已觉”,另一方面,他这个经历过秦淮旧梦的人还在,斩不断对秦淮风月,舍陵姐妹,瞬息繁华的追思、忧思、反思。雪芹的“嗜酒”,有“借于酒”、“寓于酒”的更深长的意味。
清人杨钟羲《寻桥诗活》中说,曹寅早年与其他五位名士,同以性情高介,诗酒自豪,为都中士人所知,有“燕人六酒人”之称。
雪芹也是燕市一酒人,也与朋友中的酒人交游。正如太史公慧眼所识,“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雪芹也是这样,他因深沉而嗜酒,又因嗜酒而深沉。他也“好书”不只好读书,而且好写书--写那部叫做《金陵十二钗》或《石头记》、《红楼梦》的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