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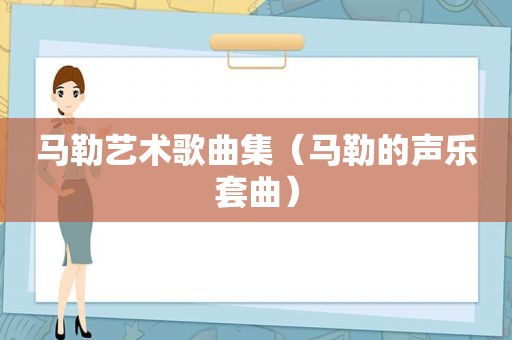
美国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汉普森(Thomas Hampson)在过去的20年里几乎是古斯塔夫· *** 的艺术歌曲的代言人,特别是《少年的魔法号角》——他以歌唱家的身份至少四次灌录过这部作品,并且以 *** 研究专家的身份重新编定了“魔号”钢琴伴奏版本的乐谱。2016年3月6日,汉普森第一次在中国登台演出,他所选择的曲目也正好是“魔号”中的6首歌;之前一天,我有幸在乐团的排练厅里占用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这篇访谈。
©摄影:韩军
另外,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可以通过以下链接在线欣赏:
中国爱乐乐团2016年3月6日交响音乐会实况录音?
(访谈部分刊载于2016年4月号《爱乐》杂志)
这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 *** 的《少年的魔法号角》,音乐会之前只安排了一天时间的排练。一天时间就足够排练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吗?
排练时间永远不会“足够”,要么像这样在一两天之内解决问题,要么就是花费一周时间依然毫无进展。最让我放心的是,这支乐团以及指挥家在我到来之前进行了充分的学习与准备,明天我们会在音乐会之前再进行一次完整的走台,届时的效果会非常理想。今天在排练时,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讲述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因为我认为音乐就像红酒一样需要时间发酵,他们今晚回到家里也会继续思考这部作品,明天登上舞台时自然就会演奏出理想的音乐织体。
©摄影:罗维这是你第一次与中国的乐团与指挥家合作。你与他们合作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们合作的经历非常愉快。我并不认识指挥家张国勇先生,他也并不认识我;但是当两位职业音乐家站在一起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就用音乐的语言交流着我们共同热爱的东西。可能对于“魔号”这部作品来说我的经验相对多一些,他因此对我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我也很感激他用如此包容的心态来与我一同完成这部作品的演出。乐团同样在排练中展现出了极佳的专业性以及对我尊重,我对此十分感激。
你的歌唱事业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是直到30多年之后才终于第一次来到中国。为什么来得这样迟?
中国三十年前就有了吗?(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如今的环球旅行十分方便,但是在80年代,“去中国”还是一件听起来特别遥远的事情。相信中国也有不少音乐家忙于在北京、上海和香港这样的城市演出,因此不太关注外面的世界,而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我主要在美国和欧洲演唱大量的歌剧和音乐会,前者是我出生的地方,后者则是我居住的地方,由于欧洲的歌剧院很早就开始定期去日本演出,我也因此去过几次日本,但除此之外我几乎没有时间安排别的演出。直到近几年我才开始安排一些别的巡演,于是我才发现我竟然从来没去过澳大利亚,也从没去过波兰,俄罗斯和匈牙利也只去过一两次……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事实上很多歌唱家都跟您的情况类似,特别是那些在欧洲活跃的歌唱家,由于欧洲的歌剧院之间距离很近,他们只需要在这些地方巡回演唱就已经足够,去中国或日本这样的远东国家演出实在是太遥远了。
所以能否邀请到欧洲的歌唱家来亚洲演出,主要还是看音乐会主办者的决心。比如余隆先生为了邀请我来中国与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花费了很多精力,他还需要把音乐会的票卖掉,需要告诉所有人托马斯·汉普森是谁……
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汉普森是谁……
现在也许如此,但是在80、90年代是绝不可能的。因此我在这个时间点来到中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也很高兴能终于实现这个愿望。
您一直是美国艺术歌曲的积极推广者,除了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唱之外,还曾在PBS电视台录制过与此相关的电视节目,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合作推出美国艺术歌曲的项目等。其实很多来自美国的歌唱家似乎都有这种“情结”。几年前,美国女高音歌唱家黛博拉·沃格特(Deborah Voigt)也曾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整场音乐会上演唱的都是《香草冰激凌》等著名的美国歌曲。您觉得美国歌唱家们的此举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还是确实认为这些作品值得在音乐会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两者皆有。如果中国的乐团邀请我来演唱美国音乐——不论是经典音乐、艺术歌曲还是配乐诗歌,我都很乐意演唱。我的艺术生涯与古斯塔夫· *** 的艺术歌曲紧密相连,曾经与伯恩斯坦一起演出过这些歌曲,还作为编辑完成了“魔号”乐谱的校对,因此余隆先生此次邀请我来北京和上海演唱 *** ,而我也欣然接受。但下一次再来中国时,我很希望能带来一些美国的艺术歌曲—,比如科尔·波特(Cole Porter)或者乔治·格什温。另外,科普兰、卡朋特(John Alden Carpenter)、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巴伯等都写过非常精彩的艺术歌曲,我很想把这些歌曲带到中国。当我演唱美国歌曲——特别是对美国以外的听众们演唱时,会格外感受到某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但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在美国非常短暂的历史中,诗人与作曲家们是如此迫切地讲述着作为美国人的故事。在这段历史中寻找到一位像 *** 、勃拉姆斯或是舒伯特这样的作曲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把美国的历史分割成10到15年的片段,让美国的诗人与作曲家们通过音乐为我们讲述发生在每一个时间段里的故事,我们自然就会对美国的文化、民间音乐以及古典音乐产生全新的理解,而我们这代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音乐推广给全世界。我希望今后能尽可能多地来到中国,把这些精彩的音乐作品带给观众。
美国的歌曲相比德语艺术歌曲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流行。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原因很复杂。德国的艺术歌曲是缘起于19世纪的文化现象,这种由贝多芬与舒伯特等作曲家开创、融合了诗歌与音乐的全新艺术形式,从19世纪开始一直流行到我们的世纪,证明了诗歌与音乐融合而成的“歌曲”是叙述故事的绝佳手段。但19世纪的美国还太年轻,只能被动地从欧洲接受文化影响,无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德国(Lieder)与法国(Mélodie)的艺术歌曲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但不论是任何地方的艺术歌曲都比不上德国艺术歌曲中的原创性,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沃尔夫、 *** 、施特劳斯都太伟大了,他们的艺术是属于全世界的。因此我不认为其它国家的艺术歌曲——不论美国、法国还是捷克——写得不好,而是德国的艺术歌曲太强势了。另外我想指出的是,美国——特别是二战之后的美国——通常是与科技进步与经济腾飞联系起来的,我们总是把美国文化想当然地理解成电影、流行音乐与星巴克的天下……
还有爵士乐。
是的,爵士乐讲述的是真正的美国故事,毫无疑问。因此,我致力于推广美国艺术歌曲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美国诗人与作曲家的笔触,展示美国文化生活中知性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
本场音乐会上除了 *** 的《少年的魔法号角》之外,还安排了两部保罗·兴德米特的作品。这其实是很聪明的安排,因为 *** 与兴德米特都因为他们音乐中的“犹太性”而被德语社会所排斥,并都选择了美国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你认为美国在当时对于欧洲的艺术家们来说为什么如此具有吸引力?今天依然是这样吗?
你要知道,舒伯特在去世时,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美国作家詹姆士·菲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小说。当时,几乎所有作曲家、诗人、思想家们都梦想着去这个叫做美国的全新的国家看一看,虽然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欧洲艰苦许多,但是这里的民主、自由等社会理想却对欧洲的艺术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的30、40年代,纳粹政权的出现使得美国成为了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他们迫害的目标其实并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所有的先锋艺术(avant-garde)。兴德米特首先是因为创作先锋音乐而被当局禁演,因音乐中的讽刺性与冒险性而被当局所不容,随后才因为他的妻子有犹太血统而离开德国。我觉得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迫害,还会有那么多才智过人之士视美国为新的家园吗?3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简直是知识分子的天堂,那些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犹太大家齐聚于此,维也纳的犹太裔轻歌剧大师罗姆伯格(Sigmund Romberg)、弗利莫(Rudolf Friml)、赫伯特(Victor Herbert)都从维也纳来到了好莱坞,如果没有他们的到来,我不知道今天的美国音乐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除了政治迫害的原因意外,美国一直都认为实现理想的自由是人最重要的权利,这也许是吸引这些人来到美国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的对话很有意义,因为我在中国巡演时也在关注发生在美国的这届无比荒唐的总统大选,我在60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反过来看,民主制度的不可理喻早就根植在这个国家内部了,它虽然愤怒、洪亮且愚蠢,却能够自发地回归理性,因此我们只能祈祷它这次也能一切顺利。我想说的是,美国的社会理想被全世界的艺术家们认同,即使他们可能并没有到过美国,就像德国作曲家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终生没有到过美国,但他称自己是“精神上的美国人”。这个国家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而这是艺术创造力的真正摇篮,也是它真正的吸引力所在。
*** 的音乐最早也是在美国流行起来的,得益于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长期努力。您觉得作为美国音乐家会对理解 *** 的音乐有什么帮助吗?
*** 是一位影响力非常大的作曲家,对于他之后的所有作曲家来说, *** 都像是一位“先知”一样预言着音乐的走向,不论是对于贝尔格、韦伯恩、勋伯格还是理查·施特劳斯。而就我所知, *** 在欧洲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不流行,你甚至会惊讶 *** 的作品上演得多么频繁,甚至在纳粹政权的时代也并没有中断。伯恩斯坦当然重新点燃了人们对 *** 的热情,他将 *** 音乐的传统带回了维也纳爱乐乐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雅沙·霍伦斯坦、舍尔欣、米特罗普洛斯这些伟大的 *** 音乐诠释者,更不必说布鲁诺·瓦尔特了。伯恩斯坦在当时广受欢迎,他并没有“重新发现” *** ,而只是帮助 *** 的音乐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我不知道作为美国人会不会在理解 *** 的音乐方面更有优势,但我知道正是得益于伯恩斯坦这样的美国音乐家的努力, *** 的音乐会如此迅速地成为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
提到伯恩斯坦,您曾经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他多次合作。您是在认识他之后才开始研究 *** 的音乐的吗?
早在认识伯恩斯坦之前我就开始接触 *** 的音乐了。1986年我第一次唱歌给他听,当时我是去面试一个歌剧角色的,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唱过很多 *** 的艺术歌曲了,于是我主动提出来能否唱一首给他听。他在边抽烟边听我唱时突然喊“停”,让我把刚才的句子重新唱一遍。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别说话,把刚才的句子再唱一遍”。在我照办之后,他突然盯着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这样唱?”我只好回答说,因为 *** 就是这样写的,除了这样唱之外我不会别的方法。从此之后,伯恩斯坦开始决定教我演唱 *** 。他是1990年的9月去世的,我们在一起合作了4年,演出了许多部歌剧和大量的 *** ,也录下了多张唱片。我第一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也是与伯恩斯坦一起,当时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小孩子是谁”,演出的效果非常棒。伦尼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不会要求你一定这样唱,而是与我一起研究音乐的结构,搞清作曲家究竟想说什么,诗人究竟希望表达什么。他为我注入了自信心,使得我在音乐上的直觉可以帮助我成为更好的音乐家,对此我永远都怀着感激。
在遇到伯恩斯坦之后,你对 *** 的看法发生变化了吗?
在伯恩斯坦一起演出的那段时间里,我觉得我对 *** 音乐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对音乐的语言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一种讲述着我们生命的语言,它不仅仅是用来演出的,更多的是我们作为人类个体的心灵之旅,这是他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
《少年的魔法号角》是对 *** 启发最深刻的一本书,正像布鲁诺·瓦尔特所说的那样,当 *** 第一次读到“魔号”时,他就像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 作为一名出生在波希米亚的犹太人,为什么会对这样一部贯穿着基督教背景的德语文学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
*** 是犹太人、波希米亚人与奥地利人,而奥地利正处在德国认同感觉醒的时代。 *** 出生于1860年,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爆发战争、俾斯麦建立德国时他10岁,这是他成长中很重要的经历。 *** 在大学时代博览群书,他甚至曾犹豫自己应该成为音乐家还是作家,他读到《少年的魔法号角》也是在学生时代。人们认为《少年的魔法号角》是一部人间的“圣经”,他讲述的是人的言行、思想、理念等,而它之所以能够逃脱当局的审查是因为它被当作儿童诗歌对待。歌德曾经说,任何有思想的家庭都应该常备两本书:《圣经》与《少年的魔法号角》,前者讲述天堂的生活,后者则讲述人间的生活,使用了最戏剧性、最栩栩如生的语言。布鲁诺·瓦尔特说 *** 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其原因在于 *** 常被困扰的问题恰巧也是这本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天堂,我们为什么要去天堂;什么是死亡,什么是超越死亡;到底是如基督教说的那样因行善而得救,还是像犹太教说的那样“变形”(metamorphosis)而至往生。这些问题困扰着 *** ,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 读了太多书,他既是尼采也是叔本华。《少年的魔法号角》是原始的人类情感与行为的隐喻, *** 则用音乐的语言重新诠释了它,每首歌都像是一个微型的宇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 首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其次是犹太人——但他并不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所谓“犹太性”更多的是一个种族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 *** 的宗教信仰超越了所有的教条,我们无法用“犹太人”“基督徒”或是“神秘主义者”这样的成见来限定 *** 。他对人性的信仰是不曾磨灭的,爱与同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这些都可以从书中找到。
2011年,托马斯·汉普森与维也纳独奏家乐团合作录制了《少年的魔法号角》,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录制这套作品。这个版本由于是由室内乐团伴奏而十分与众不同。对于您来说呢?《少年的魔法号角》这部作品您已经录制过四五次了,它与 *** 的其它声乐套曲比起来有什么特别之处?
“魔号”是一个很大的集子,演唱者可以从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段落来演唱,所以有无穷的可能性。 *** 唯一的“套曲”其实是《亡儿之歌》,因为歌曲之间的逻辑、调性都是不可更改的,而《旅人之歌》、《吕克特歌曲》等都是可以自由调整顺序的。我一直都喜欢民间诗歌,而我最早对《少年的魔法号角》中神话故事的兴趣也是通过 *** 的音乐产生的。我对这部作品的特殊情感是与我编辑校对其乐谱有关的。 *** 设想中的“魔号”有三个版本:钢琴伴奏版,管弦乐团伴奏版,以及室内乐团伴奏的版本,但长期以来人们对 *** 的歌曲存在着误解,特别是钢琴版本的乐谱中伴奏部分使用的是管弦乐团伴奏的缩减谱,而这样是不正确的。我编辑出版了 *** 原始的钢琴伴奏乐谱,并将它题献给了已故的伯恩斯坦,现在这份乐谱已经是全世界通行的版本。我很庆幸自己依然常被邀请演唱《少年的魔法号角》,包括这次在中国的两场音乐会。
为什么这次在中国的两场音乐会选择了这六首歌?(注:帕杜阿的圣安东尼对鱼布道、塔中囚徒之歌、当美妙的号角声响起、人间的生活、天堂的生活、原光)
我其实给出了三套方案供余隆先生挑选,这套曲目是他的选择。《少年的魔法号角》中的歌曲是可以分成几组的,有主要讲述精神世界、超越性与死亡等话题的一组,有讲述军队生活的一组,还有寓言性质的一组,所以我试图从每组中都挑选一些出来。因此可以说这次巡演的曲目是我们双方共同决定的,我个人也很喜欢余隆先生选择的这一组歌曲,因为每首歌之间有着戏剧性上的关联,我也很高兴他挑选这一组。
我们似乎聊了太多与 *** 相关的话题了。除了 *** 之外,您最喜欢的作曲家都有哪些?
我全都喜欢,我也只演唱那些我欣赏的作曲家的作品。我喜欢太多作曲家了,包括法国作曲家、意大利作曲家……我觉得威尔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还有莫扎特与罗西尼。我刚刚花了一年时间演唱理查·施特劳斯,他的作品太不可思议了。当然,所有的艺术歌曲共同的“缪斯”是弗兰茨·舒伯特,他是一位我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天才,就像莎士比亚或者莫扎特一样,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舒曼也是非常伟大的作曲家,是他第一次将艺术歌曲真正带进了钢琴艺术的王国里。当代也有许多伟大的作曲家,美国女作曲家艾伦·茨维里希(Ellen Zwilich)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另外约翰·科里亚诺(John Corigliano)、理查·丹尼尔珀尔(Richard Danielpour)、珍妮弗·西格登(Jennifer Higdon)、马克·阿达莫(Mark Adamo)等,他们都曾为我写作过新的作品。另外,我也喜欢那些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我从来就不能特别领悟斯拉夫学派的音乐,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西贝柳斯——虽然我喜欢听其中的旋律,但我因为对他们的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无法演唱。音乐的世界是无穷无尽的。
刚才您也提到了演唱新作品的经历。最近几年似乎您一直致力于演唱新的歌剧与音乐会作品。
是的,我在过去十年中的每一年里都首演了至少一部新作品。我刚刚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首演了捷克作曲家米罗斯拉夫·斯尔卡(Miloslav Srnka)的《南极》,未来几年我也将继续致力于新音乐的演唱。
托马斯·汉普森在歌剧《南极》中。©Wilfried Hösl事实上,《南极》应该是您今年仅有的两三部歌剧计划之一,更多的精力将花费在音乐会上。您未来对自己的定位是“音乐会歌唱家”多过“歌剧歌唱家”吗?
其实我只是今年安排的音乐会多了一些,明年就不会这样了。我的定位就是“歌唱家”,我的工作是将人类的情感与思想用声音表达出来,不论音乐是由哪位作曲家写下的,我的工作就是理解他们想说的,然后唱给观众听。作为歌唱家,我的工作是为作曲家服务的。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北京之行的感受的。过去几天里北京的空气污染有些严重,这会对您的演唱有影响吗?
坦诚地说,来到北京之前我对此非常担心,因为也经常在CNN上看到对北京的报道,所以提前准备了口罩。我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住在洛杉矶,那个时候洛杉矶的空气质量非常可怕,广播里总是说“如果没有必要出门的话,千万不要出门”,但我还是在外面边咳嗽边慢跑。昨天我去长城游览,还买了一件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衫,正像 *** 说的,我现在是“好汉”了,游览的全程我是戴着口罩的。我是歌唱家,因此肯定会照顾好自己,明天的演出会非常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