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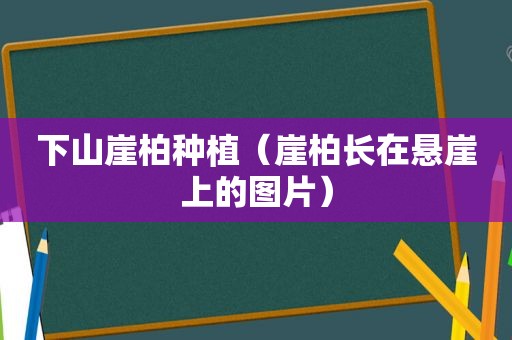
图①为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远眺。
图②为崖柏扦插繁育幼苗。
图③为在雪宝山保护区发现的一株野生崖柏,树高21米,树龄240年。
图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检查崖柏扦插苗木生根情况。
图片均由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
制图:张丹峰
今年以来,杨泉和他的团队风雨无阻,每天必做同一功课——认认真真为“小帅哥”拍照,认认真真撰写“小帅哥”成长日志,认认真真将“小帅哥”图文资料传给中国林科院专家。
杨泉是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负责人。秦巴古道上的雪宝山,两万三千公顷莽莽林海。杨泉身在其中摸爬滚打,已有二十个年头,过眼的树木不计其数。然而,他对其中三株情有独钟。
第一株,严格说来是一棵六百年前的树桩。上世纪树干被砍伐后,树桩上再生出十多株小树,如今有点独木成林的味道。
第二株,三百多年前的一棵树,因为长在当地农户的祖坟前,被长期保护下来,而今依然昂首挺立。
第三株,他们叫它“小帅哥”,去年出生,算是“早产儿”,当前还很孱弱,因身份非常特殊,受到林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
这三株树,共同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崖柏。2021年,崖柏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一级保护物种。
一
那年,雪宝山脚下的老住户陈宗兵,坐在自家的祖传木板房前,漫不经心地听着杨泉的科普宣传。听着听着,他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杨泉告诉他——
中国崖柏,诞生于三亿年前,十分古老,全世界仅中国独有。1892年,法国人法吉斯在大巴山南麓的雪宝山山脉北坡首次发现崖柏。一百多年后,因为再无科考记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1998年将崖柏列为已灭绝的三种中国特有植物之一。1999年10月,崖柏在重庆被重新发现。
“你看,你家这木板房,从房顶的檩条,到墙体的木板,全都是崖柏做的!实在奢侈得不能再奢侈。”
陈宗兵听完后,目瞪口呆。
他只记得,老一辈的人管这种树就叫柏树。口口相传中,这种柏树重量轻,便于运输,木质韧,从山顶滚到山脚都摔不坏,加之自带香气,防腐防虫,因而成为山里人建房、打家具的首选。
陈宗兵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常常有外地人来到雪宝山砍柏树,据说是要制作手串、根雕,但是被林业人员一批批扭送到了公安机关。
看到陈宗兵一脸紧张,杨泉告诉他:“你家建房那个年代,崖柏还没被列为保护树种,所以不会追究你家的责任。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家都要保护好崖柏。”
陈宗兵若有所思,问杨泉:“你们要不要护林员嘛?长辈砍了树,我来跟着你们一起保护树嘛。”
从此,陈宗兵成为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踏上保护崖柏的漫漫长路。
二
雪宝山位于重庆市开州区境内。
2002年,三十岁的杨泉被林业局领导相中,到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监测员。那时,监测中心只有三个人。第一次随同科考人员进山,他还完全是个外行。跟人家背着外观相同的帐篷,雪夜宿营一晚之后,才发现材质差距巨大:人家的帐篷入夜之后是保暖的,而自己的帐篷底下,积雪被自己的体温“烤”出一个深深的雪窝。
此后多年,他无数次经过手扳岩、王家岩、骆驼峰……踏遍雪宝山的沟沟岭岭,大体弄清楚了,雪宝山上的崖柏分布在海拔一千三百米至两千一百米的区域,分布面积十平方公里左右。
2019年,杨泉已是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他与同事们决定,对保护区所有野生崖柏实行精准管控。有条件的地方,实现每株数字定位;无条件的地方,实现空中视频监控。眼下,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摸清家底,数清全域崖柏数量,并挂牌编号,让每株崖柏获得身份。
北京专家郭泉水,重庆专家刘正宇,保护区全体职工,护林员陈宗兵……被集中编为四个小组,带着方便面等速食品,齐齐奔赴深山老林。
两万多公顷的面积,莽莽的原始森林。
他们没想到,崖柏果真名副其实,绝大多数生在悬崖峭壁上。如要近身,挂上号牌,几乎次次都是千难万险。
他们没想到,进山容易,出山却难,一入森林,常常就是两个多月时间。
他们没想到,生存成为有生以来第一大难题。
缺水怎么办?找木荷。这种植物,点火猛熏,即刻有大颗水珠滴落。除了饮食用水,洗脸水也有了。
缺食物怎么办?野芹菜、马兰蒿、蒲公英、野小蒜、野花椒叶……烫烫就下肚。
遇到毒蛇怎么办?别动,别动,别动!全身吓出冷汗都别动。
摸清家底,历时两年。数次进山,终于获得山上崖柏的第一手资料。
所有队员,茶余饭后,各有自己的谈资。张光箭所在的考察组,第一次在雪宝山上发现黑熊,并与黑熊面对面对峙。王家岩无路,六十九岁的郭泉水教授攀爬上去后,却下不来,是张光箭组织了营救。周李萍说,作为女性,此生第一次野外露营,第一次离星空这么近,第一次明白“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其他各组,也都有自己的故事,或者发现雪宝山成为鹰群迁徙中转站,或者发现了野生红豆杉……
三
“高高山上一树槐,
…………
我望槐花几时开。”
在大山里,杨泉常常会唱这首歌。他说,当初,自己天天盼着崖柏开花。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开花,才可能结果;只有结果,才能有种子繁育。
谁成想,一年过去,花是开了,却没结果;盼着来年花开,花又开了,还是没结果。
翘首期盼,第三年开花之际,杨泉再也坐不住了,他四处筹钱,购进了一台高倍电子显微镜。他要着手研究,弄明白崖柏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他的观察是,崖柏雌雄同株,早则一月开花,迟则三月开花,本身生长在高海拔区域,此时正是冰天雪地,少有昆虫授粉;再则,雄花雌花经常错时开花,授粉难度进一步加大;况且,雌花状如米粒,花蕊还非常害羞地藏在苞叶之中,无形中都增加了授粉的难度。
自然授粉如此艰难,只能人工辅助。天寒地冻之中,杨泉与同事们手持塑胶口袋,罩在崖柏枝上一阵摇晃,待花粉水汽干去,再用棉签蘸粉,一朵一朵为雌花“传递爱情”。
尽管使出绣花功夫,用尽吃奶力气,但收效甚微。
说到稀有植物的种种娇气,杨泉的语气中也透着无奈。
转机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雪宝山野生崖柏大面积结果。杨泉他们视若珍宝,颗粒归仓,居然采集到三十公斤的崖柏种子。
第二年播种季节,他们满心欢喜,仿佛眼前已是一片翠绿,崖柏幼苗已欢快成长。
然而,初次育种,大家毫无经验,为图用水方便,育种地选在了河边。一夜山洪暴发,苗圃被冲走了一半。
懊恼。痛悔。自责。
剩下的一半,越发成为他们的心头肉。
为了安全,为了科研,他们再不敢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幼苗移栽,从海拔六百米到海拔两千余米,他们为幼苗分别相中了三个“家”,让小宝贝们在不同的基地竞相成长。
六年一晃而过。去年,小宝贝长成大宝贝,居然有几株成功“早恋”,并结出果实。
杨泉他们如获至宝,选取其中最饱满的三粒种子,放进了保育箱中。
从种子进入保育箱的那一天开始,基地所有人员昼夜轮班,为三粒种子查温查湿,仿佛是在精心哺育自己的孩子。
两个月后,三株“小宝宝”达到回归自然条件。遗憾的是,回归自然之后,其中两株不幸“夭折”。
硕果仅存者,就是那位“小帅哥”,刚刚长到三厘米。
四
那天,杨泉和同事闲聊中谈到一个困扰已久的话题:自从2012年崖柏大量结果之后,大面积结果的奇迹再没发生。如果崖柏不再结果,还有没有其他繁育方法?
聊着聊着,他们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扦插。理论上讲,就是截取崖柏母株上的新生枝条,经过消毒剂、生根剂浸泡,制作崖柏插穗,然后开展扦插育苗,扦插成活后,移植到苗圃,最后移栽到崖柏原生地。
说干就干。第一年,他们截取野生崖柏枝条进行扦插,但枝条生根寥寥无几。分析原因,多年老树,生命力有限。
第二年,采用2012年那批种子成树的枝条,生长状况也不理想。分析原因,崖柏就是崖柏,可能生根剂、消毒剂、营养剂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扦插植物的配比。
第三年,调整药物配比,自配树苗基质,精细化操作流程,居然成功了!
正是人间四月天,走进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育苗基地,面对大棚苗圃中一畦一畦扦插成活的幼苗,杨泉手舞足蹈,兴奋得难以自持。
他说:“你知道不?截取的那一段,是当年新生的八到十厘米枝条,又细又嫩,做扦插繁育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折断。”
他说:“你知道不?扦插用的轻基质土,配比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其中的腐质层草炭土,国内根本买不到,我们是从国外进口的。”
他说:“你知道不?车间那台轻基质自动灌装机,是我们自己设计、厂家按我们的要求生产出来的。”
他说:“你知道不?这几十亩苗,要回归自然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在他絮絮叨叨如数家珍之中,我能感受到,这人间四月天,充满了爱和希望。
杨泉今年刚好五十岁。
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让崖柏从极度濒危植物中除名。他乐意见到,山山水水处处都有崖柏的身影。
目前,雪宝山挂牌编号的崖柏只有一万株,种子繁育成功的大约三十万株,扦插育苗的希望还生长在基地的试验大棚里。
显然,他的梦想短时间无法实现。
但他充满信心。
他的团队已经壮大。全是大学毕业后汇聚到此的年轻人,全都晒得一身黑,专业学识和工作态度足以让人放心。三十七岁的张光箭,已在深山坚守了十六年;三十七岁的女队员周李萍,已经能够熟练指挥各道工作流程;三十五岁的王雷,为了梦想从江西奔赴到了重庆;三十四岁的朱志强,练就了饿得、累得、做得的“三得”基本功;三十一岁的蔡松才、二十九岁的吴浩,完全适应了保护区一人身兼三职的角色,既是研究员,又是车间工人,还是田间农民……
杨泉神秘地宣布:他们自主研发、自购设备,利用崖柏枝条,成功提取了崖柏精油,价格不菲。相关收入,将极大反哺崖柏繁衍。
真该为他们喝彩!汪 渔
来源: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