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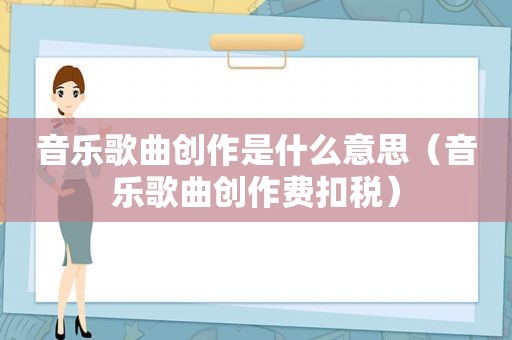
前 记
岁月留韵。一转眼距离上次和著名作曲家徐坚强教授一起谈论音乐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记得2003年中国成都国际现代音乐节暨全国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交流会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在上海音乐学院新作品专场交流会上,作曲家徐坚强的一首民族器乐合奏《日环蚀》给到场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回到上海之后,笔者便采访了作曲家徐坚强教授,后来访谈录《<日环蚀>与他的作者徐坚强》刊登在了当年的《人民音乐》。时过二十年,再于2022年上海当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听到徐老师的《大开门》,让人耳目一新。
1984年7月作曲家徐坚强教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曾先后师从王久芳教授、顾冠仁教授、沈传薪教授和胡登跳教授,同年分到北京东方歌舞团创作室工作。1989年底,调回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任教,在职期间师从于著名作曲家何训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现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合唱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来,其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日环蚀》曾荣获世界华人民乐作品比赛的唯一银奖(金奖空缺);歌曲《你是风》荣获“亚洲音乐节原创歌曲十大金曲奖”;无伴奏合唱《运杨柳的骆驼》荣获中国“金钟奖”;2005年丝弦五重奏《嚣板》荣获全国文华杯金奖;声乐作品《归园田居》荣获教育部“中华诵,古辞新韵”作品大赛一等奖。可谓是硕果累累。如今徐坚强教授已从青年作曲家迈入更为成熟的创作阶段,笔者循着时间的痕迹采访了徐坚强教授,听听他对音乐创作的坚守和创造。
举一反百:徐老师,好久不见,久违了。这次音乐会听到您的新作品《大开门》,距离上次听您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日环蚀》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20年时间,真是时间如梭啊!从《日环食》到《大开门》,您的创作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徐坚强:时间过得真是快啊,不知道时间都去哪了?可能都跑到音符中去了。从《日环蚀》到《大开门》时间跨度二十多年了!我的变化从大方向来说没有变!那就是一直努力做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最佳结合点!很多人都在找这个“点”,但有的做得好一点,有的做着走着又会偏一点。这个大方向懂的人不少,但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对我来说,这个大方向永远都不会变,也不需要变。只是在做的时候会有小变化的。比如:我现在的创作理念是追求“简单的不简单,不简单的简单”。我自己创建了一些作曲法,“肿瘤作曲法”、“旧城区改造作曲法”。《大开门》是用“旧城区改造法”来进行创作的。我的室内乐《ZHI》是用“肿瘤作曲法”来创作的。这两种作曲法虽然名称上我还未想好用更“学术”化的词,但我也觉得从字面上更能让人一目了然!
举一反百:在《日环蚀》中,您主要是将小时候所熟悉的民乐及其演奏技法加以发挥,力求遵循“借景抒情”这一中国传统美学原则。这部作品在表面上是运用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的音色来表现宇宙变 化的这一瞬间,内涵是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为一体的这样一个主 题。 整部作品非常注重弦乐的运用,由慢到快,也结合戏曲里的慢 板、 快板、散板,整个乐曲的结构也就是一部戏。在《大开门》的创作中您选用了唢呐这件民族乐器来做新的探索,似乎寓意着人生之门,与其说《日环蚀》是思考天地,《大开门》则是思考人生、生命。您在这首《大开门》的创作中选用唢呐来表现这样的主题有什么样的思考吗?您是想通过《大开门》来做新的探索吗?
徐坚强:我创作《大开门》大量运用的戏曲音调是有旋律的。我就是要在一支传统唢呐只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内,把唢呐的各种情绪的旋律发挥到极致!演奏这样的作品也多亏了青年唢呐演奏家刘雯雯老师的精湛演技,这是给作品加分了的!这部作品的曲式结构我没有按西方创作中的任何一种模式。我就是按一个“顺”字,按快快慢慢的情绪顺着走下去。
要说创作手法,我是用了自己创建的“旧城区改造法”。即,将唢呐旋律作为一个“旧城区”,管弦乐队对其进行合理的“破坏和改造”。在和声上很注重各种色彩。这次闭幕音乐会上的演出,我由原来四支中音唢呐扩大到了九支唢呐的助奏。一开始九支中音唢呐每支吹奏一个音、九支唢呐九个不同的音,而且用不同的演奏法形成长音铺垫式的背景音,现场效果非常好!在独奏的高音唢呐华彩段中,我赋予了九支中音唢呐即兴式的助奏,达到了很热闹的艺术效果!我的基本立意就是想运用中国戏曲“大开门”的曲牌作曲名及某些音调作创作素材来表现这样的场景:打开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门;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瞻望中国未来发展的幸福大门!
我从来不给自己定位或定框框。我一直觉得一个作曲家一定要充满好奇心。有了好奇心才能驱使我写这、写那。我喜欢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全能型的作曲爱好者。所以中西管弦乐作品我都写了不少,歌剧写了两部,芭蕾舞剧一部,歌曲写了不少,平时还做电子音乐,合唱作品写了很多。
创作合唱作品是因为我看到了合唱作品在当下社会的需求量很大,因为一个作品获了奖就“一个不小心”来了很多委约创作,这样一来也就“不可推辞”了。我还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我个人无伴奏合唱音乐会!后来也被瑞典国家室内合唱团聘请为作曲,还在瑞典首都开了合唱作品音乐会。这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创作历史上还是不多的,目前应该算是唯一的。我为瑞典创作了无伴奏合唱实时微电影《蓝柳》创作音乐(实时进行配乐),这在中国应该也是唯一的。该乐谱已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这在上音院也是唯一的。
举一反百:2015年您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个人无伴奏合唱音乐会这个我是知道的,本来也是被您邀请前去聆听的,后来因为公务没有赶上,据说当时反响很大,很成功。迄今为止,上音院也是唯一的一件事。这次您创作《大开门》选用唢呐作为独奏乐器,唢呐一直作为一件表现大喜大悲的乐器,为什么选用唢呐来表现你的音乐探索?
徐坚强:我为何选用唢呐来创作一部协奏曲,是因为我曾在戏曲团里工作过十年,对唢呐非常熟悉。我觉得唢呐是一件很有民间音乐特色的乐器,它的表现力是很强,也很丰富。青年唢呐演奏家刘雯雯老师曾在我的歌剧《汤显祖》里有一段唢呐与管弦乐队的演奏,观众反响很强烈。她细腻入微的演奏感染了我,我萌发了要为刘雯雯老师创作一部大作品。巧的是,刘雯雯老师也同时先主动邀请我为她写唢呐协奏曲!我一直认为,一个作曲家就是要为像刘雯雯老师这样优秀的演奏家量身定做地写作品,就会容易产生成功率!我是喜欢用一支传统唢呐来写的,而且在一支高音唢呐只有两个八度的有限音域中,要写出彩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就是喜欢挑战自己!
另外,传统唢呐具有各种滑音效果,改良唢呐是做不出来的。为了加强音乐气氛,我还用了九支中音唢呐来助奏,实际效果证明是很不错的。唢呐的确是中国民间团体、尤其是农村广大村民非常熟悉和最常用的乐器之一。它高亢激昂的声音有,也能奏出委婉抒情的旋律,唢呐的确是中国民间音乐特色很鲜明的一种音乐符号,这是可以肯定的!
举一反百:听了您的想法,我觉得您讲的很有见地。从中外音乐历史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凡是作曲家参与的乐器,往往正是作曲家的作品推动了一件乐器的成熟和技术提高。中国乐器留下的作品都很有限,这方面作曲家其实可以做更多探索,您也为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带了一个好头啊。徐老师,您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擅长旋律写作的作曲家,我记得您的一首《上海叫卖小调》还入选了上海音乐教材;前不久,您创作的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歌《地球是个美丽的圆》也被教育部审定入选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您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呢?看您近年来创作了不少合唱作品,您选择合唱作为您的创作方向之一有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吗?
徐坚强:我是从来不给自己定框架、定类的。我的好奇心很强,兴趣爱好很广。我的创作几乎涉足了音乐的各种类型及风格,管弦乐队、民乐队、流行音乐等乐队,我都较为熟悉。歌剧(有两部)、交响乐曲、芭蕾舞剧、各种室内乐、合唱音乐和流行歌曲等我都写过了。至于旋律,我认为旋律仍是音乐作品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
一个作曲家必须要学会写出好听的旋律,但我也写过不少实验性的音乐作品,比如《为三个踏板而作》的钢琴独奏曲,用手指甲“抠出来”的钢琴曲;还写过《废品系列》和《生活日用品系列》等音乐作品。两部歌剧,第一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无调性的;《汤显祖》是必须要有旋律的,因为我的委约创作很多,国内委约大部分是命题之作,必须要有好听的旋律。国外的委约作品相对自由一些。比如,受国内某合唱团委约创作的无伴奏合唱《归园田居》等就必须要有好听的旋律,该作品在全国各地传唱率很高。而我受瑞典国家室内合唱团委约创作的微电影《蓝柳》(无伴奏合唱)则是无调性的旋律风格。一句话来说:我的创作要有好听的旋律,这是委约方的要求,也是我的追求;实验性的创作,也是我的兴趣爱好。
举一反百:记得多年前采访您,您曾说了这样八个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您的创作是不是总有这种感觉,您在未来的创作中还是在合唱与民族乐器方面做进一步的创新融合吗?
徐坚强:意料之外并不是目的,也并非简单的标新立异,一部成功的作品就是作曲家智慧和创意的最佳发挥。现在很多创作有很多误 区,将创作的重点偏离了音乐的本质。一个作曲家要想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一定要用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即要营造自己的辨识度很高的音乐符号,再进一步结合本民族的丰富音乐资源,并对传统音乐素材进行新的诠释。至于未来的创作,主要还是看委约的数量及要求而定。
目前我刚完成一部受委约的中阮与管弦乐队的大作品《星空》(预计2023年1月份演出)。2022年11月8日在无锡刚刚首演了受无锡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命题之作《梅之韵》。2022年6月5日在杭州也首演了受天台市 *** 委约创作的大型合唱情景剧《盛世和合》。目前正在准备创作的是受昆山市某中学委约的大型合唱组曲《顾言武》,这部作品将采用昆曲风格,整个编制和题目还在和委托方进一步商量而定。
举一反百:您目前除了委约作品外,自己有自己的创作计划吗?
徐坚强:除了委约作品创作之外,我自己一直挤时间在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汤显祖》。另外还在做一些有趣的实验音乐,实验音乐主要用于教学,用来启发学生而用。
举一反百:我们经常看到西方音乐家在自己创作生命生涯中,往往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域创作出不少系列作品,您有这样的思考吗?有自己的创作方向吗?您对自己的创作人生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徐坚强:我对自己的创作人生有自己的追求,在创作方面不管有旋律还是无旋律,我都会尽量创作出能留得下来的各种类型的音乐作品。我只凭自己的好奇心来写作品(包括各种委约创作)。当然,还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行!
举一反百:能谈谈您对近年来音乐创作界出现的新现象吗?
徐坚强:近年来,我国的音乐创作很繁荣,但佳作甚少,雷同的、千人一面的作品较多。我在创作中尽量考虑自己创作的作品能否留得下来。在当下不知其他作曲家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尤其是青年学生们,他们创作的作品有的自认为很现代,很时尚,其实,其中的一些“现代作曲技法”,别人早就都用过了。如果他们不考虑作品是否能留得下来,那么该作品有可能就会昙花一现、一次性演出现象很多。有些作品虽然获了国际大奖,但后来却再也无人问津。这也是一种看似成功,其实是很遗憾的“成功”,而且一个作品留不下来,那么作曲家就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未来音乐该如何写,其实是不可预知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未来音乐该怎么写,就不好玩了。但是,有一点我是头脑清醒的,也是一直在坚持的!那就是,未来音乐不管往前走还是往回走,我都会尽量地做到每写一个作品能留得下来!关于未来音乐之路,我有四种走法:往前走,往回走,原地走,来回走,这四种走法没有好坏之分,因人而宜,任何一种路走得好都是好的!
举一反百:一个作曲家其实是脱离不了本国土壤的。只有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努力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挖掘、继承,将管弦乐、现代民乐、流行音乐等各种风格进行融合,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来,我们静静地期待着您的新作,谢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徐坚强:应该的,也谢谢您的一直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