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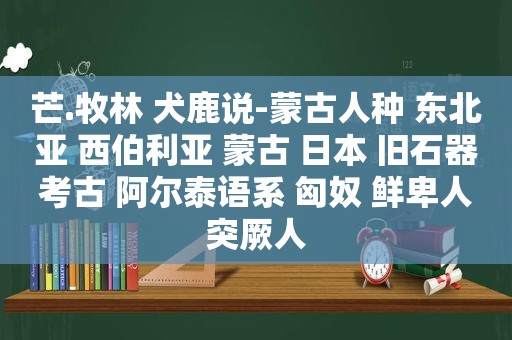
就匈奴到底属于哪类人种的问题,各国学者得划分依据又是什么? 就语言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匈奴语属阿尔泰语系。匈奴语言从它与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的关系看,从它所处的时代条件看,它是属于一种在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规范化以前的一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阿尔泰原语,即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尚未分明时期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又包含着其他相近语族的成分。
就体质而言,
⑴在前苏联,学者们主要对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塔拉河流域的肯特尔匈奴人墓葬、天山和阿莱地区的匈奴人墓葬、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匈奴人墓葬进行了大量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⑵20世纪60年代在蒙古国的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匈牙利、蒙古的人类学家还曾经对一批属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骨骼形态等方面的测验。测验结果为:在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可归入古西伯利亚类型;在外贝加尔湖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存在少量欧洲人种混血,也可能有少量远东人种混血。
⑶我国考古工作者和人类学工作者也就有匈奴人种的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对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葬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的东汉匈奴古墓中出土的人类骨骼进行测量。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人骨只是一具颅盖骨和面部皆残缺的头骨,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的东汉匈奴古墓由于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一枚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铜印,因而被认定是具有明确族属证据的匈奴墓葬,具有很高的参照性。
据潘其风、韩康信先生的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头骨不很长,顶结节附近的似近额宽很宽,估计为短颅类型。鼻指数在中鼻型上限,具有很高的面,眶高则低,属低眶型。鼻颧角所示上面部扁平度也大,鼻骨突度低。这样的综合特征比较接近北亚蒙古人种型。
青海大通匈奴墓葬的人骨是3具头骨(1男2女)。这三具头骨的共同特征是,具有较大的颅宽,颧宽小于颅宽,颅型扁短,同时有较大的上面高和很大的眶高(全呈眶高型),矢状方向面突度为中颌型。个体间存在一些变异。其综合特征与近代蒙古族接近一些,可能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更为密切,没有大人种的混血现象。
由于青海大通匈奴墓中人骨的族属非常明确,因此,武沐先生认为,匈奴人种最初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或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种。其北部和西段,有欧洲人种的混合,这和中国史料的记载基本相符,也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分布的特征基本吻合。
=========================
匈奴强盛时期,控地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在这一广阔的危围内,陆续发现有关匈奴的文化遗存。目前发现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即苏联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其中外贝加尔地区匈奴遗存的发掘工作起步最早,1896一1902年间,苏联学者塔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吉达河、色楞格河、奇科依河和希尔卡河流域发现有近百座匈奴墓。在这些墓地中,规模最大的是恰克图以北23公里的伊里莫瓦(发掘三十三座“木椁墓”)和吉达河左岸的德列斯堆(发掘二十六座“木棺墓”)两处墓地。发掘者认为“木椁墓”和“木棺墓”属于不同时期,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并推测前者与匈奴有关,后者则与吉尔吉斯或通古斯有关。不管当时人们对这类遗存的认识如何,从此却揭开了匈奴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序幕。
1912年,一位俄国探金者因偶然的机会,在今蒙古中央省诺音乌拉发现了一座不寻常的古墓葬,引起了苏联学者的关注。1924一1925年间,科兹洛夫等人在此又发掘八座大墓和四座普通墓。诺音乌拉匈奴墓地的发掘,将匈奴考古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诺音乌拉大型贵族墓葬均被盗掘,然而墓葬结构基本完整,并出上了丰富的随葬品,为研究匈奴人的埋推制度、文化面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特别引人注目的是,5号墓(希姆科夫墓)和6号墓均出土带有“建平五年”等明确纪年的漆耳杯,为确定诺音乌拉墓地的年代和族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关于诺音乌拉墓地的发掘资料,由苏联学者作了初步报道。随后,特列维尔用俄文和匈牙利文对诺音乌拉墓地的发掘作过详细描述。但到目前为止,诺音乌拉匈奴墓的发掘资料尚未系统整理和发表,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诺音乌拉匈奴墓的发掘,引起苏联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发现先前发掘的伊里莫瓦和德列斯堆等墓地,无论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品,都与诺音乌拉墓地非常相似,促使苏联考古学家对外贝加尔地区的类似遗存给予格外关注。1928——1929年间,以索斯诺夫斯基为首的布利亚特蒙古考古队在伊里莫瓦谷地又发掘十一座匈奴墓,其中包括一座有墓道的大墓。同时,在乌兰乌德附近发掘了伊沃尔加古城,这是继匈奴墓葬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因遗址内出土类似于诺音乌拉和伊里莫瓦墓地的器物,发掘者确定其为匈奴城址。此外,1925年杰别茨在奇科依河左岸发掘都连村遗址,出土的遗物与德列斯堆墓地出土随葬品类似。
外贝加尔匈奴遗存的发掘工作停顿二十年之后,自1949年以来,布利亚特蒙古考古队重新发掘伊沃尔加古城,发现大量的房址、作坊等。1956年发掘同古城相关的墓地,直至1970年先后发掘二一六座墓葬。1957一1958年间,在恰克图以北25公里的切列姆霍夫墓地发掘二座匈奴墓,1965一1966年在科诺瓦洛夫领导下又发掘十八座。1980一1983年间,布利亚特考古学家又发现新的匈奴遗存:乌兰乌德以南60公里的巴尔盖和距德列斯堆墓地20公里的英霍尔居址和墓地,以及图格内河畔巴彦哈拉山墓地。
蒙古境内匈奴遗存的发掘,如前所述,始于1924年。稍后,1926一1927年间,蒙古学者希姆科夫在诺音乌拉发掘两座大型贵族墓葬,其中5号墓(希姆科夫墓)出土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带有汉字铭文的漆耳杯。1954一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在中央省和后杭爱省发掘了匈奴墓葬。在诺音乌拉又发掘一座大墓、四座普通墓和八个祭祀坑。1956一1957年,道尔吉苏荣在呼尼河流域发现三百多座匈奴墓,并在高勒毛都地方发掘二十六座普通匈奴墓。六十年代,蒙古、匈牙利和苏联考古学家先后在乌兰巴托郊区伯勒希、科布多省芒汗苏木及呼尼河流域发掘匈奴墓。1969年在达尔汗山附近发掘六座普通匈奴墓。七十年代,在后杭爱省呼塔格乌拉、苏赫巴特尔省小乌勒古特、前杭爱省特布希乌拉等地发掘匈奴墓葬。此外,1952和1956年,蒙古考古学家普日莱发现四座匈奴古城。1972年,苏蒙历史文化考察队在中央省、肯特省又发现三座匈奴古城,蒙古考古学家纳万在南戈壁省巴彦布拉克也发现一座匈奴古城。
中国境内匈奴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五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才开始寻找有关匈奴的文化遗存,相继发现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和扎赉诺尔三处墓地。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的同行们对这三处墓地的族属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属匈奴,有人认为属鲜卑,至于西岔沟墓地还有乌桓说和扶余说。鉴于人们对这三处墓地的族属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故本文暂不作为匈奴文化遗存来讨论。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属于两个不同阶段的匈奴遗存。第一阶段的遗存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关于这一阶段的遗存将在第四节中详加讨论;第二阶段的遗存相当于秦汉时期,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存有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补洞沟、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和倒墩子、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140号墓、铜川县枣庙等墓地,共发掘袋葬五十三座。
总之,苏联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匈奴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已进行近一个世纪,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发现,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已出版数目可观的研究成果。在已发表的论著中,除了大量报道资料及就个别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著述外,也有一些综合研究的著作。如苏联学者鲁金科的《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科诺瓦洛夫的《外贝加尔的匈奴》、达维多娃的《伊沃尔加遗迹群——外贝加尔的匈奴遗存》;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遗物》等。国内有关匈奴遗存的论著还不多,只有田广金的《匈奴墓葬的类型和年代》和《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郭素新的《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以及拙作《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等论文。
综观以上各家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匈奴考古遗存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涉及到有关匈奴史上的一些重要课题,诸如匈奴定居及农业、手工业、文化艺术、生活习俗、丧葬制度、族源及其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单凭有限的文献史料是很不够的,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当然,国内外学者在利用考古资料论述这些问题时,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匈奴考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尚望同仁批评指正。
二、分布、年代与文化特征
如前所述,匈奴遗存包括墓葬和城址,主要分布于苏联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这里所说的匈奴遗存是指秦汉时期、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墓葬和城址,至于前匈奴文化或有争议的有关遗存没有包括在内。
关于匈奴城址的资料将在第三节中讨论,这里着重分析匈奴墓葬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在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二十处墓地,约九百座墓葬,已发掘三七七座;蒙古境内发现三十处墓地,约二千座墓葬,其中已发掘的约五百座;中国境内发现匈奴墓地七处,已发掘五十三座墓葬(附表一)。表中所列仅限于著述的已发掘的匈奴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外贝加尔的伊里莫瓦、德列斯堆、切列姆霍夫和伊沃尔加墓地,蒙古境内的诺音乌拉、高勒毛都、特布希乌拉和达尔汗山墓地,中国北方的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墓地。以上发现,基本反映了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的概貌。
匈奴墓葬的形制,大体可划分为八种类型。
(一)长方形竖穴土坑,无葬具,地面无任何标志。西沟畔、补洞沟墓地和客省庄140号墓可作为代表。年代为西汉初至东汉初。以补洞构3号墓为例,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人骨右侧发现长铁剑,腰部围一圈铁带饰,左侧有铁刀、铁链等(图一)。
(二)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葬具,地面无任何标志。倒墩子墓地可作为代表,年代为西汉中晚期。以19号墓为例,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北壁有龛,内置陶罐。随葬品有铜带饰、铁刀、五铢钱、海贝等(图二)。
(三)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葬具,地面有圆形石堆。伊里莫瓦、切列姆霍夫和达尔汗山墓地部分墓葬可作为代表。年代为公元前一至公元一世纪。以切列姆霍夫39号墓为例,地面有圆形石堆、葬具为木棺,单人葬。随葬品有陶罐、装饰品、铁刀等,刀背上有铭文,因锈蚀无法释读。
(四)长方形竖穴土坑,有棺有椁,地面有圆形石堆。伊里莫瓦、切列姆霍夫和达尔汗山墓地部分墓葬可作为代表。年代为公元前一至公元一世纪。以伊里莫瓦58号墓为例,地面有圆形石堆。头端棺椁之间置陶罐,并随葬铁刀、锥、带扣和牌饰、以及绿松石坠饰和漆耳杯。漆耳杯上有四对凤凰图案和汉字铭文(图三)。
(五)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葬具,坑壁下部用不规则石块围砌。诺音乌拉、德列斯堆、伊沃尔加和高勒毛都墓地部分墓葬为代表。年代为公元前二至公元一世纪。以德列斯堆32号墓为例,坑壁围以石块,填土中亦有石块。随葬陶罐、铜铃、带扣和环、铁刀、带扣和马衔,以及五铢钱、丝织品、海贝等(图四)。
(六)长方形竖穴墓道,偏洞室,木棺葬具。以倒墩子墓地部分墓葬为代表。年代为西汉中晚期。以13号墓为例,西壁掏洞,内置木棺。墓道和墓室间有一排小柱洞。单人葬,头向北。随葬品有金耳环、铜带饰、石牌饰、五铢钱、海贝等。
(七)方形竖穴土坑,有墓道,有内外椁,内撑中置木棺,地面有封土。诺音乌拉、伊里莫瓦大型墓葬可作为代表。年代为公元前一至公元一世纪。以诺音乌拉24号墓为例,封土为14x15米,墓道封土为12x5米。墓扩为13x12x9米。墓底铺两根方木,其上排列十五根圆木。外椁3x4.4x1.8米,顶上盖十八根圆木。内椁3x1.7x.1.22米。棺2.16x0.77x0.85米。随葬品有丝织品衣服、发囊、鞋垫、袋子和小旗、龙纹玉饰、案、残漆器等(图五)。
(八) 砖室墓,分前后室,有墓道和棺椁葬具,地面有封土。以上孙家寨墓葬为代表。年代为东汉晚期。封土呈圆形,墓室穹窿顶,斜坡式墓道。墓圹口横置一排二十八根圆木。随葬品有铜镜、五铢钱、“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及仓、井、灶等陶明器(图六)。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结构的复杂程度和随葬品的多寡有明显区别,这究竟是反映年代早晚或地域的差别,还是反映匈奴社会成员的分化及拥有财富的差异。我认为这几种因素都应当考虑进去,同时还要考虑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首先,从年代上说,中国境内西沟畔、倒墩子、客省庄140号墓和枣庙墓,外贝加尔德列斯堆和伊沃尔加墓地的年代偏早。这些墓葬的形制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无葬具,有的以木棺为葬具,所不同的是漠北几处墓地地面有石堆,墓圹四周用不规则的石块围砌,个别墓葬有棺有椁。据出土遗物分析,西沟畔、客省庄和枣庙匈奴墓的年代为西汉前期;倒墩子、伊沃尔加和德列斯堆墓地都出土西汉五铢钱、伊沃尔加古城出土西汉四乳草叶纹镜。德列斯堆墓地出土的铜铃、铜环、透雕铜环、双马互斗纹和鹰虎夺羊纹透雕铜带饰及伊沃尔加墓地出土的龙虎相斗纹透雕铜带饰等,与倒墩子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故这几批匈奴墓地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或稍晚。
中国境内补洞沟,外贝加尔伊里莫瓦、苏吉河口和切列姆霍夫墓地,蒙古诺音乌拉、达尔汗山和高勒毛都墓地的年代偏晚。这一时期除上述结构的墓葬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有棺有椁及三重墓室有墓道的大型墓葬。补洞沟和切列姆霍夫墓地出土西汉末至东汉初的规矩镜,诺音乌拉、高勒毛都、苏吉河口和伊里莫瓦墓地出土几何纹规矩镜、四乳四璃纹镜、四乳四神镜、日光连弧纹镜、昭明连弧纹镜等,都是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铜镜。诺音乌拉5号墓(希姆科夫墓)和6号墓均出土“建平五年”漆耳杯,伊里莫瓦墓地也出土相同的漆耳杯。“建平五年”即公元前2年。由此可见,这几批墓地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末至东汉前期。
其次,从地域上说,外贝加尔和蒙占境内匈奴墓的结构,与中国北方匈奴墓有所不同。外贝加尔和蒙古匈奴墓的地面往往有石堆,有些墓圹四周围以石块,有的墓底用石块奠基。中国境内的匈奴墓,除上孙家寨墓地面有封土外,其余匈奴墓地面均无任河标志,墓穴内未见围砌石块的现象。可见大漠南北匈奴墓的结构有所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将在第四节中加以讨论。
第三,匈奴社会的分化及悬殊的贫富差异,在墓葬结构和随葬品方面得到充分的反映。像诺音乌拉和伊里莫瓦墓地,除有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外,同时存在着结构简单,随葬品贫乏的普通墓葬。这种现象出现于同一墓地,生动的展示出匈奴社会内部已发生深刻的分化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阶层。结构复杂的大型墓葬,显然属于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及其近亲所有。
除此之外,造成匈奴墓葬结构的多样化,除匈奴固有的葬俗外,不能不考虑到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像诺音乌拉和伊里莫瓦大型贵族墓葬,其三重墓室及斜坡式墓道的结构,显然是仿效汉朝上层贵族的埋葬制度。倒墩子墓地偏洞室墓也非匈奴墓葬的传统结构,而是吸收了月氏等古老民族的文化因素。
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的结构虽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随葬品的种类和特征却趋于一致,无论青铜器、铁器和陶器,还是装饰艺术都表现出明显的共性。陶器以罐为主,纹饰以弦纹和波折纹为主要特征。青铜器有刀、镞、铃、环、带扣和管状饰,铁器有衔、带扣、刀、镞等,装饰品有铜带饰、透雕铜环、石牌饰、各种质料的珠子、海贝等(图七、八)。装饰品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各种动物、人物或几何纹样的带饰,绝大部分为铜质,少量为金质,有些铜带饰鎏金。这些带饰大部分为透雕,少量为浮雕。形制和花纹类似的带饰,在南起长安客省庄、同心倒墩子墓地,北到外贝加尔伊沃尔加、德列斯堆墓地均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饰往往成对发现,图案丰富多彩,仅从发掘品看就有双马、双牛、双羊、双驼、双龙、双马互斗、龙虎相斗、龟龙相斗、鹰虎夺羊、双人跤斗、佩剑武士、武七骑马捉俘等(图九)。至于传世品中则有多种题材的带饰,构成匈奴特有的造型艺术。
这种独具风格的造型艺术对邻近各族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北方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辽宁西丰县西岔沟等非匈奴人墓葬,以及苏联南西伯利亚塔加尔文化贴西期墓葬中均有发现,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也有大量发现。匈奴人特有的另一种装饰品是透雕铜环,中国境内的客省庄140号墓、倒墩子1、13、15号墓和外贝加尔的德列斯堆10、38号墓均出土透雕铜环。这种透雕铜环往往成对发现,见于人骨腰部或腰部以下,倒墩子13、15号墓、德列斯堆38号墓出土的铜环上部均缀以串珠、成流苏状饰物,显然是悬于腰带上作为装饰。
三、城郭与农业、手工业
人们提起匈奴族,自然同“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司马迁曾描绘过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畜群的主要品种为马、牛、羊,另有奇畜橐驰、驴、驘等。匈奴人的衣食住行主要来源于畜牧业。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匈奴为游牧民族、从事游牧畜牧业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但匈奴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给研究者以新的启示,有些学者根据考古资料提出匈奴人建有定居点,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冒顿单于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公元前209年,他杀父自立为单于,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犂之国,结束了北方各部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局面。匈奴统治者为有效的管辖这一广大的地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建立三个行政区划:中央地区,包括色楞格河、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北至外贝加尔,南到云中、代郡,这是匈奴的大本营,设有单于庭,由单于直接管辖;西部称右地,包括河西走廊、西域诸国,由右贤王管辖;东部称左地,接涉貉、朝鲜,由左贤王管辖。随着匈奴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联系的加强,昔日分散的游牧经济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定居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关于在匈奴统治的范围内,特别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中央地区,出现有定居点或设防城郭的问题,在中国汉文献史料中有几条记载。《史记·匈奴列传》:“五月,大会茏城”;公元前129年,卫青出塞击匈奴“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汉书·严安传》:“深入匈奴,燔其龙城”。《汉书·韩王信传》:“信亡人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日颓当”。《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公元前119年,汉军“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前将军赵信于公元前123年降匈奴,四年后卫青率汉军至赵信城,可见这座设防的城堡当为赵信所建。
文献记载中多次提到茏城,即匈奴重要的行政中心。问题在于,茏城的规模和建筑是否与一般概念中的都城一样,由高大城墙围绕的宏伟宫殿,是很值得怀疑的。匈奴茏城,原先在漠南,秦以后在漠北。但至今在蒙古境内尚未发现具有都城规模的城址。所谓茏城,很可能是由“旃帐”组成的。据文献记载,匈奴人住穹庐(即毡制帐幕),乌维单于时“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史记·匈奴列传》)。后来,汉使杨信去匈奴,“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史记·匈奴列传》)。由此可见,匈奴单于的“宫室”即是旃帐。由这种旃帐构成的特殊的城市,在后来的游牧民族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在苏联西伯利亚就曾发现十二至十七世纪的帐幕古城遗址。由此推测,匈奴茏城极有可能就是由旃帐构成的聚居点。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的实物资料,还有待证实。
匈奴境内出现典型的城郭,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蒙古境内发现匈奴城址十几座,分布于中央省、后杭爱省、布尔根省、肯特省、乔巴山省及东方省。这些城址规模不大,实际上都是些设防的小城堡。如中央省孟根莫利苏木特列勒金古城,呈正方形,每边长235米。围墙外有壕沟,四面有栅门。城内有大小建筑基址数处,发现瓦当、方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图一O);中央省尼拉咙苏木高瓦道布古城,近方形,南北长367米,东西宽360米。南北墙有栅门,城中央有一大型建筑台基(56x45x3米)。发现大量筒瓦、板瓦、瓦当、方砖及柱础石等。其他如中央省孟根莫利苏木布和方台古城,肯特省吉尔戈勒特汗苏木成赫林赫鲁姆古城、南戈壁省诺姆根苏木呼勒特道布古城等,其规模和布局都与上述古城大同小异。从这些城址的结构和规模看,似乎更具军事性质。城址内普遍发现汉式板瓦、筒瓦、卷云纹瓦当和陶器等(图一一),为断定城址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城址以伊沃尔加古城为代表。该城址位于乌兰乌德西南16公里处。城址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一216米。三面有设防,由四条围墙和三条壕沟组成(图一二)。城内发掘房址五十一座,以及窖穴、炼铁炉等。出土遗物与匈奴墓相同,除大量陶器外,有铁犁铧、铲头、锄、镰、刀、锥、镞和甲片,铜矛、镞、牌饰和各种带扣,以及汉代铜镜、弓饵、骨镳等。城址附近还发现一小城址,面积不大,可能是围栏类遗迹,表明这里的居民不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同时也经营畜牧业。外贝加尔地区另一处重要的定居点是恰克图以东35公里的都连村遗址,该遗址面积较大,发现大量陶器、青铜器及房屋、窖穴遗迹。陶器以泥质灰陶罐为主,纹饰以弦纹和波折纹最为典型。青铜器有马纹牌饰、牛头形饰、三叶锨、带扣等。这里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等,与伊沃尔加古城和匈奴墓地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无疑是匈奴居址。
关于匈奴城郭和定居点由何人修筑和使用的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种种迹象表明,匈奴居民的成分是复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匈奴人。在匈奴城郭和定居点,除居住着匈奴人外,还有被匈奴人征服的当地居民及被匈奴人俘获或亡人匈奴的 *** 、西域人及鲜卑、乌桓人等。外贝加尔地区原本不属于匈奴所有,自冒顿单于之后,匈奴人占据了这一地区。这里原有的居民很早以来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很多 *** 来到这里,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83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尽管卫律的建议未能实现,后来以“胡人不能守城”为由停止修建。但卫律的建议是有一定道哩的,因为匈奴境内有所谓“秦人”,即秦时亡人匈奴者及其后代。到了汉代,为数更多的 *** 亡入匈奴。公元前33年,候应曾说过:“边人奴婢愁去,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汉书·匈奴传》)以至无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与匈奴签约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缓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汉书·匈奴传》)。可见 *** 逃往匈奴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汉朝廷不得不明令禁止。此外,也有不少汉朝高级将领和谋士降匈奴,也有通过“和亲”随公主到匈奴境内安家落户的。毫无疑问,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高,深得匈奴单于的宠信,他们完全有可能按原有的习惯建造房舍,过着定居生活。苏联哈卡斯自治共和国阿巴坎附近的中国式宫殿就是个最有力的证明。
这座宫殿位于阿巴坎市西南12公里处,1941年发掘。中央大殿由东西两殿组成,均由夯土筑成,中间隔墙厚约1.8米,有门相通。南墙和东墙厚约2米,墙壁和地面抹有草泥土。房内地下铺设石板砌筑的暖气管道。殿址内发现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板瓦、瓦当、铺首等(图一三),瓦当上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汉字铭文。这座宫殿,无论从建筑形式,还是从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来看,都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其建造者和使用者显然是地位不凡的 *** 。苏联考古学家推测其为李陵的宫殿,而有的国内学者考证其为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宅弟。不管宫殿的主人是谁,但建造和使用者为 *** 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是说,在匈奴统治的地域内,具有特殊身份的 *** 可以建造宫室,过着与游牧匈奴人完全不同的定居生活。当然,对匈奴境内的大部分普通 *** 来说,他们只能居住在城郭和定居点内,依他们各自的特长,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随着匈奴境内城郭常居之处的出现,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找式一些线索。《史记·卫将军列传》:“逐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汉书·匈奴传》:漠北“连雨雪数日,谷稼不孰。”这两条记载说明匈奴本地确有耕田之业,这一点也得到考古发现的印证。
伊沃尔加古城内发现数量可观的农业工具,包括犁铧、铲头、锄、镰等(图一四)。见于14号房址地面的犁铧保存最好,长11、宽8、厚3.5厘米。类似的犁铧,在外贝加尔地区已发现数十件,大部分出自都连村附近遗址。这些犁铧的发现,说明当时己有牲畜牵引的木犁耕作,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此外,伊里莫瓦墓地40、58和123号墓,伊沃尔加墓地40、41和48号墓、切列姆霍夫墓地40号墓、达尔汗山墓地2和4号墓、特布希乌拉墓地20号墓,以及诺音乌拉两座大墓内均发现粮食作物的遗留。伊沃尔加古城还出土石磨盘和镰刀。匈奴陶器中流行一种近底部穿孔的陶器,显然是储存粮食的器具。不难看出,匈奴境内确实有一部分居民从事农耕,以补充畜牧业之不足。
我们说匈奴本土有定居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是说农业已成为匈奴人的主要经济部门,也不可能满足整个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根据文献记载,匈奴经常从中原地区输入大量的粮食,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史记·匈奴列传》:孝文帝时“故诏吏遗单于秫蘗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汉书·匈奴传》:公元前89年,狐鹿姑单于遗汉书日:“今欲与汉闓大关,取汉女分妻,岁给遗我蘗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公元前48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毂二万斛以给焉。”这些记载说明汉朝廷经常赠予匈奴大量的粮食。至于匈奴人通过民间渠道从汉地获得的粮食其数量还会更多。因此,考察匈奴经济时,既不能否认匈奴境内有农耕的存在,也不能夸大农业在匈奴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不能由此得出匈奴经济为半农半牧的结论”。实际上,游牧畜牧业仍然是匈奴社会经济的基础。匈奴墓葬中普遍忘性,说明家畜仍然是匈奴家庭的主要财富,如伊里莫瓦墓地3一5、8、9、17、19一22、25一28、30、31、33、45、48、50、52、53、58号墓,切列姆霍夫墓地40、48、60、61号墓,达尔汗山墓地4、5号墓,以及倒墩子墓地6、7、10、13、15号墓均发现殉牲。伊里莫瓦墓地52号墓殉有十九具家畜头骨及趾骨,倒墩子墓地6号墓殉有十五具牛羊头骨及趾骨。殉牲种类以家畜牛、羊、马为主,充分反映出畜牧业在匈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匈奴境内定居的居民也兼营畜牧业,伊沃尔加古城近旁有圈栏类遗迹,城址内发现的动物骨骼,92.5%是家畜,其中55%是马、牛、羊。另外,匈奴畜牧业是中原地区畜群补给的主要来源之一,汉朝廷通过劫掠和交换途径从匈奴输入大量的家畜。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匈奴本土上的畜牧业仍然是非常发达的,而农业只不过是个辅助的经济部门。
单一的畜牧经济远不能满足匈奴经济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缺乏手工业产品。随着定居点的出现,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包括制造日用器皿、武器、马具、穹庐及车,以及皮革、毛纺织和乳品加工等。《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8年,乌珠留单于立,汉求匈奴温偶王所居地,单于不给,并说:“匈奴西边诸候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树木。”诺音乌拉匈奴墓中发现很多毛织品,其中有精制的毛毯,显然出自匈奴工匠之手。此外,冶金业和制陶业有很大发展,出现专门从事某项制造业的手工业者。伊沃尔加古城就是一处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城址内发现制陶、金属(铁和青铜)冶炼和加工、制骨及皮、毛加工的作坊。如41号房址内不仅发现大量陶器,而且发现半成品;32号房址内发现大量铁器;25号房址内发现的遗物以骨角器和半成品为主。遗址内发现的炼铁炉,由炉胸和炉膛组成,尽管结构不十分清楚,但无疑是炼铁的场所(图一五)。32和37号房址内发现坩锅和大量铜渣,表明这里是制造铜器的作坊。此外,匈奴境内还有一定数量的加工木器的工匠,匈奴墓葬的棺椁都很讲究,特别是诺音乌拉贵族墓葬有复杂的木结构,包括内椁、外椁和木棺,榫卯结合,严丝合缝,木棺表面还涂漆(图一六)。诺音乌拉墓地还发现不少木器,如案、伞等(图一七),制作精致,技术娴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制陶业是匈奴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陶器有自身的特点,有轮制也有手制,器形比较单纯,以罐为大宗,纹饰有绳纹、弦纹,尤以波折纹为显著特点。匈奴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器,如伊里莫瓦墓地六十座墓中发现约六十件,切列姆霍夫墓地二十座墓中发现十三件,德列斯堆墓地三十三座墓中发现八件,诺音乌拉墓地发现约十件,高勒毛都墓地二十六座墓中发现九件,达尔汗墓地六座墓中发现五件,倒墩子墓地二十七座墓中发现二十件,布利亚特不同地点的三十七座墓中发现三十件。此外,伊沃尔加古城和都连村遗址均发现典型的匈奴陶器。诺音乌拉墓地和伊沃尔加古城都出有高达l米的大型陶罐,可代表匈奴制陶业的水平。
匈奴境内手工业的发展,同匈奴人口成份的复杂构成很有关系。一像伊沃尔加古城这样的定居点,不仅居住着匈奴人,而且有被匈奴征服的当地居民的后裔,以及被俘或逃亡来的各族手工业者,其中包括汉族工匠。这里发现的几十座房址都像阿巴坎宫殿一样,具有汉式建筑的特点。有些陶器和磨刀石上有仇、党、岁、役等汉字(图一八)。蒙古境内的匈奴城址中也普遍发现板瓦、筒瓦、方砖、卷云纹瓦当等汉式建筑材料。所有这些发现,充分说明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工匠活跃在匈奴境内,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后来的游牧民族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政权建立后,曾将众多汉族工匠招至女真人故乡“白山黑水”之间,从事冶铁、金银加工等手工业生产,金上京就有金银店铺,发现有“翟家记”、“邢家记”等戳记的银器,显然都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后来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也曾掳去大量汉族手工业者,他们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蒙古地区,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长春真人西游记》描述“汉民工匠络绎来迎”、“燕京童男女及工匠万人居作”等,充分说明在蒙古地区的汉族各类工匠数目相当可观,对漠北地区手工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现象说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有很大的依赖性,也是游牧畜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四、匈奴族源问题的探索
匈奴族源问题,如同匈奴文化的起源问题一样,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人认为匈奴族与蒙古境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所谓石板墓文化的代表者有关。有人认为早期匈奴人活动在中国北方的鄂尔多斯及阴山一带,这里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些遗存应为早期匈奴人的遗留,也有人提出匈奴人种成分不纯,是由很多具有各自地方文化特征的部落组成的。这第三种意见,实际上融合了前两种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不会是单一的,如同汉族的形成过程中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成份一样,很多少数民族的形成同样也经历了复杂的融合过程,匈奴族也不例外。一般说来,民族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部落联盟,顾名思义,是由很多部落联合而成的,它们经过长期的融合,逐渐形成后来的民族。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族源,而是非常复杂的。
匈奴冒顿单于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建立国家政权以前,匈奴已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关于这一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过精辟的描述,他写道:“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头曼时建立了部落联盟,冒顿单于时建立了国家政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因此,从分散的氏族、部落发展为部落联盟,又逐步建立起国家政权,正是匈奴民族形成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从考古学上探索匈奴族的起源,寻找组成匈奴部落联盟的早期遗存,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方面,苏蒙考古学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关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匈奴族源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同所谓石板墓文化的居民有关。这一点可从陶器的纹饰、某些青铜器和铁器的形制、“野兽纹”装饰艺术等方面得到证实,从而得出外贝加尔遗留下石板墓的当地居民加人到匈奴成分之中的结论。蒙古东部、中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石板墓文化,蒙古学者也提出匈奴同先前的石板墓文化有亲缘关系,表现在陶器、生产工具和某些日用装饰品等方面。因此,苏蒙考古学家将蒙古和外贝加尔的晚期石板墓文化居民同匈奴族的形成联系起来是合乎情理的。
匈奴部落联盟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中国北方的古代部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八至前三世纪),即冒顿单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以前,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很多互不相属的游牧部落,像活动在鄂尔多斯及阴山一带的林胡、楼烦等,都是其中比较强大的部落。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早在春秋时期,即晋文公(公元前636一628年)和秦穆公(公元前659一621年)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这两条记载说明,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林胡、楼烦就活动在中国北方。战国时期林胡、楼烦为赵国的北邻,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299年)“胡服骑射”正是从林胡、楼烦那里学来的。及至冒顿单于时,“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自此楼烦成为匈奴部落联盟的一员,楼烦之名已不见史籍。林胡何时归于匈奴,史无记载。然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林胡在赵武灵王20年(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说明此时林胡仍以独立的部落存在。公元前265一24,年间,李牧曾大败林胡,从此林胡之名也就不再出现于史籍,很有可能部分林胡人加人匈奴部落联盟。
关于匈奴出现于中国北方的记载,有人曾作过详细考证。先秦文献中有关匈奴的唯一可靠记录是《战国策·燕策三》:“太傅(鞠)武谏曰;……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其年代为公元前228年。另据刘向《说苑》一:“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11年。自冒顿单于之后,林胡、楼烦逐渐成为匈奴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族称随之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因此,探索匈奴族源即匈奴部落联盟的形成问题,不能不考虑到林胡、楼烦及其他部落加人到匈奴部落联盟这一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在内蒙古西部,主要是鄂尔多斯及阴山南麓陆续发现同春秋战国时期林胡、楼烦等部落相关的遗存。有人主张称之为前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是可取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杭锦旗桃红巴拉和阿鲁柴登、准格尔旗西沟畔、玉隆太和速机沟、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凉城县毛庆沟、饮牛沟和崞县窑子等十处墓地,共发掘墓葬一三一座(附表二)。
这十处墓地中,前五处分布于鄂尔多斯地区,后五处分布于河套以北的阴山南麓。它们基本反映出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游牧部落的文化面貌。根据文献记载及墓地年代和地望分析,鄂尔多斯地区的几处墓地同林胡等部落有关,其中出土金冠饰及大量金银器的阿鲁柴登和西沟畔2号墓可能属于某一酋长或王的墓葬。阴山南麓的几处墓地,大致同楼烦等游牧部落相关。从这些墓葬的埋葬习俗和随葬品看,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特征,其共同特点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葬,仰身直肢,大部分无葬具,普遍流行殉牲习俗,通常是马、牛、羊的头和蹄(图一九)。早期(春秋至战国早期)随葬品以青铜短剑、鹤嘴斧、刀及兽头饰、鸟形饰、管状饰、联珠形饰、动物纹牌饰等最为典型,并出现衔、鑣、马面饰等马具(图二O);晚期(战国中晚期)兵器和工具种类无多大变化,只是器物形制有所不同。短剑和鹤嘴斧已出现铁制者,而且有了铁制长剑。装饰品以动物纹长方形牌饰和带扣为主,兽头形饰等小型装饰品逐渐消失。陶器以泥质灰陶罐为主,纹饰以波折纹为显著特点(图二一)。
另一方面,鄂尔多斯和阴山南麓墓葬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异,表现在:(l)鄂尔多斯墓葬均为南北向,头向北。阴山南麓墓葬则以东西向为主,头向东,晚期还出现棺椁葬具;(2)鄂尔多斯地区殉牲数量比阴山南麓为多,阴山南麓墓内殉猪的现象在鄂尔多斯地区则不见;(3)鄂尔多斯地区马具很发达,阴山南麓马具较少,而且未见马面饰;(4)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丰富的金银器(图二一),以及大量的圆雕动物形杆头饰件,阴山南麓则以腰带饰牌和各种饰件为大宗;(5)早期陶器略有不同,鄂尔多斯地区以褐陶带耳罐为主,阴山南麓则以泥质灰陶鼓腹罐、双耳罐为主。这些差异显然反映出不同部落之间的差别。
秦汉时期匈奴墓同上述春秋战国时期墓葬有很多内在的联系,这表现在墓葬结构、埋葬习俗及随葬品等各个方面。从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看,西沟畔、补洞沟、倒墩子等汉代匈奴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向,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普遍殉牲,以马、牛、羊的头和蹄为主。倒墩子墓地有些墓头前有龛,内置陶罐和漆器。男女合葬只是个别现象。从随葬品的种类和特征看,秦汉时期匈奴墓出土的长方形动物纹腰带饰件、管状饰、铃、环、环首铜刀和铁刀等,同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器物相似。战国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的饰波折纹的泥质灰陶罐,成为秦汉时期匈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总之,秦汉时期匈奴文化的很多典型因素可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找到渊源。上述这些特征,同外贝加尔、蒙古境内两汉时期普通匈奴墓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中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林胡、楼烦等部落加人匈奴部落联盟是毫无疑问的。
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公元48年,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匈奴是有深刻原因的。这里除了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为原因就是匈奴族源的构成极其复杂。从大的范围说,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石板墓文化的居民,以及中国北方的诸游牧部落共同组成了匈奴”而这正是后来形成南北匈奴的基础。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外贝加尔和蒙古境内两汉时期的匈奴墓地,可视为北匈奴的遗留。中国北方属南匈奴的遗存发现不多,有些东汉时期的匈奴墓,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宁夏同心县河西乡等匈奴墓,其结构和葬俗与汉墓无殊,木椁墓或砖室墓,随葬铜镜、五铢钱、货泉,以及仓、井、灶等陶明器,若不是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波折纹陶罐和长方形透雕动物纹带饰等典型匈奴遗物,简直无法判明其为匈奴墓,说明东汉时期南匈奴已丧失了固有的习俗。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墓地的年代早些,其墓葬结构、葬俗及随葬品仍然保留着匈奴文化的传统,与大漠以北的普通匈奴墓进行比较,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向,单人葬,以木棺为葬具,仰身直肢,头向北;普遍殉牲,以马、牛、羊的头和蹄为主;随葬品以动物纹和几何纹金带饰或铜带饰、透雕铜环、铜铃、环首铁刀、铁带扣,以及波折纹陶罐为代表,并普遍发现铜镜、丝织品、漆器等汉式文物。这些共同点表明它们同属于匈奴文化。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有某些不同,北匈奴有些墓葬地面有石堆,有的沿墓圹竖有石板,继承了当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结构的传统。南匈奴墓葬则继承了当地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特点,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地表无任何标志,葬具除木棺外,无任何石板结构。倒墩子墓地少量偏洞室墓是个例外(图二二),这似乎不是匈奴的传统,可能受了甘青地区某些民族葬俗的影响。因为在甘青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始就流行偏洞室墓。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伏尔加河下游萨尔马特文化墓葬(公元前3一公元4世纪)中流行偏洞室墓。萨尔马特人是匈奴同时代的游牧民族,这里发现的铁短剑和刀、带扣,以及日光连弧纹铜镜等,都与匈奴墓出土的遗物类似。这种偏洞室墓在图瓦艾梅尔雷格匈奴一萨尔马特时期墓地也有发现,所不同的是墓道内填有很多石块,并用石板封门(图二三)。但偏洞室墓在匈奴墓地所见极少,显然是一种外来因素,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匈奴族源构成的复杂性。
南北匈奴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也能看到某些不同之处,如北匈奴墓中普遍发现的羊矩骨(所谓“戈拉哈”)、椭圆形浮雕神兽纹铜带扣、椭圆形镂孔铜带饰及长方形圆角铜牌饰等(图二四,1、2、4、7),在南匈奴墓中很少发现。然而,在内蒙古札赉诺尔、陈巴尔虎旗完工、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等鲜卑墓中则普遍发现这类器物(图二四,3、5、6)。这些鲜卑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北匈奴墓中发现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鲜卑是北匈奴的近邻,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南匈奴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要比北匈奴密切得多,这一点在墓葬随葬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倒墩子墓地出土为数众多的五铢钱,西沟畔墓地出土的龙虎纹石(玉)佩饰、石舞人、玉石觽、汉字刻款的陶器,补洞沟墓地出土的铁鼎、铁釜等,都是汉墓中常见的器物,显然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漠北普通匈奴墓出土汉式文物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及南匈奴墓。当然,漠北匈奴单于及贵族墓葬是个例外,这些大墓都有墓道,有内外椁和木棺,随葬汉代丝织品、漆耳杯、玉石器等,表明匈奴单于及贵族仿效汉代的埋葬制度。但漠北普通匈奴墓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随葬品中汉式文物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这正反映了南北匈奴与中原地区的亲疏关系。
此外,南北匈奴的区别也得到体质人类学资料的印证。有人根据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匈奴墓的人骨资料研究,认为外贝加尔和蒙古诺音乌拉墓地头骨的人种类型基本相同,属蒙古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在外贝加尔地区可能混杂有欧罗巴人种成分。中国北方匈奴墓中,尚未发现两个大人种共存或混血的现象,亦缺乏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人骨具有东亚和北亚人种混合的特征。大通上孙家寨匈奴墓的颅骨特征不同于古西伯利亚类型,从而推测组成北匈奴的主体居民与后来人居塞内的南匈奴,在人种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苏联人类学家考察外贝加尔匈奴人骨后,认为具有古西伯利亚类型和欧罗巴类型混合的特征,得出了与当地原有居民的体质特征有明显区别、匈奴是外来民族的结论。
综上所述,匈奴族的形成过程是很复杂的。从大的范围讲,中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游牧部落(其中包括林胡、楼烦)和蒙古草原上石板墓文化的居民,共同构成了匈奴的主体部分。随着匈奴的强大,又有一些邻近的民族成分融合于匈奴之中,使得匈奴的族源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正因为匈奴族源的复杂构成,造成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匈奴。
五、匈奴与中原地区的紧密关系
匈奴地处亚洲中部腹地,南面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中心,东面是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的农耕文化,西面通过阿尔泰、图瓦同中亚 *** 。由于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随着匈奴的向外扩张,同外界的联系也随之活跃起来,特别是同汉族发生着频繁的接触。这种交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包括军事、结亲、移居、交换、劫掠等。通过这些频繁的交往,匈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得到了发展,尤其得到物质和劳动力的补充,促进了匈奴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关于匈奴与汉族之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接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这里不想详述这方面的内容。但有一点应当指出,“和亲”在汉匈关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据文献记载,汉匈和亲之约始于公元前198年,正值汉高祖和冒顿单于时。此后,西汉历代皇帝均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昭君出塞”。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在位期间曾多次朝汉,关系十分密切。呼韩邪单于死后,按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王昭君嫁复株累单于为妻,继续为汉匈友谊奔走。包头市西郊召湾汉墓出土的“单于和亲”等文字瓦当,就是汉匈和亲的实物证据。和亲政策给汉匈双方带来和平,人员来往不绝。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磾曾任汉朝马监,后任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深受武帝信任。汉哀帝时,匈奴乌珠留若鞭单于曾上书愿随从五百人入朝。汉平帝时,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有的匈奴使者死后葬于长安附近,可见关系之密切。
匈奴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也十分频繁。西汉前期,汉与匈奴便已通关市,鼓励边境贸易。这种贸易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武帝时曾出现“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盛景。公元84年,北单于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说明到东汉时期,汉匈之间仍存在着高额的边境贸易。通过这种边境贸易途径,匈奴从中原地区输入粮食、丝织品及其他各种手工业产品,不仅改善了匈奴人特别是上层人士的粮食结构、服装和生活用品,而且促进了匈奴经济文化的繁荣。当然,汉朝廷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曾明令禁止持兵器及铁出关,更不允许进行交易,违者将受到严厉制裁。尽管如此,汉族商人仍私自与匈奴人交易,汉朝廷是阻止不住铁器外流的。
边境贸易对汉匈双方都非常有利。汉族可从匈奴那里得到牲畜和皮毛,特别是汉代骑兵成为主要的兵种,由于连年战乱,马匹的消耗相当严重。所以,通过正常的交易,从匈奴输入马匹对汉朝廷非常有利,尤其大量牲畜的输入,对中原地区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积极惫义。
汉匈之间这种紧密关系在考古遗存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匈奴遗存中出土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织品、铜镜、五铢钱、漆器、日常生活用具,以及各种建筑材料,生动的展示出匈奴与汉族之间频繁交往的情景。匈奴墓葬和城址中均发现汉代铜镜,如外贝加尔伊里莫瓦墓地3、38、51号墓、苏吉河口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2、15、38号墓、伊沃尔加古城37、41、49号房址及10、57、87号灰坑、诺音乌拉25号墓、高勒毛都25号墓、特布希乌拉7、8号墓,以及补洞沟2号墓、大通上孙家寨匈奴墓等,共发现二十二件铜镜。值得注意的是,除上孙家寨匈奴墓出土的二件铜镜中有一件完整器外,其余墓葬和遗址内发现的铜镜均为残镜。伊里莫瓦3号墓所出二件残镜,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个体。铜镜的种类有四乳草叶纹镜、四乳四螭纹镜、四乳四神镜、禽兽纹和几何纹规矩镜、日光连弧纹镜、昭明连弧纹镜、蝙蝠形柿蒂纹镜等,都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铜镜(图二五)。
匈奴墓出土的汉代漆器更为普遍,但保存较好的为数不多。伊里莫瓦墓地38、43、45-47、49-51、53、55a、58号墓、切列姆霍夫墓地7、13、40、48、51、59、60号墓、德列斯堆墓地33号墓、高勒毛都墓地12、19号墓、特布希乌拉20号墓、倒墩子墓地4、10、18号墓,以及上孙家寨匈奴墓、诺音乌拉大部分墓内均发现残漆器。漆器种类以双耳杯为主,还有钵、碟、奁等(图二六)。伊里莫瓦墓地38、43、,0和58号墓、诺音乌拉墓地6、23和5号(希姆科夫冢)墓都出土比较完整的漆耳杯,其形制和彩绘图案都很相似。其中伊里莫瓦58号墓、诺音乌拉6号墓和5号墓(希姆科夫冢)出土的漆耳杯上均有汉字铭文。诺音乌拉6号墓漆耳杯底部有“上林”二字,杯底边缘有“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经画工获壶天武省”等汉字。希姆科夫(5号)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印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侖素工尊髹工褒上工寿铜耳黄涂工宗画工口印工丰清工白造工失造获工卒史巡守长克丞骏掾丰守令史严主”等六十九个汉字。建平为西汉哀帝年号,五年为公元前2年。蜀郡的工官不仅制造金银器,同时也制造漆器。蜀郡成都就是一个重要的制造漆器的场所,西汉中期以后由汉朝廷直接控制。这里制造的漆器,主要是供宫廷使用,铭文中有“乘舆”二字,说明这些漆器是皇帝的御用品。铭文中还记录有制作的年代、工官的名称、器物的名称和容量、制器工匠的姓名,以及各级官员的名字等。这些专供西汉皇室使用的漆器,应该说是比较贵重的非卖品,它们出现于漠北匈奴贵族墓内,正说明汉匈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匈奴人不可能通过一般的交换途径得到这些漆器,显然是汉朝廷馈赠匈奴单于的礼物。因此使用这些漆器者也绝非一般的匈奴人,而是匈奴单于及其近亲。有人据此推测诺音乌拉6号墓的主人为乌珠留若鞮单于,因为乌珠留若鞮单于于公元前1年朝汉,住上林苑蒲陶宫中,临行时汉朝庭赠送锦绣、缯帛等礼物,其中可能就包括这件漆耳杯。此外,匈奴墓内还发现很多涂漆的木器,如诺音乌拉墓地出土的圆桌面及加工精细的桌腿。诺音乌拉、伊里莫瓦和切列姆霍夫墓地出土的筷子涂有红漆。诺音乌拉贵族墓、伊里莫瓦49、58号墓和切列姆霍夫49号墓的木棺都非常讲究,表面涂有红漆,有的还有彩绘,同中原地区汉墓中的木棺别无二样,显然出自汉族工匠之手。
匈奴墓中发现的丝织品,绝大部分也来自中原地区。德列斯堆墓地28、29和33号墓、切列姆霍夫墓地62号墓、高勒毛都墓地24号墓和达尔汗山墓地3、4号墓均出土丝织品断片。伊里莫瓦墓地45、46、49、50、51、52、58号墓和切列姆霍夫14、35、49、50号墓的木棺都有用丝织品包裹的痕迹。诺音乌拉贵族墓出土的丝织品最为丰富,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好,是前所未有的,包括长袍、长袖衫、肥裤、帽子、鞋垫、额带、小旗、发囊、带子等。织物品种有汉绮、锦、刺绣、罗纱、绢等,其中锦绣都是汉代丝织品中的佼佼者。汉锦是一种五色缤纷的多彩织物,代表了汉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伊里莫瓦和诺音乌拉墓地都出土汉锦,有的还有刺绣。伊里莫瓦128号墓出土“万世如意”植物纹锦(图二七)。诺音乌拉墓地出土的织物上有龙、凤等中国传统的图案,尤其“皇”、“仙镜”、“新神灵广成寿万年”汉字锦、龙纹绢等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汉朝廷常将丝织品作为礼物赠予匈奴,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锦和绣。据《汉书·匈奴传》载,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赠“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赐“锦绣绮谷杂帛八千匹。”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加赐锦绣缯帛三万匹。”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加赐锦绣增帛三万匹。”贾谊《新书·匈奴篇》中说:“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锦。”表明匈奴人的服装普遍用丝织品缝制。关于“新神灵广成寿万年”铭文,有人论证“新”是王莽篡汉后的国号,“寿万年”当指王莽,“神灵广成”即颂扬王莽的功德。王莽时馈赠匈奴有四次,其中包括织锦。
五铢钱是汉代通行的货币,在匈奴墓中也时有发现,特别是在南匈奴墓中很常见。倒墩子墓地l、2、4、6、7、10、11、13-22、25、26号墓均出土五铢钱,其中最多的一座墓(M18)出土一八七枚。外贝加尔德列斯堆墓地32、33号墓和伊沃尔加墓地34、54、172、190号墓均出土五铢钱。塔里克-格林采维奇早年在德列斯堆墓地也曾发现四枚五铢钱。
除此之外,诺音乌拉25号墓出土的带把铜灯、铜罐、铜车軎、透雕狼纹玉饰,6号墓出土的木制伞柄,1954-1955年发掘的诺音乌拉4号墓出土的铁灯、带铺首装饰的铜壶;高勒毛都10号墓出土的玻璃圆盘和铁灯;伊沃尔加古城出土的石制双耳杯、带汉字的磨刀石和陶器;补洞沟2号墓出土的马蹄形铁鼎;都勒戈乌拉出土的马蹄形铜鼎;西沟畔墓地出土的刻有汉字的陶器、龙虎纹石(玉)佩饰等,显然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图二八)。
匈奴除了同中原地区有紧密关系之外,随着匈奴的不断向外扩张,同中亚、西域诸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特别是同月氏、乌孙、安息及大夏有着密切的交往,中国古代文献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蒙古和外贝加尔匈奴墓出土的毛织品、玻璃珠、绿松石坠饰等,表明匈奴人同西域和中亚诸族之间的联系。诺音乌拉墓地出土有伊兰式植物纹、鸟兽纹的西域毛织品,6号墓出土有耗牛与有角狮相斗、格里丰袭击鹿形象的毡毯,25号墓出土有人物肖像的毛织品和6号墓出土有骑士形象的壁毯等,无论其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还是人物的特征,都具有中亚艺术的特点,充分表明这些地区的手工业产品经某种途径也输入到匈奴境内。
总之,匈奴在中国北方活跃了约三百年,他们长期游牧于纵横数千里广漠之地,与中原地区建立了水 *** 融般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互依存的典范。自青铜时代晚期形成的这种格局,在亚洲中部腹地持续数千年之久,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族文化历来为匈奴人所钦慕,他们或秣马厉兵,不断向中原地区挺进,或与汉朝廷结为和亲,入朝事汉,双方之间的关系从未间断。匈奴衰败后,除部分北匈奴人西迁,部分融于鲜卑族外,大部分南迁进入塞内,在以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建立过前赵、北凉政权。然而,这一时期的匈奴人与汉族在文化方面已基本融为一体。
编辑说明: 文章来源于《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篇幅所限,注释从略。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
最近的匈奴大墓的研究渐渐解开了神秘匈奴人的面纱为了更好的区分,我们同时再用一种更适合东方人群的E11算法跑了一下DA39样本的原始数据,结果如下:
覆盖率 = 0.709709
e11
非洲: 0.00%
欧洲: 1.15%
印度: 1.19%
马来亚: 0.00%
傣族: 0.00%
彝族: 17.13%
中国东部: 29.13%
日本: 10.92%
鄂伦春: 23.28%
雅库特: 16.46%
美洲: 0.74%从两种算法的分析结果看,这位匈奴单于具有很明显的北亚血统,其西伯利亚成分大致介于现代内蒙古蒙古族和蒙古国人群之间,更接近后者,但是其西欧亚成分却比现代的蒙古人群还要偏低一些,根据我们的匹配,最近的却是新疆的锡伯族。
----------------------------
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东方考古学教授里奥托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说法:匈奴来自东北亚,并研究证实匈奴国就是古代的韩国。
里奥托教授还特意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简述下他的论据:
1.匈奴和古代韩国的房屋、墓葬方式一致;2.韩国出土了匈奴特有的口哨箭;3.两者都没有监狱系统;4.两者都有娶寡嫂的习俗;5.两者都有杀白马盟誓的习俗;6、金日磾的后裔曾迁徙到朝鲜半岛。
==================================
阿尔泰学人物杂谈
所谓“阿尔泰学”,主要指研治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的学问。
冯家昇(1904-1970)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和语文学家。他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讲师,并协同顾颉刚编辑《禹贡》半月刊。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了辽金史的研究。1937年应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之邀,赴美工作。两年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然后又回图书馆工作。1947年离美返国,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先后任中科院考古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科院民族所研究员。1959年曾去前苏联考察。
冯先生在美国十年,主要从事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继续研究辽史。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协助任教于该校的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教授编写《辽代社会史》。魏氏对中国史的见解,基于风行一时的所谓“征服王朝论”。该学说从历史上把中国社会分为典型的中国社会和征服王朝的社会两大类,运用美国人类学家提倡的涵化论(theory of acculturation)分析征服王朝的社会文化关系,然后又拿辽作为征服王朝的典型,并且以此为基准,对其后的金、元、清诸朝进行考察。
魏特夫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原是德国人,从1921年起,在莱比锡大学学汉学,192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写过戏剧作品。他曾是德国 *** 党员和第三国际工作人员,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从事反对纳粹的活动,于1934年逃到英国,其后去了美国。
1957年,魏氏出版了一部专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 ***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遍及全国的组织形式,形成最高的统治权力,君主专制由此而生,而中国就是这一形式的集中体现。这本书引起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此书应被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研读,甚至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称赞魏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方则认为书中内容失实,充满偏见,根本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只是标准的冷战产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同样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和1994年还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会,1997年出版了李祖德等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集了相关论文。
--------------------------------------
耿世民及其学生
耿世民先生生于1929年,江苏徐州铜山县人。1949-195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维语科,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至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冯家昇先生所受局限不同,耿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已有良好的 *** 尔、哈萨克等现代突厥语和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他读了葛玛丽的名著《古突厥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从此迷上了古代突厥-回鹘语,孜孜不倦地攻读钻研,数十年如一日,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权威之一。1956年他到新疆阿勒泰地区进行调查,首次准确地判断出该地区一部分蒙古族人所操的语言其实是图瓦语(属突厥语),
-----------------------------
====================================
芒·牧林又作牧林,曾用名敦若布、拉希栋鲁布。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讲师。1929年9月17日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期人,蒙古族。
我最初对芒·牧林教授的了解只是一些碎片,例如我在年轻时读过《巴拉根仓的故事》,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听说内蒙古师范大学有位教授在师大门口卖包子。6年前我读到芒·牧林教授的专著《犬鹿说概要——中华民族万年史源流·寻根篇》,我并不懂史前史,只是对中华民族的源头出处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就壮着胆子写了书评《中华民族来自何方——“犬鹿氏”南下与“龙”的北上》,我在文章中认为芒·牧林教授描绘的“南下图”只是一种逻辑推测。芒·牧林教授看了文章设法找到了我,那是在6年前,他当时80岁。我这才对上号:《巴拉根仓的故事》的作者和卖包子的教授原来是一个人,他叫芒·牧林。
芒·牧林豁达、爽快、乐观、直性子,有啥说啥。我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很快就和他成了好朋友。我们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边喝边聊,聊得很投机。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学者,他出生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贫困牧民家中,只学过7年蒙古文,随后闯荡社会,从事过十几种职业。
通过近30年的研究,芒·牧林认为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并不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两个不同语系,而是同根同源的亲属语。并绘制出了《蒙古人种后裔语言普系“树形图”》。这是他的重大研究成果。芒·牧林还依据我国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扎赉诺尔地区、嘎仙洞等地发掘出的蒙古人种现代人的化石和居落遗址,得出蒙古人种现代人是诞生于黑龙江、松花江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结论,这是他在历史领域的又一个独立创见。
芒·牧林的7个发现,被他用图表的形式形象、简约地概括了。他绘制了《蒙古人种后裔诸族历史源流谱系年表》和《蒙古人种后裔语言“树形图”》,这一图一表是他近40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从图上能清楚地看出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原本同根同源;从表上能看出黄种人后裔的各民族的历史沿革过程,他们本是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芒·牧林这些研究成果,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如果能够经得起今后的专家学者和时间的检验,那将是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建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