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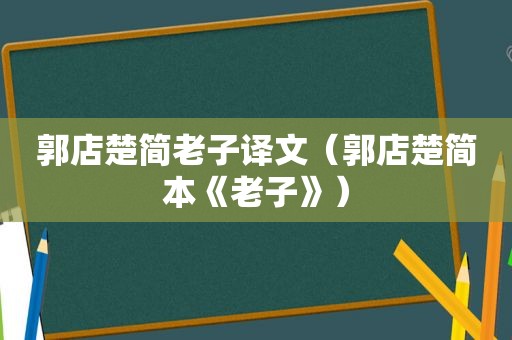
楚竹简《老子》甲组
第二章勘定文本:
江海所以能为百源王,以其能为百源下,故能为百源王。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
其在民上民弗压,其在民前民弗害,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原文今译:
王者众望所归。江海能聚百川而成百源王,因其身处百源之下,这才成就了百源王。圣人之所以能引领百姓,是其能将自身利益放在最后;之所以能为百姓拥戴,是其能将自我置于百姓之下。因此,圣人位居百姓之上则决不欺压百姓,身处百姓之前则决不损害百姓的利益。天下乐于供奉而决不厌弃,正是因为圣人从不与百姓争利。也正因如此,天下才无人能与圣人相争。
楚简图文:
江海所㠯(以)能爲𦣻(百)[⿱谷水](源)王,㠯(以)亓(其)能爲𦣻(百)[⿱谷水](源)下,是㠯(以)能爲𦣻(百)[⿱谷水](源)王。聖人之,才(在)民前也㠯(以)身後之;亓(其)才(在)民上也㠯(以)言下之。亓(其)才(在)民上也民弗[⿱石毛](压)也,亓(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詀(厌),㠯(以)亓(其)不[⿰青爭](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廾](与)之[⿰青爭](争)。原文注释:
(1)“圣人之”,圣人是;“之”,动词,是、为;句子读作“圣人就是”或“圣人表现为”。《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这里,“之”即动词“是”。
(2)“在民前也以身后之”,“也”,表示停顿转折,不是单纯的语气停顿,相当于“则”的用法;“以”,将,下句用法同。此句义为:“当位居百姓之前时,则将自身利益置于百姓之后”。
(3)“在民上也以言下之”,“也”,停顿转折,相当于“则”;“言”,表示“我”,将“言”作“言辞”解系误读。此句义为:“当位居百姓之上时,则将自我处于百姓之下”。《诗经·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亨传:“言,我也。师,女师也。”诗意说的是,女子要告请自己的女工师傅,自己要回娘家探望父母。
(4)“其在民上民弗压,其在民前民弗害。”先秦文言中,动词有直接用法、使动用法和被动用法三种情形。这里,“压”和“害”都是动词的被动用法,“民弗压”指百姓绝不会遭到欺压,“民弗害”指百姓绝不会受到损害。“弗”,在此用法与“不”的含义略不同,先秦文言中,“弗”有“绝不会”的意思,而“不”仅仅指当下没有发生,但绝不是不可能发生。
(5)“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进”,作“奉”解,义为供奉、奉献。“厌”,厌弃。“其”、“之”,代指圣人。《战国策·齐策》:“群臣进谏。”“进”即奉献。
本章点评:
楚简《老子》并非老子原本或原本摘录,还原版《道德经》已举证说明,楚简本混入了战国后人的若干段衍文,且出现了多处对老子原章节的混编,以及对关键字的误读误勘。根据还原版《道德经》,楚简《老子》此章也出现了整段的脱文,而脱文在帛书《老子》和传世本《道德经》中则成了另外一章。还原后完整的老子原本章节如下: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江海所以能为百源王,以其能为百源下,故能为百源王。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
其在民上民弗压,其在民前民弗害,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还原后的章节气势磅礴,结构完整,论证严谨,义理明确。天地与江海対举,圣人与百姓対举,其与天下対举,清晰诠释了“圣人不自生”的概念及内涵,将老子不争而有争的辩证逻辑展现无余。
因此,解读楚简《老子》本章,要放在还原后章节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方能不离老子宗旨。本章是老子对“圣人不自生”的全面阐释,包括定义、原理、表现形式及特征、以及其所昭示的辩证逻辑。
“圣人不自生”体现为“无私”、“无我”,表现为“后其身”、“下其言”,所以从义理出发,这里的“言”绝非“言辞”之意,而是罕见的代词用法“我”,这一点是传统老学完全没有认识到的。传统老学天真地认为,只要言辞谦下,就能成为翩翩君子,但这与老子的境界仍就是天壤之别。言辞谦下不排除虚情假意,没有自我才是圣人的境界,来不得半点虚伪。将“言”作“言辞”解显然是未通老义。
“其在民上民弗压,其在民前民弗害,天下乐进而弗厌”,这三句中出现了动词的两种用法。先秦文言中,动词有直接用法、使动用法和被动用法三种情形,使动用法常见,但被动用法极少见。“压”与“害”是被动用法,读作“被压”和“被害”,指圣人不欺压百姓、不损害百姓;而“厌”则是动词的直接用法,表示天下不厌弃圣人。传统老学似乎对动词的被动用法并没有清醒认识,将“压”误勘为“重”,如果用被动用法解读就成了“圣人位居百姓之上则不尊重百姓”,足见“重”非老子原文。而诸校本将“压”隶定为“厚”,只是为了附会传世本的“重”字,表明诸校本也未认识到先秦文言中的动词被动用法。
本章的校勘还涉及了先秦各国的文字差异。楚国地处偏远,国君又非周王室嫡亲或近臣,与周朝主流文化的交流相对不频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发展进程,体现在文字上便出现了诸多与中原不同的文字写法。这种文字上的差异导致了后人对老子原本的释读讹误,最典型的就是“浧”与“盈”在内涵上细微的差别导致了对“道冲”的误读,并延续至今。本章又出现了两个例子,老子原本中代表“源”的字被后人误读为“浴”,有转而误释为“谷”,于是“谷神”这个莫须有的概念横空出世,误导人们至今。另一个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压”字,楚人与周人文字写法上的不同导致了后人对老子思想的曲解。类似的例子在《道德经》的校勘中屡见不鲜,值得人们重视。
最后不得不提及,“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楚简本中作“以其不靜也,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在楚简《老子》中写作“静”。这向世人证明,老子原本中“静”是“争”的通假字,从而进一步证明,“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千古名言是一个赝品,老子的原句是“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
诸校本对照:
江海所以能为百源王,以其能为百源下,故能为百源王。(龙潭校本)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能爲百谷下,是以能爲百谷王。(李零校本)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能爲百谷下,是以能爲百谷王。(丁四新校本)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能爲百谷下,是以能爲百谷王。(廖名春校本)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能爲百谷下,是以能爲百谷王。(彭吴校本)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邓谷泉校本)龙潭校本与诸校本差异:
此段文字,龙潭校本与诸本的差异在于“百源王”的“源”字和“故能为百源王”的“故”字。
“源”楚简《老子》作“上谷下水”,诸校本均将此字隶定为“浴”,并认为“浴”假借为“谷”。如此解读虽与帛书的“百浴王”和传世本的“百谷王”相印证,但“谷”字本身的释义在解诂老子时却始终是个问题。
楚简《老子》中有两个不同的字今天都被隶定作“浴”,分别是“上谷下水”和“左水右谷”。从楚简《老子》的上下文分析,两字的含义并不相同,用法上并不能互换,故两字实际上并非一个字。将“上谷下水”隶定为“浴”有明显的不适之处。
郭店楚简《老子甲》中的“上谷下水”郭店楚简《老子甲》中的“左水右谷”刘信芳、崔仁义等将“上谷下水”隶定为“涡”,但刘信芳认为“涡”为河流之总称并无他证可举,难以令人信服。“上谷下水”的“谷”是个上面盖了顶的山谷,象形山洞,洞里流淌着山泉,出了洞口形成了瀑布。因此,从造字上推断,此字含义应该代表“水之源”。
“上谷下水”这个字金文未见,那么同样的含义当另有文字代之。从含义推断,这个代字应该就是金文和秦篆中的“原”字。“原”,从厂从泉,厂表示山崖;“原”即源泉,指泉出地表沿山崖流躺而下。
西周晚期的“原”字秦篆中的“原”字而反过来,楚篆中也未见“原”字。前后两相综合,可以推断,楚篆的“上谷下水”对应的该是金文和秦篆中的“原”字,因各国文字有差异故出现同一概念有不同写法。“上谷下水”与“原”其实就是同一命题下的两幅画,前者为楚人所作,后者为周人所作,又被秦人传承。两个字表达都是“水之源”,而“水之源”今写作“源”,故“上谷下水”当隶定为“原”,通“源”。
而“左水右谷”则会意山谷中流淌着水,这里的“谷”没有盖顶,是“谷”的原形,其含义是“溪”与“川”的统称。古“溪”指没有出口的山间水沟。后“溪”、“川”兴而“浴(用作溪或川)”废,故今天的“浴”字并无“溪”或“川”的含义。但这却是“浴”在楚简《老子》中含义。
“浴”,始见于甲骨文,会意人立于器皿之中,四周有水滴落下,写作“人+水+皿”,本义为沐浴。但此写法大约在战国时期讹变成了“浴”字,中间过程不明。但这并不能排除“浴”与“人+水+皿”在春秋时期是两个独立的字,“浴”指“川溪”,“人+水+皿”指“沐浴”,而在战国后期,“浴”字才替代了“人+水+皿”,有了“沐浴”的含义,且“浴”的本义“川溪”也随之消失。
甲骨文中的“浴”字,从人从水从皿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沐浴”不用“浴”字,可以在《庄子·知北游》中找到佐证:“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 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庄子这里“澡雪而精神”的“澡”字,就是“沐浴”的意思,可见楚人用法中,“浴”指“溪川”,“澡”指“沐浴”。
综上,“上谷下水”和“左水右谷”在楚简《老子》中是两个字,一个当读作“源”,一个当读作“溪川”,两者都没有“沐浴”的含义,与“人+水+皿”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字。战国后期,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左水右谷”与“人+水+皿”两字合并为一字,作“浴”,同时也不再有“溪川”的用法。而在统一文字后,“上谷下水”则又被“源”取代,此字也从此消失。
基于上述论证,龙潭本隶定“上谷下水”为“原”,读作“源”。
“故能为百源王”,楚简本作“是以能为百(谷+水)王”,帛书甲乙本作“是以能为百浴王”,汉简本及各传世本作“故能为百谷王”。据还原版对诸版本的综合分析,楚简本已是战国后人在老子原本基础上的改写本,因此存在一个更原始的祖本,这个祖本是否已经出现了大量错简无法定论,但至少是没有战国后人的添加和改动。根据还原版《道德经》所复原的完整章节,从文章的语句结构上判断,老子原文此句应该是以“故”开头而非“是以”开头。至于传世本等的“故”字是否直接传承于更原始的祖本则不得而知。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龙潭校本)
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李零校本)
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丁四新校本)
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廖名春校本)
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彭吴校本)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邓谷泉校本)龙潭校本与诸校本差异:
龙潭校本的断句与诸校本异,且删除了后句句首的“其”字。
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龙潭校本对句中的三个字,“之”、“也”、“言”的释义与诸本不同。此三字的用法决定了版本校订。
“之”字,传世本皆无,但帛书甲乙本及汉简本均有,然后人大多未予以重视,如高明在校订帛书时根本未提及帛书与传世本在这点上的差异。诸楚简校本也均未言及“之”字的用法,唯廖名春提及“之”是助词。“之”在此并非助词,而是动词,表示“是”或“为”。《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这里,“之”即动词“是”。
“圣人之”表示“圣人就是”或“圣人表现为”,其后两句“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是圣人特质的体现。因此,这一段文字与上段“江海”的特质是并列关系,但传世本将其改成了因果关系,在“圣人”句前添加了“是以”等字,误导了人们的理解。又因为“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是圣人特质的体现,两句是平行的,故“其”出现在后句之首为多余,系后人误读而讹增,故龙潭校本将其删除。
“也”在此为转折连词而非单纯的停顿助词,其用法如“则”。“在民前也以身后之”读作“在民前则以身后之”,“在民上也以言下之”读作“在民上则以言下之”,因此“也”字不作断字符处理,也不需要在此断句,如此才是对这两句的正确理解。这两句是老子“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另一种表达,寓意相同。
帛书甲乙本此段文字作“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是以”、“欲”、“必”、“其”皆系后人妄增衍文,传世本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帛书本。
“言”,诸校本读作“言辞”,非是。“言”在此作代词,表示“我”。《诗经·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亨传:“言,我也。师,女师也。”“以言下之”就是将自我排除在外,相当于“外其身而生存”,是无私无我的体现,而以“言辞”释“言”则没有“无我”的内涵,未能体现老子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最后,“在”楚简本作“才”,“才”通“在”,诸校本皆同。
其在民上民弗压,其在民前民弗害,(龙潭校本)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民弗害也。(李零校本)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民弗害也;(丁四新校本)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民弗害也;(廖名春校本)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民弗害也。(彭吴校本)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民弗害也。(邓谷泉校本)龙潭校本与诸校本差异:
龙潭校本删除了衍文“也”字,并读第一句为“其在民上民弗压”,句末字为“压”而非“厚”。
“压”,楚简本作“上石下毛”,读作“压”。此字,裘锡圭、张光裕、崔仁义、刘钊等隶定为“上石下毛”,读作“厚”;廖名春隶为“上石下丰”,仍读作“厚”,释为“重”。二说皆非是。“上石下毛”为会意,石在毛上,表示“压”,含“重”义,但“重”另有其字。“厚”字写法则不同,为“上后下子”。因“石”、“后”二字形近,又“毛”、“子”二字形近,故两字常被混淆。楚简“含德之厚者”一句,其中“厚”字作“上石下毛”,系抄写讹误,而非“厚”之另一写法,诸校本将讹误视作“厚”之异体,系受到传世本“圣人处上而民不重”的影响,以“重”释“厚”,而误将“压”读作了“厚”。
楚简《老子甲》中的“压”字,“从石从毛”,“毛”的一笔向右撇望山楚简中的“厚”字,“从后从子”,“子”的一笔向左撇传世本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还原版《道德经》将此文校订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弗狎其所居,弗压其所生。夫唯弗压,是以弗厌。”传世本的三个“厌”字,前两个都是“压”之误读。古“压”、“厌”均作“猒”,或通“壓(压)”,或通“厭(厌)”,故传世本将“弗压其所生。夫唯弗压,是以弗厌”误读为“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至今仍困扰着许多人。据此可知,“压”、“厌”対举为老子本义,楚简本这里遵循同一逻辑,上文言“其在民上民弗压”,下文言“天下乐进而弗厌”,是“压”、“厌”対举又一例。
“压”字的写法不同,很可能又涉及周楚两国文字的发展不同,“上石下毛”为楚字,而“猒”字为商周金文的写法,后人未明“上石下毛”即“猒”字,而将前者误勘为“厚”字。
“其在民上民弗压,其在民前民弗害”二句,句义完整,无需再增加断句,且“其在民前,民弗害也”的“前”字后也无“也”字,暗示这里的三个“也”字,盖为后人画蛇添足之举,反致文义拗口晦涩,故龙潭校本将此三个“也”字删除。
这里要对先秦动词用法再另作强调。先秦文言中,动词有直接用法、使动用法和被动用法三种情形。这里,“压”和“害”都是动词的被动用法,“民弗压”指百姓绝不会遭到欺压,“民弗害”指百姓绝不会受到损害。诸校本对此均无明确阐述。此外,“弗”,在此用法与“不”的含义略不同,先秦文言中,“弗”有“绝不会”的意思,而“不”仅仅指当下没有发生,但绝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两点直接导致对文义的理解不同。
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龙潭校本)
天下樂進而弗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李零校本)
天下樂推而弗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丁四新校本)
天下樂進而弗詀。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廖名春校本)
天下樂進而弗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彭吴校本)
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邓谷泉校本)龙潭校本与诸校本差异:
龙潭校本删除了后人添加的衍文“也”字,其余与诸校本无实质差异。“以其不争”句后的“也”字系衍文,可从还原版《道德经》复原后整章的文脉和语气中推断得知。
“乐进”,楚简本作“樂進”,帛书甲本作“樂隼”,帛书乙本作“樂誰”,汉简本及各传世本作“樂推”。疑老子本字为“樂隹”,而后人对“隹”作了不同解读。“隼”与“誰”系讹误,“進”与“推”义近。丁四新读“進”为“推”,以符会传世本,并引《礼记·儒行》郑玄注:“推,犹进也,举也。”其最终仍然释“推”为“进”。
“厌”,楚简本作“詀”,诸校本读“詀”为“厌”。唯廖名春与诸本有别,训“詀”为“止”,谓“弗詀”即“不止”,称与“不厌”义近。故所引诸校本实无本质区别。然丁原植、刘信芳等读“詀”为“詹”,训“多言”,是未通老义。
至于“詀”为何读作“厌”,谢偑霓引颜世炫说颇据说服力,言马王堆帛书《杂疗方》云:栖木者为蜂、蛅斯。而古“蛅”字的写法为“疒+猒+虫”,提供了“猒”通“占”更为直接的证据。
最后,非常有必要谈一谈这段文字中的两个“争”字。“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楚简本中作“以其不靜也,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在楚简《老子》中写作“静”。从文义上分析,这个“静”字无疑是个通假字,以音通“争”。这是从文献基础上证实了老子原本中的“争”写作“静”。这一点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从侧面证明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千古名言竟是个千年乌龙,老子的原句是“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将“有争”改作“不争”是汉以后的闹剧,帛书甲本此句作“上善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帛书乙本和汉简本作“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帛书乙本及汉简本晚出,后人已根据通假规则将“有静”校勘成了“有争”。“不争而有争”是老子辩证逻辑的智慧结晶,然而这一超人的智慧却被封存了两千年,正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