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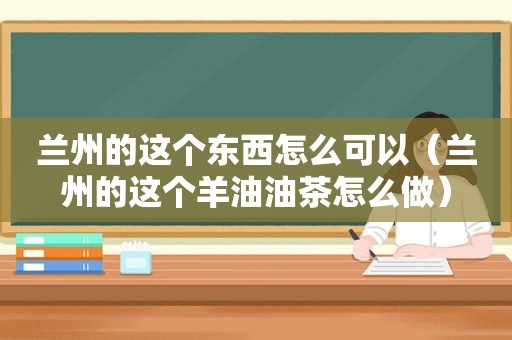
我在阿干镇,七里河区东南部。
早在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这里即置阿干堡。后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
升为阿干县,元初仍为阿干县,又为司侯司。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废县、司并入 *** 。明为 *** 阿干里。明洪武年间(1268年至1398年)开采煤炭,随即制陶、冶铁、铁器加工业相继发展,商贸兴起。阿干镇为远近驰名的集镇。
阿干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炭花坪。
相传,在明代正式开采这里的煤炭之前,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阿干镇与很多地方一样,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商。有位客商途经阿干镇砂子沟,在半山处休息时,用几块黑石头垒个土灶拾柴生火取暖,烧着烧着,这几块石头也着了起来。自此,发现了阿干镇的煤炭。后来,人们把发现煤炭的地方就叫做炭花坪。
曾经,由于地质断裂形成,炭花坪有煤层暴露。因此,在炭花坪挖洞开采煤炭,自然是阿干镇最早的煤洞。然而,历经多年之后,由于山体缺乏支撑,形成了巨大的山体滑坡,将炭花坪掩埋。就这样,炭花坪不复存在,变成了没有揭秘的传说。但如今砂子沟的煤炭,亦是阿干镇煤炭质量最好的地方之一。
比这更为久远的历史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300年),阿干镇就有先民生息。在今阿干镇中街西1公里,西沟北坡台地上,东西长200米、南北宽20米的范围内。
1974年农民耕作时,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彩陶罐,经鉴定,属于马家窑晚期。1976年进行了普查,发现该地保护情况尚好,地面陶片较多,断崖处有暴露的文化层和灰坑。采集到的标本有彩陶片、细泥红陶片、细泥灰陶和夹砂粗陶。还有零星兽骨、石器等,属马家窑、半山两种类型。
这就是坐落于阿干镇的“古城坪遗址”。据说,它与被掩埋的炭花坪之间的距离不足500米。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阿干镇广为流传:阿干镇原名瓦缸寨。清朝康熙年间陕甘分治,左宗棠督甘期间,因朝廷权力之争,皇宫一位阿哥为了逃避宫廷之乱遇害,带着自己护卫来到瓦缸寨,为了纪念皇子,把瓦缸寨更名为阿哥寨,后由于历史变迁,当地百姓土语叫白,就成了现在的阿干镇。
一个“哥哥”,就这样出现在了 *** 城的历史中,但我要说的是,这个传说并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也只能是个传说。在 *** 有一句这样的谚语:“先有炭花坪,后有古城坪”;“先有炭花坪,后有 *** 城”。这谚语把我推向一个比清代更为悠远的历史空间,让我想到了一个鲜卑单于的深情呼唤。
阿干西,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为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大棘住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这首歌被称为《阿干之歌》,是鲜卑单于慕容廆(音:伟)为自己的哥哥写的,它拉近了东北与西北的距离,让我在血液中的那份亲情感动里,把 *** 的历史一页页地翻开。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曾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山长。他在合校本《水经注·卷二》中,有段关于阿干、关于 *** 的记述:
“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 *** 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又说:“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又有沃干岭,亦阿干之转音。”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阿干之歌》曾在 *** 地区广泛流传。阿干水就是阿干河,为黄河南岸沟谷支流,古称阿干河。源于榆中县南部马口卸山北麓。汇集榆中县马口卸山与兴隆山之间马坡、银山两乡山区水流向西北流入七里河区,始称柴沟河、阿干河。经铁冶、阿干镇,汇琅峪沟、铁冶沟、西沟、烂泥沟、大沟、石佛沟等沟壑水流,叫水磨沟;经岘口子、东果园、清水营、侯家峪、花寨子、二十里铺、崖头、后五泉、八里窑、五里铺、沈家坡等村落,汇黄蒿沟、沙沟、黄家沟、后五泉等沟壑和山泉水流,再北流经沈家坡、孙家台、 *** 市工人文化宫、北园,至白云观西入黄河,这段俗称雷坛河。
*** 人民对这条河非常熟悉。阿干河全长44.6公里,流域面积256平方公里,年径流可达987万立方米。合校本《水经注·卷二》中说“利民”是因为,过去的 *** 城,虽处黄河之滨,但可取水的途径较少,在阿干河引水渠开凿之前,“黄河岸峻,东西两川田亩,水不能上”、“独城西南为阿干河,发源自天都山者,为利频广”。至于人们把这条河叫做溥惠渠还有着这样一段故事:
据《 *** 水利志》载,七里河区八里镇有个古老的引水渠叫溥惠渠,是 *** 最早的水利工程,初修建于明成化年间,沿阿干河东西两侧凿渠架槽修成引水渠,西渠绕助峰山(华林山)麓西流至西园,灌溉上、下西园农田;东渠绕龙尾山麓东流,灌溉今 *** 解放门、北园及酒泉路南端以西,包括今上下沟、双城门、王马巷、甘家巷等地区,还引此渠水穿城而过,作为 *** 城市用水的一个补充水源。但东渠多砂砾、西渠多冢穴,经常“崩坏而咸泄”,每至春夏旱季则“ *** 滴不入”,“不沾勺水”。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皋兰知县湖南慈利人丁璇,筹款拨料,还得到肃王世子的赞助。制作木槽,“布之东西二渠”,克服了“渠崩泄塌”之虞。从此渠水畅通,给 *** 人民带来生活灌溉之利,因而被彭泽命名为“溥惠渠”。
彭泽在《溥惠渠记》中称:阿干河水引入 *** 后,“为利颇广,环郡城之东西南北,为圃者什九,为田者什一,几百倾之灌溉,附郭之戍卒居民,壅飧饮食,咸仰给焉”。“凡官民蔬圃暨艺业者无不沾其利,然阿干河之利固若此,而黄河之利尤大焉。”彭泽逝世后,就葬在上西园,紧临这条溥惠渠。此渠至解放初期仍发挥着灌溉作用。(张正军《寻找消失的溥惠渠》, *** 晚报2013.05.02 )
“哥哥”在这里城池、地名,而且还是河流与 *** 人民的幸福。现在,让我们回到慕容廆的《阿干之歌》,回到1000多年前的北方辽阔草原,寻找那个距我们分明有些遥远的人或者民族——吐谷浑。
公元283年,辽河流域的慕容鲜卑首领慕容涉归去世,他有两个儿子,老大是小老婆生的,叫慕容吐谷浑;老二是大老婆生的,叫慕容若洛廆(简称慕容廆)。慕容涉归在临死前,把自己的部落分成两部分,主体部落由老二若洛廆统领,老大吐谷浑则分得了1700户。小老婆生的孩子在这里就受到了“歧视”,但对于吐谷浑来说,这才是个开始。
某年春天,慕容廆正率部众召开会议,会然部卒来报,两兄弟的马在河边喝水的时候互相打了起来,慕容廆的马大概吃了亏,就很生气,派人对他哥哥说:“父亲临死前已经让我们分家了,你为什么不走远点,害得我们的马互相打架。”
吐谷浑听了也很生气,对弟弟说:“春天来了,马在一起吃草喝水,互相打架有什么稀奇的呢?可是马打架,你却迁怒于人,太不讲理了。你不是叫我离你远点吗?那好,我马上就走,一定离你十万八千里!”
听哥哥这么一说,慕容廆有些后悔,派族中的长老以及长史七那楼去向吐谷浑道歉。
吐谷浑说:“父亲生前曾占卜过,说他的两个儿子以后都会大显于天下,我是庶出,不敢和嫡子争雄。现在,我们兄弟俩因为马打架的事情闹得不愉快,也许是天意让我离开独自发展。现在你们既然留我,那么就看看上天的意思。请你们诸位把马往东边赶,如果马朝东走,我就随你们回去。”
七那楼等人把马往东赶,可马走了没有几百步,突然就发出长长的悲鸣声,然后掉头又朝西跑。马是识途的,东边才是它的“家”,但七那楼等人却遇到了“意外”,他们一共试了十几次,马都不肯向东而去,都会掉头西跑。
七那楼等人被折腾得实在没有力气了,只好无奈地跪下来对吐谷浑说:“单于,看来真的是天意啊!”
吐谷浑对七那楼等人说:“上天告诉我,我们兄弟俩的子孙都能昌盛于天下,若洛廆的子孙在一百年内就会名盛一时,而我的后代则要到我的玄孙子那一辈才会闻名天下!”随后,带领自己的部落一路向西、向西,再向西。(《晋书·吐谷浑传》)
这就是在今天仍然被流传的吐谷浑部落西迁的传说诱因。在哥哥离去的背景里,是弟弟深情的追忆与呼唤。歌中所说“辞我大棘住白兰”,一东一西,即是吐谷浑西迁的里程。
大棘,古城名。又名棘城。故址在今辽宁义县西北。公元294年鲜卑慕容廆徙此,建前燕国后即以此为都城,至公元342年始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
白兰,在今天的青海南部,在吐谷浑部落到来之前,当地生活着的是以游牧为生白兰羌人。其地因白兰羌人而得名。
人生能有几阿干?在鲜卑语里,阿干就是阿哥的意思。在弟弟的声声呼唤里,哥哥一直向西。哥哥先是率领部众先到了阴山,不久西移甘陇,渡过洮水,进入今天的甘肃西南和青海东南部。由此,吐谷浑由一个人的名字——慕容吐谷浑,渐变成了一个部落、政权民族的名称。
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后经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唐后期称之为退浑 、吐浑。
一段历史就这样停留在了阿干镇,在“先有炭花坪,后有 *** 城”民谚里, *** 城也便有了一个让人倍感温暖的名字——哥哥!而当翻开史书,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名字要比 *** 更早。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在 *** 西设令居塞驻军,为汉开辟河西四郡打通了道路,但那时的 *** 不过一个小小的“兵站”。公元前86年,汉朝在今 *** 始置金城县,据说是当年修城时,挖出了金子,所以,就叫了“金城”这个名字,时属天水郡管辖。
583年,改金城郡为 *** ,置总管府。因城南有皋兰山,故名 *** 。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 *** ”之名,但很显然地,它要比吐谷浑率部西迁及建立吐谷浑王国的时间(公元313年)晚得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公元前86年有“金城”之名,至吐谷浑率部西迁,至583年“ *** ”出现,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时光里,人们至少有200多年是将“金城”与“阿干”混杂在一起并称今天所说的“ *** ”。
地名就这样与历史不可分割地吻合在了一起, *** ——哥哥、哥哥—— *** !我在阿干镇就这样将 *** 一次次地呼唤,在弟弟深情的歌声里、在哥哥西行的马蹄间,涌在我心头的不仅是亲情的温暖,更有对地域的爱恋。未完待续(文/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