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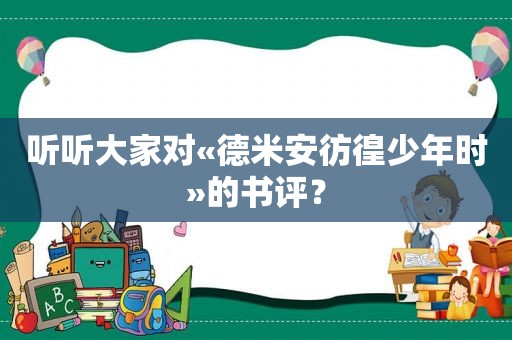
不太同意前边关于《德米安》这本书的解答,所以自己写了一篇。
1919年《德米安》出版时,作者黑塞因政治主张家破人亡,正面临国家的驱逐,这使得他不得不前往瑞士以辛克莱为笔名出版了本书。伟大的作品不会被轻易埋没,《德米安》一出世便收获了各界关注,人们向这本书的出版商寄信,询问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黑塞对于青春期的分析和对自我的探求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正在、已经经历青春期的读者,都能从辛克莱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一段脆弱、敏感、渴望成长又惧怕新世界的阶段是一些人的梦魇,也是一些人后半生不断回头歌颂的青春,黑塞给出了他对青春期的定义——“这些迷惘、彷徨,是为了让人具有自己的个性,让人向内探求认清自我,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个性的人。”
我一直觉得读小说在于拓宽生命的厚度,在有限的时间里,小说的主人公传递着不同的人生体验,以不同的视角帮助我们体验生命的更多可能。
《德米安》这本小说比起其他拓展人生样貌的戏剧化小说而言,更像是一本启示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历的年少,那些与世界对抗、努力成为具有个性的独立个体所做出的痛苦挣扎,最终鼓励个体去成为自己的信仰。
整本书暗含的宗教色彩一直在为最终的自我信仰做铺垫,从一开始辛克莱因为逞能说谎偷的苹果,该隐与亚伯的故事,邪恶与纯真的神,到破壳而出的鸟与男女共体的Eva,都在为辛克莱一步一步走出父辈所创造出的无菌、高尚的环境,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做铺垫。
辛克莱家境优渥,自幼家教得体,但他总隐隐的感觉那个明亮的世界与他自身有一层隔阂,他难以与那个世界亲近起来。恰巧一次嬉戏时,辛克莱在小伙伴面前逞强,编造了自己偷了果园里的莱茵特苹果的故事,而后被弗兰茨·克罗默威胁,自此走上了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
辛克莱害怕被戳穿的恐惧支配着自己偷窃、欺骗、行尽家教所不容之事。
我的罪过不是这个或那个,我的罪过在于我把手伸给了恶魔。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辛克莱有了胜过权威的感受,尝到了恶毒的甜头。
一种生满了倒钩的恶毒而又刺痛人心的感觉:我觉得我胜过了父亲!一时间我感觉到自己对他的无知的某种蔑视。
我这样想着,觉得自己象一个本应供认谋杀罪、现在却因一个被偷窃的小圆面包而受审讯的罪犯。这是一种丑恶而又有害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很强烈,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比任何其他想法都更紧密地把我和我的秘密和罪过联系在一起。《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吃了禁果,描述的是一种性启蒙,黑塞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启蒙,对父权的颠覆,而后当辛克莱面对克罗默弑父、邀请姐姐的要求,辛克莱的无助与忐忑将他引向了另一个极端;把自我的控制权移交到恶魔的化身——克罗默手上。
德米安以导师的身份带领辛克莱走上了认识自我的道路,对“该隐和亚伯”故事的颠覆让辛克莱开始质疑神学的权威。
我没完没了的这样想着。一块石头掉进了井中,这井就是我年轻的灵魂。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该隐、杀人和标记这件事是我对认识、怀疑和批判所进行的一切尝试的出发点。德米安的出现,将辛克莱从恶魔的手中解救出来。
人不用害帕任何人。如果你害怕某人,那么等于承认了这个人对你的控制权,比如你干了某些坏事,被另一个人知道了,于是他就获得了对你的控制权。解决了克罗默这个大难题后,辛克莱开始逃避,放任自己回到从前的生活中去,然而启蒙后的意识再也回不到当初。
是我摆脱痛苦的解放来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面,伴随着这种解放,某种东西进入了我的生活,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前往自身的道路荆棘密布,辛克莱在之后的青少年时期,无时无刻不因认识自我而痛苦。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走一条把人引向他自身的道路使人更厌恶的了。
上帝有多重方法让人孤独,却唯独引导我走向自身。但是辛克莱内心明白,自己不能再依靠父亲与母亲,依靠恶魔或者德米安,面对成长如潮水般袭来的速度,躲避在他人的麾下固然容易,但精神上,辛克莱唾弃这样的自己。
我把自己变的更幼小,更需依靠,更天真。我必须用一种新的从属来代替对克罗默的从属,因为我不能独自行走。我过着儿童的双重生活,可我已不再是儿童了。我的意识存在于惯常的、符合规矩的东西里,我的意识否定逐渐产生的新世界。我就像大多数具有良好教养的人一样,把自己的事情干得很糟。德米安关于老实强盗临危悔改的不屑再次冲击了辛克莱的世界,辛克莱建立在宗教上的世界观也一点点的被德米安推翻,让辛克莱察觉到自己所知的完美世界不过是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半。那个世界充满了欲望、丑恶和禁律的事物,辛克莱恐惧的守卫着自己建立在不完整世界观上岌岌可危的自我意识,德米安告诉他。
“犯禁律”不是永恒的,它会变。谁懒得去思考,懒得做自己的法官,谁就不得不服从既定的禁令。每个人必须代表他自己。辛克莱离家去St学习的那段时间,沉沦在自我觉醒的成就感中无法自拔,不断做出出格的事以彰显自身的独特,同时对这种觉醒带来的痛苦无能为力。
我在心灵深处对我所嘲讽的一切怀着敬畏,我内心哭泣着跪在我的灵魂、我的过去、我的母亲面前,跪在上帝面前。直至辛克莱遇到女孩贝雅特丽齐,陷入了爱情,他回溯与德米安的过去才恍然发觉,他看到的世人不过是他自己打在世界这个荧幕上的影子,他笔下的爱人画像,不是德米安也不是他爱的姑娘,而是辛克莱自己。
无论自身是天使还是恶魔,是平庸还是高贵,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辛克莱自己。
我渐渐地感觉到这不是贝雅特丽齐,不是德米安,而是我自己。这张画像不像我——我觉得它也不必像我——但是它构成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内心、我的命运或者我的魔鬼。假如我什么时候又找到一个朋友,他就将是这个样子。假如我什么时候得到一个爱人,她就将是这个样子,我的生和我的死都将是这样,这是我的命运的音调和节奏。世上的其他人没有经历过这些吗,并不是的,每个人青春期时都曾走上过通往自身的道路,只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丢了。辛克莱经过打破建立的自我与平常人逃避建立自我的痛苦而达成的成长是不同的。
遗忘的人走向平庸,再次为自己的后代建立“无菌”的环境,一如往昔的忽视真实的世界。
学会把一部分感觉变成思想的成年人发觉童年时的这些思想丢失了,于是他们认为经历也不复存在了。而经历过痛苦思考和打破旧观念的人,开始迎接新生。
鸟从蛋里挣脱出来,蛋即世界。谁要想出生,就必须摧毁一个世界。鸟飞向上帝,上帝叫Abraxas。邪恶与正义的完备之神 Abraxas辛克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情感在外界的投射。
爱情是两者兼而有之,两者兼而有之或者还要多得多,爱情是寓于一体的天使形象和魔鬼、男人和女人,以及人和动物,极善和极恶。我觉得自己必定会有这种经历,为此付出代价是我的命运,我思念命运,害怕命运,但是它总是在这里,总是控制着我。从这时开始,辛克莱对于自我意志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阶段——通过世界与他人的投射认识自我,打破命运的枷锁。这也为之后辛克莱再次回到世界中去埋下了种子。
辛克莱开始与古怪的音乐家皮斯托利乌斯交朋友,从音乐中找寻自己,在谈天中与世界交流内心的想法。
我们必须每天更新我们的内心世界,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与德米安重逢,与Eva太太的交流一步步的推动辛克莱的自我意识趋于完整。
他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命运,不是随便哪一个命运,并在内心充分的享受它,完整而不间断地享受它。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企图逃脱,都是逃回中庸的理想,都是适应,是害怕自己的内心。人必须找到自己的梦,然后道路就轻松了。但是不存在永远不断地梦,每个梦都会被一个新的梦所代替,谁也别想把它留住。有人说辛克莱最后参军的部分难以理解,有些烂尾,与整本书的格调不符。事实上,黑塞早在前言部分就隐隐埋下了自身的完成,需要走向与其他人的联结这个观点。
世界的各种现象在这里交错只此一次,永不重复。因此,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每个人只要他在生活着,实现着大自然的意志,他就是奇妙的、值得人人关注的,在每个人身上,精神变成了形体,在每个人身上造物在忍受痛苦,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拯救者,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也刚好与蒙太奇式的结尾形成了应答,
我找到秘诀,完全进入我自身时,因为在那儿昏暗的镜子里潜藏着命运影像,我就只需向漆黑的镜子俯下身去,就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像,这影像现在完全像他,像他,我的朋友和引路人。亲爱的德米安,是辛克莱成长道路上的导师,但是为什么会两次被辛克莱撞见“如同寺庙大门上一个古老的动物面具,毫无生气,向内凝视,如死亡一般。”呢?这种趋近于死亡的状态我无法理解,或许是黑塞为了打破“导师”这个角色的圣洁性而作的把戏——即使睿智如德米安,正确如德米安,仍不过是有秘密与黑暗面的独立个体,那些构成他自身的矛盾将他塑造成一个拥有完整个性的人,才能在辛克莱的每一个阶段,给与适时的引导,将他带到新的世界中去。
每个少年都有彷徨的时刻,在躲入旧世界和迎接新世界的迷茫中等待着自己亲爱的德米安,希望能走上前往自我的道路。这不仅仅关乎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立,而与个体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我认为德米安并不是辛克莱的另一个人格,这样解读黑塞有些过于浅显,我认为德米安是先于辛克莱找到自我的一位前辈,找到了辛克莱身上的该隐标记,将他带入到寻找自我个性的道路上去,这也恰恰符合黑塞在小说的前言和最后都提醒着我们,成长完备的独立个体要发挥作用,仍要与世界和社会发生连接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