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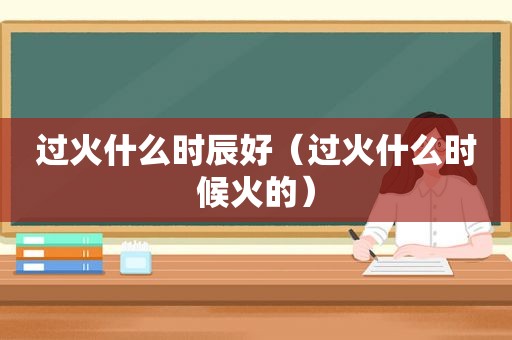
简介:一个看起来胆小的妹妹一步步引诱狡猾的继兄的故事。
有的时候兔子也会反杀狐狸。
今晚应该是姜恪和虞俏的订婚夜。
“哥哥,我这里雨下得好大,你那里大吗?”
我故意给他发了这条消息。
姜恪回得倒挺快:“开门。”
第一章:
“不要尝试弄懂狐狸,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玩笑。”
九月的歪南巷像七八月份一样,只是凭空多了点潮湿和闷热。
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巷子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罩在人的头顶,稍微在这里走两步脑门就要出汗。
“好没好啊,蒋科?”
我半蹲在阴凉处,手里拿着两根吃剩一半的冰棍,这天气热得我眼镜片都起雾。
要不是蒋科非拉着我扯什么网线这个天我是打死都不会出来的。
“好了好了。”
我从包里掏出两张纸巾递给他:“都说了天热,你非要现在弄。”
蒋科咧着嘴笑个不停,拿着纸巾在脸上随意抹了两下。
他的睫毛很长,汗水就这么挂在上面掉不下来,我想提醒他擦一擦,想想后又把话咽到了肚子里。
“行了,别抱怨了,哥哥请你吃冰棍儿。”
蒋科习惯性地想要把手搭在我的肩膀,又担心我会嫌弃自己一身臭汗,最后把动作改成了戳。
我蹲在地上专注地收拾东西,没观察到蒋科一系列的动作变化,只是闷声道:“不了,我家来人了。”
“来人?”
蒋科顺着我的话朝巷子里面看去。
果不其然黎家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款式是他们在老旧的电视上都没见过的那种。
“谁啊?”
蒋科心大,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可这次他看着那辆车心里总是没由来的心慌。
我的声音细得像只蚊子,但蒋科还是捕捉到了那个称呼。
“我妈。”
我也不知道这么称呼那个女人是否恰当,反正那个女人是这么自我介绍的。
“黎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妈妈啊。”
“你和爸爸过得怎么样?”
“饿不饿?穿得暖不暖?学习怎么样?偏科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把我问得定在那里。
我没告诉那个女人在她出现前,我被同龄的孩子骂了十六年“没妈的野孩子”。
也没反驳她问得一点儿都不恰当的问题。
我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的一角,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连喉咙里瘙痒得想要蹦出来的咳嗽都被我压了下去。
“黎国强,我今天来就是想把她带走,你放过她行吗?”
“我放过她?她十六年都是老子养的,吃我的住我的,你算什么东西让我放过她。”
黎国强的声音很大,大到听起来都有点刺耳。
我猛然想起蒋科对他的评价:“黎梨,你爸爸像个怪兽。”
当时的我还是小孩子心性,就算黎国强再不好那也是我爸爸,于是我当即就反驳了回去。
“你爸爸才像怪兽!”
蒋科也不甘示弱,一张小脸憋得通红:“反正我就觉得你爸不像个好人。”
“黎梨!黎梨!”
黎国强的声音又在耳边炸起,他在叫我,可我并不知道原因。
“问你话呢,要不要跟张丽走?”
他嘴中的张丽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女人。
我像只受惊的小兽,不知道在这个场合是该说要还是不要。
“我不……”
话说到一半又被黎国强打断:“算了,问你也白瞎。”
我又把头垂了下去。
“你冲孩子发什么火?”张丽捋了一下耳边的碎发,冷笑了一声,“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说吧,多少?”
黎国强一下子被激怒:“你他——”
“三十万够不够?”张丽冷不丁地抛下一个数字。
我眼睁睁地看着原本还气得像头狮子的黎国强一下子哑了火。
我懂三十万对黎国强的诱惑有多大,那是喝不清的白酒,打不完的扑克和抽不尽的香烟。
三十万,足以买我十六岁的生命。
就这样,我被送上了张丽的车,什么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用张丽的话来说就是到那边什么都可以买,这些破烂儿就不要了。
在话尾还加了一个腻的要死的‘乖’。
好像我们不曾分别十六年,她只是出差回家,而我还是她最疼爱的女儿。
我只向她求了一个和蒋科告别的机会,张丽皱着眉头,似乎对她来说这是多大的麻烦,不过终了她还是点了点头。
车子路过蒋科家门口的时候,我下了车,对着那扇半旧的,油漆早已脱落的木门轻轻用力,像我十六年来经常做的那样,只是这一次,我没有推开。
我失去了最后一次和十六岁告别的机会。
回到车上,张丽惊讶于我的迅速,毫无顾忌地拉着我的手跟我描述另一个家的美好。
她说她再婚的丈夫人很好,很支持她把我接过去照顾。
可惜,她说的这话并没有在我的耳朵里留存多久。
她说他也有一个儿子,叫姜恪,比我大两岁,很乖巧。
“什么?”
这是我上车来说的第一句话,张丽好脾气地询问:“怎么了?”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
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决定保守地以‘他’来代指那个未曾谋面的人。
“姜恪,”张丽笑着补充,“敬恪恭俭的恪。”
“是有重名的朋友吗?”
我没有把蒋科的名字说出口,轻轻地摇头。
我有个毛病,坐车的时间稍长一些就会发晕想吐,这次也不例外。
她仔细巡视了一圈,这车上好像没有一处是能让我赔得起的。
强行压住想要呕吐的欲望,我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强迫自己不去想还在翻涌的胃液。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围开始变得明亮。
张丽拍了拍我露在外面的手:“乖乖,我们到了。”
过分亲热的称呼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
张丽没有夸张,姜家比我想象的要大的多。
庭院称得上是宽阔,就连随处可见的一处小花圃都要比原来家的总面积都要大,里面种着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总归是名贵的。
“夫人。”
一个女佣打扮的妇人接过了张丽腕上的包回道:“老爷在客厅等着呢。”
我埋着头,方才车上的颠簸还没消尽,喉咙里止不住地泛着酸水,偏张丽拉着我的手不让我动,摆尽了一副好母亲的姿态。
我难受得不行,奋力地想转移注意力,不想一个转头冷不丁的对上了一双眼睛。
我受了惊吓没能忍住还在翻滚的胃液,直直的朝那人身上吐了上去,惹得张丽和女佣一齐惊呼:“快拿纸巾。”
我敏锐地捕捉到男生那一秒皱紧的眉头,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闯了大祸,连忙把头垂得更低,眼睛只敢对准脚下破旧的凉鞋和光洁的地板,嘴边还残留着余下的酸水,粘腻酸臭,可手边并无供我擦拭的东西,只能就这么等着它晒干,结块。
“擦擦。”
我抬眸,是一双修长的手指,指甲部分修剪得干净,指尖红润让她不由得想起了书中描写的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还不快点谢谢哥哥。”张丽戳着我的腰窝,催促着我,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这才接过那张帕子,攥在手里:“谢谢。”
我自觉忽略掉了剩下的两个字,不知为何,我总有种感觉,眼前的人是不会想听自己叫他哥哥的。
不出意料地,我听到了他的回复:“我妈没给我生妹妹。”
张丽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却也是一闪而过,立马又端起了恰到好处的笑容。
“走吧,你父亲还等着我们呢。”
“她不需要收拾一下吗?”
我反应过来他口中的她指的是自己。
张丽皱着眉头在我身上扫荡了一圈,然后吩咐:“刘妈,带黎梨去洗洗。”
我跟着她口中的刘妈走开,经过那人的时候我抬眼打量了一下,恍惚间竟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狡黠,像只爱好愚弄人的狐狸。
刘妈带着我走进一条狭窄的小道,看样子应该是姜家的家佣们自用的地方。
我对着有些脏污的镜子冲洗了好几遍,直到刘妈催促,我才直起身跟着刘妈左拐右拐进了客厅。
“这就是黎梨吧?”
我看着男人身旁的张丽意识到,他就是张丽的再婚丈夫,也是这座房子的主人,我名义上的继父,姜文华。
“姜叔叔好。”
我明显感觉到对面的男人表情一愣,张丽也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他用眼神制止:“孩子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说完,接着指着沙发旁的人儿:“那是姜恪,我儿子,比你大两岁。”
姜恪闻声抬头,我这才就着灯光看清他的脸。
他皮肤白皙,身材有些单薄,甚至透过白色的T恤能清晰地看见几块凸起的骨头,碎发有些长,堪堪遮住小半边眼睛,只露出眉尾不知道因什么留下的淡淡的疤痕。
“哥哥好。”
话脱口而出的那一刻我就有点后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了这个称呼,分明刚才他还在外面宣示了自己没有妹妹的话。
我现在的称呼倒像是故意要和他对着干。
姜恪勾起唇角,捋了一把额间的碎发,露出那双藏在黑夜里的眼睛,嗤笑一声,极尽讽刺,我被他这一声吓得发抖。
我潜意识里觉得姜恪是个危险人物,即使他方才还在外面帮了我。
“好,妹妹。”
姜恪把‘好’字的尾音拉得很长,长到快要跟‘妹妹’二字黏在一起,配上他那一张玩笑的脸更显荒诞。
“姜恪!”
我装作没看见他眼里的那故意的逗弄,在姜文华的呵斥中慌忙埋下头,以至于错过了姜恪的离开。

